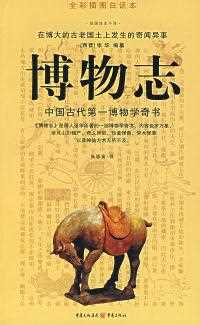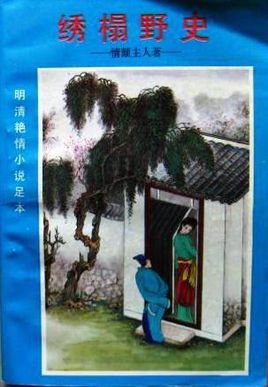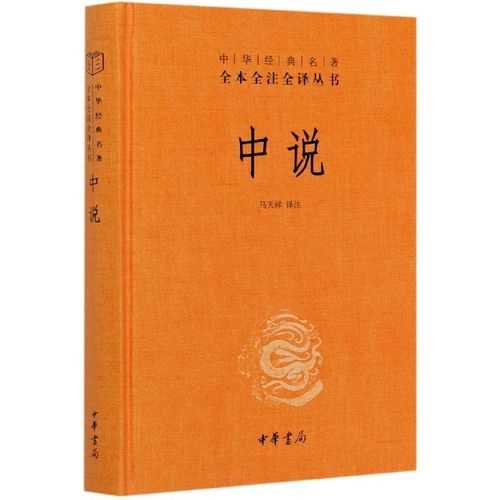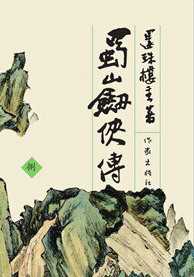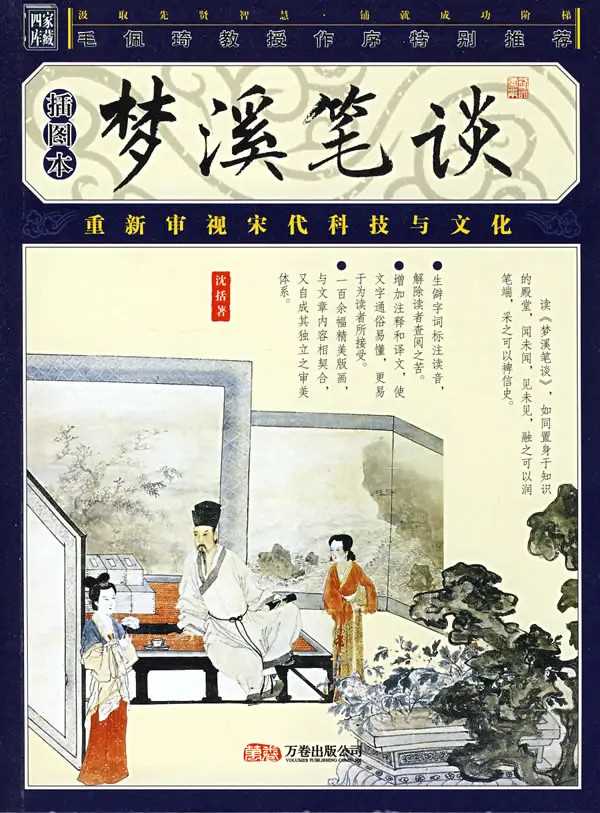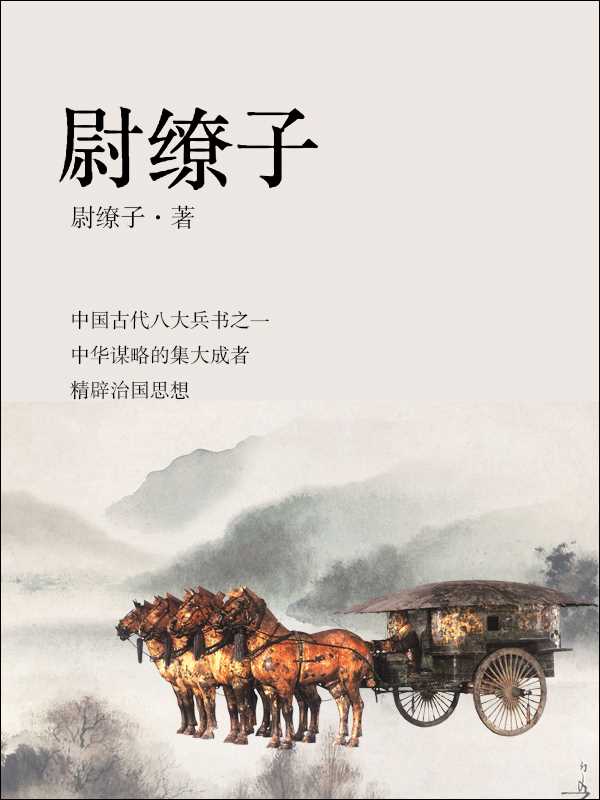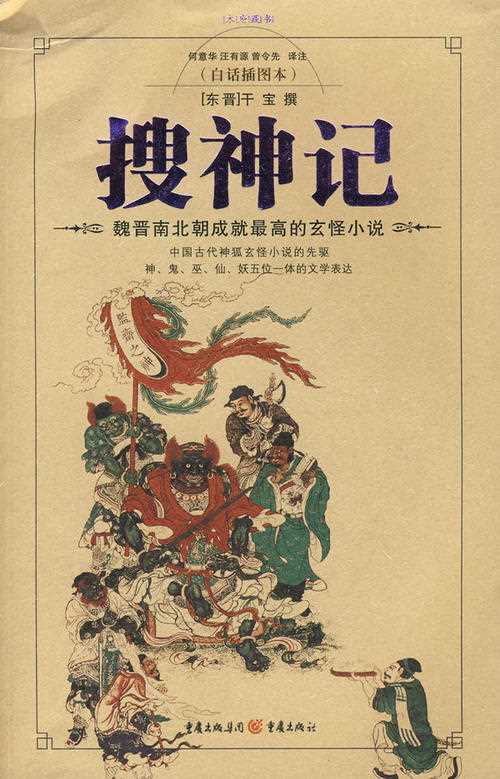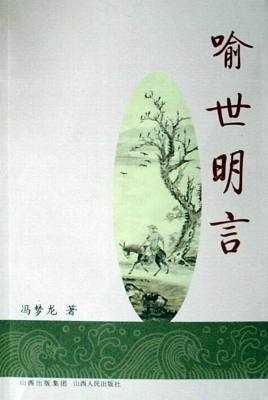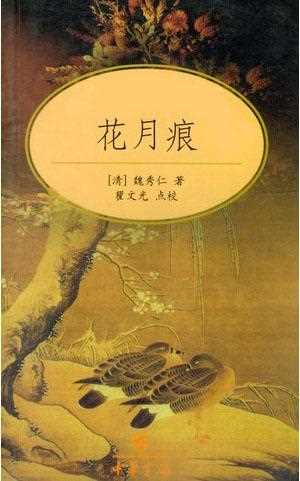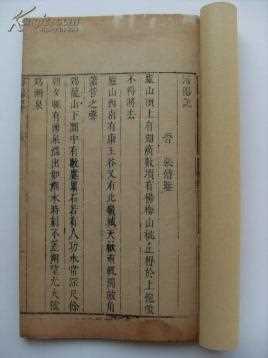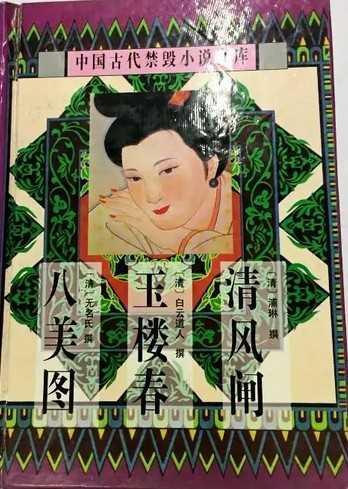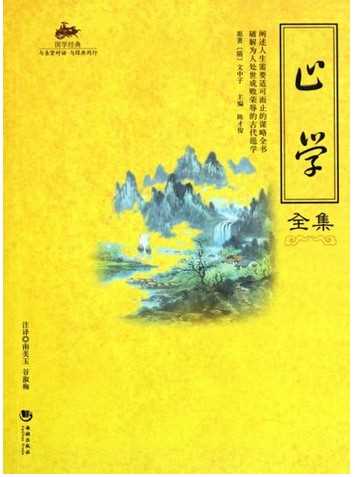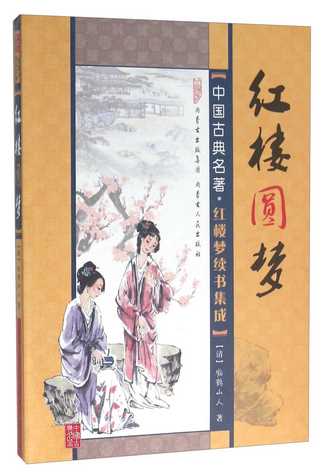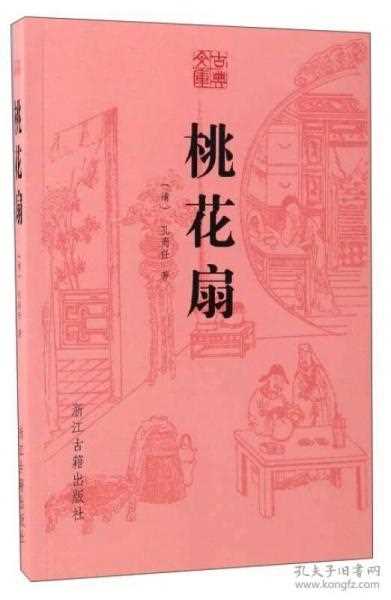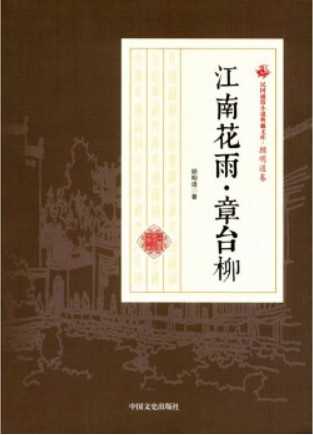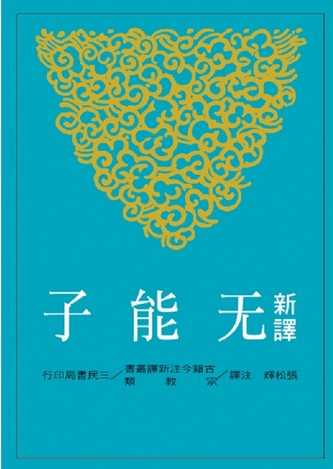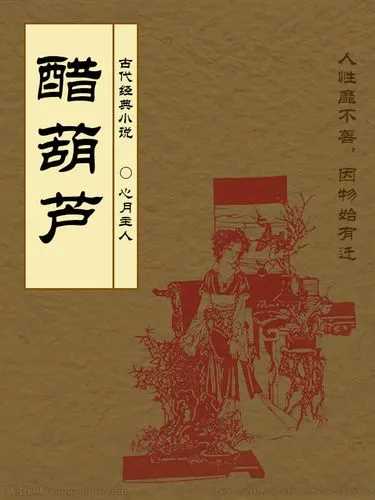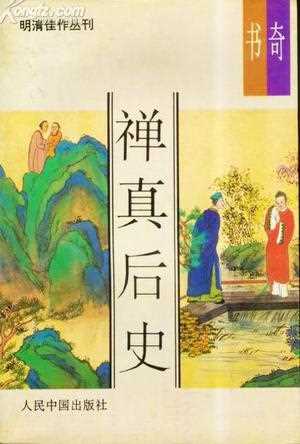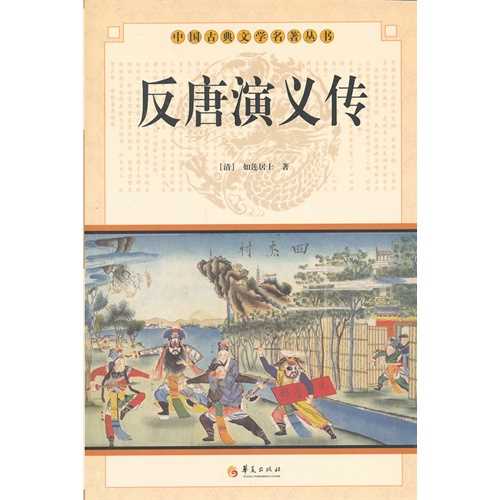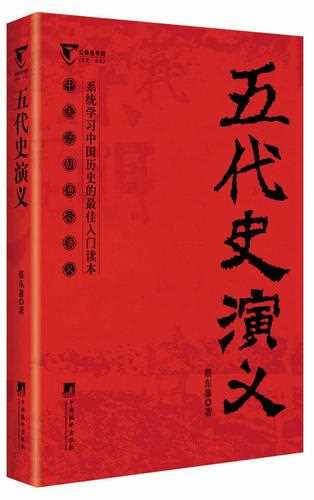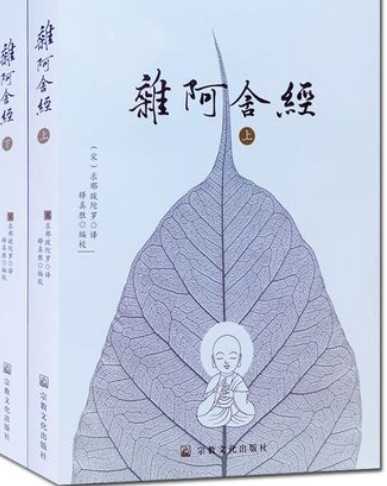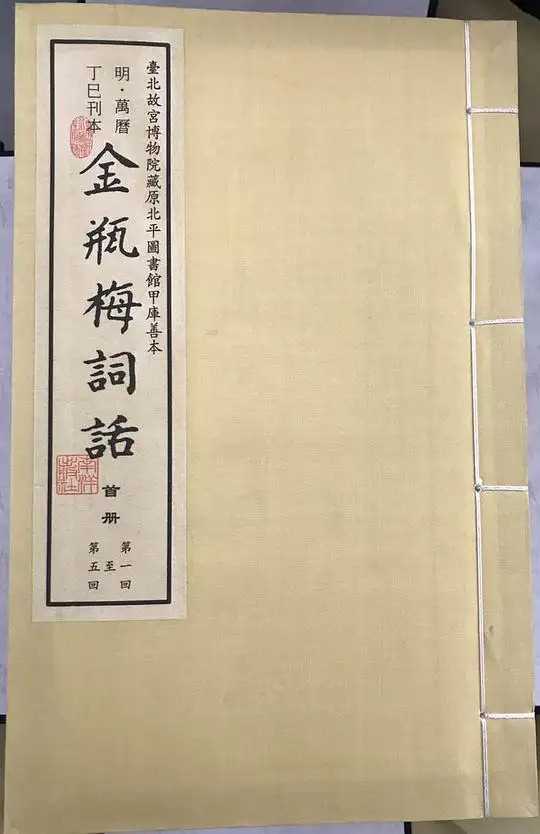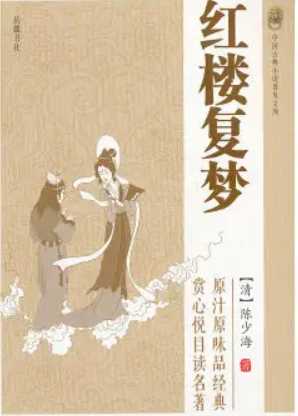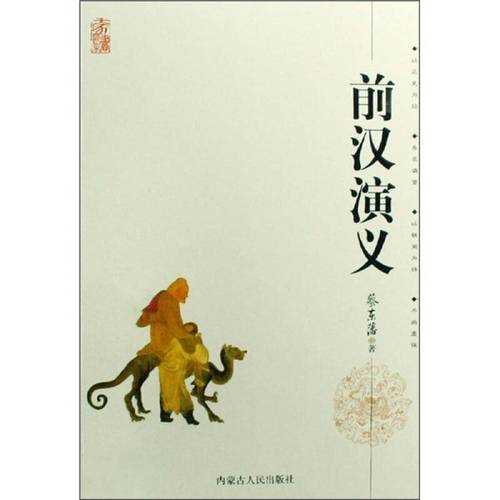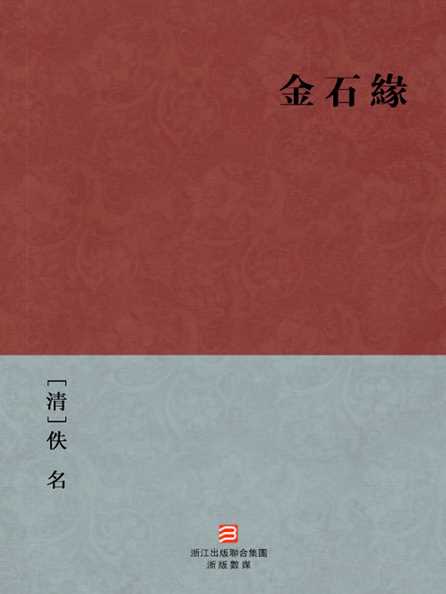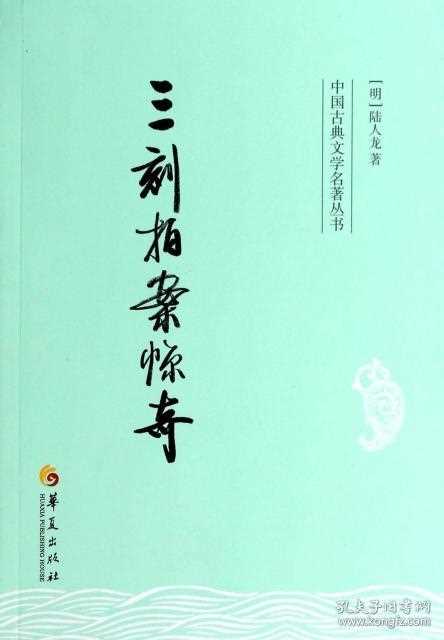云从恐父母听了着急,还不敢实话实说,只说见那人面生可疑,想知道他的来历,和二伯有何瓜葛。子敬闻言,叹了口气道:“这事实在难说。当你中举那年,不知怎的一句话,你二伯多了我的心,正赶你二伯母去世,心中无聊,到长沙去看朋友,回来便带回了一个姓谢的女子。我们书香门第,娶亲竟会不知女家来历,岂非笑话?所以当时说是讨的二房。过了半年多,才行扶正。由此你二伯家中,便常有生人来往。家人只知是你二伯的内亲。我因你二伯对我存有芥蒂,自不便问。你大伯他们问过几次,你二伯只含糊答应,推说你二伯母出身小户人家,因她德行好,有了身孕,才扶的正。那些新亲不善应酬,恐错了礼节,不便与众弟兄引见。你诸位伯叔因你二伯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宠爱少妻,人之恒情。每次问他,神气很窘,必有难言之隐。老年弟兄不便使他为难,伤了情感。至多你二伯母出身卑下,妻以夫贵,入门为正,也就不闻不问。及至你这次出门,你二伯母将她家中用了多年的女仆遣去,那女仆本是我们一个远房本家寡妇,十分孤苦,无所依归,我便将她留了下来。被你二伯母知道,特地赶上门来不依,说那女仆如何不好,不准收留,当时差点吵闹起来。你母亲顾全体面,只得给那女仆一些银子,着她买几亩田度日,打发去了。据那女仆说,你这二伯母初进门时,曾带来两个丫头,随身只有一口箱子,分量很重。有一天,无意中发现那箱子中竟有许多小弓小箭和一些兵器。不久她连前房用的旧人,一起遣去,内宅只留下那两个丫头。二伯问她,她只说想节俭度日,用不着许多人伺候。她娘家虽有人来,倒不和她时常见面。除此便是性情乖谬,看不起人,与妯娌们不投缘罢了。”
云从闻言,便去告知张老四。张老四沉思了一会儿,嘱咐玉珍:“云从虽然早晚用功,颇有进境,但是日子太浅,和人动手,简直还谈不到。醉仙师赐的那口宝剑,不但吹毛断钢,要会使用,连普通飞剑全能抵御,务须随时留心,早晚将护才好。”到了第二日晚间,张老四特意扮作夜行人,戴了面具,亲身往子华家中探看。去时正交午夜,只上房还有灯光。张老四暗想:“产妇现已满月;无须彻夜服侍。这般深夜,如何还未熄灯?”大敌当前,不敢疏忽,使出当年轻身绝技,一连几纵,到了上房屋顶。耳听室内有人笑语。用一个风飘落叶身法,轻轻纵落下去。从窗缝中往室内一看,只有子华的妻子崔氏一人坐在床上,打扮得十分妖艳。床前摆有一个半桌,摆着两副杯筷,酒肴还有热气。张老四心中一动,暗喊不好,正要撤步回身,猛听脑后一阵金刃劈风的声音。张老四久经大敌,知道行踪被人察觉,不敢迎敌,将头一低,脚底下一垫劲,凤凰展翅,横纵出去三五丈远近。接着更不怠慢,黄鹄冲天,脚一点,便纵出墙外。耳听嗖嗖两声,知是敌人放的暗器,不敢再为逗留,急忙施展陆地飞腾功夫,往前逃去。
且喜后面的人只是一味穷追,并不声张。张老四恐怕引鬼入宅,知道自己来历,贻祸云从,只往僻静之处逃去。起初因为敌人脚程太快,连回头缓气的工夫都没有。及至穿过一条岔道,跑到城根纵上城去,觉得后面没有声息。回头一看,城根附近一片草坪上,有两条黑影,正打得不可开交。定睛一看,不由叫声惭愧,那两人当中,竟有一个和自己同一打扮,一样也戴着面具,穿着夜行衣服。那一个虽纵跃如飞,看不清面目身材,竟和前年所见的那个碧眼香狒闵小棠相似,使的刀法,也正是他师父游威的独门家数。本想上前去助那穿夜行衣服的人一臂之力,后来一想不妥,自己原恐连累女婿,才不敢往家中逃去。难得凑巧,有这样好的替身,他胜了不必说,省去自己一分心思;败了,敌人认出那人面目,也绝不知自己想和他为难。权衡轻重,英雄肝胆,到底敌不了儿女心肠。正待择路行走,忽见适才来路上,飞也似的跑来一条黑影,加入闵小棠一边,双战黑衣人。这一来,张老四不好意思再走,好生为难。终觉不便露面,想由城墙上绕下去,暗中相助。
刚刚行近草坪,未及上前,便听那黑衣人喝道:“无知狗男女!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夜游太岁齐登是怕人的么?”一言未了,闵小棠早跳出了圈子去,高喊双方住手,是自己人。那夜行人又喝问道:“俺已道了名姓,我却不认得你二人是谁。休想和刚才一般,用暗器伤人,不是好汉。”闵小棠道:“愚下闵小棠,和贵友小方朔神偷吴霄、威镇乾坤一枝花王玉儿,俱是八拜之交。这位女英雄也非外人,乃是王玉兄的令妹、白娘子王珊珊。若非齐兄道出大名,险些伤了江湖义气。我和珊妹因近年流浪江湖,委实乏了。现在峨眉、昆仑这一班假仁假义的妖僧妖道,又专一和江湖中人为难,连小弟养父智通大师,都没奈何他们。公然作案,他们必来惹厌。恰好珊妹在长沙遇见一个老不死心的户头,着实有很大的家财,便随了户头回来。本想当时下手,又偏巧珊妹怀了身孕。那户头是个富绅,九房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是他本人亲生。前月珊妹分娩,生了个男孩,乐得给他来个文做,缓个三二年下手。一则可避风头,二则借那户头是个世家大户,遇事可以来此隐匿。不料近日又起变化,遇见一个与我们作对的熟人,只不知被他看出没有,主意还未拿定,须要看些时再说。好在那厮虽是父女两人,却非我等敌手。如果发动得快,一样可以做一桩好买卖。到底田地房产还是别人的,扛它不动。不如文做,趁着他们九房人聚会之时,暗中点他的死穴,不消两年,便都了账,可以不动声色,整个独吞。今晚看齐兄行径,想是短些零花钱,珊妹颇有资财,齐兄用多少,只说一句话便了。”
齐登人极沉着,等闵小棠一口气将话说完,才行答道:“原来是闵兄和王玉兄的令妹,小弟闻名已久,果然话不虚传。适才不知,多有得罪。恭喜二位做得这样好买卖。峨眉派非常猖獗,小弟纵横江湖,从来独来独往,未曾遇见对手,近来也颇吃两个小辈的亏苦,心中气忿不过。现在有人引进到华山去,投在烈火祖师门下,学习剑术,寻找他们报仇。路上误遭瘴毒,病了两月。行到此地,盘川用尽。此去倒并不须多钱,只够路上用费足矣。”闵小棠与王珊珊同声说道:“此乃小事一端。本当邀齐兄到家一叙,因耳目不便,我等出来时已不少,恐人觉察,请齐兄原谅。待我等回去,将川资送来如何?”齐登道:“我们俱是义气之交,又非外人,无须拘礼,二位只管回去。川资就请闵兄交来,小弟愧领就是。”说罢,闵、王二人便向齐登道歉走去。一会儿,闵小棠单身送来了一个包裹,交与齐登,大概送的金银不少。齐登谦谢,便行收下。闵小棠又要亲送一程,齐登执意不肯,才行分别走去。
齐登原是在安顺铜仁一带作案,路遇诸葛警我从关索岭采药回山,吃了大亏,幸得见机,没有废命。齐登立誓此仇不报,绝不再做偷盗之事。谁知路上生了一场大病,行至贵阳,待要往前再走,钱已所余无几,重为冯妇,又背誓言。心中烦闷,进城寻了一家酒铺,买了些酒肉,独个儿往黔灵山麓无人之处,痛饮吃饱。想了想,这般长路,无银钱还是不行。借着酒兴,换了夜行衣,恐万一遇见熟人,异日传成笑柄,便将面具也戴上,趁着月黑天阴,越城而入。一看前面是一片草坪,尽头处有一条很弯曲的小巷,正要前进,因为饮酒过量,贵州的黄曲后劲甚烈,起初不甚觉得,被那冷风一吹,酒涌上来,两眼迷糊,觉着要吐,打算呕吐完了,再去寻那大户人家下手。刚刚吐完,猛觉身后一阵微风,恍惚见一条黑影一闪。未及定睛注视,巷内蹿出一人,举刀就砍。这时齐登心中已渐明白,见来人刺法甚快,不及凑手,先将身往前一纵,再拔出刀来迎敌。两人便在草坪上争斗起来。闵小棠本从智通学会一点剑术,虽不能飞行自如,也甚了得。因为昨日遇见熟人,晚间便来了刺客。张氏父女和周家关系,早从子华口中探明,便疑心来人定与张氏父女有关。所以紧追不舍,仗着脚程如飞,想追上生擒,辨认面目,问明来因,再行处死。偏巧一出小巷,便见敌人停了脚步。先后两人,俱是一般身材打扮,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人并非先前奸细。及至打了半天,各道名姓,竟是闻名已久的好友。彼此忙中有错,忘了提起因何追赶动手之事,自己还以为无心结纳了一个好同党。万不料适才刺客,已经隐秘而去。
张老四等他二人走后,才敢出面。暗想:“幸亏自己存了一点私见,如果冒昧上前,一人独敌三个能手,准死无疑。如今详情已悉,自己越装作不知,敌人下手越慢。”因为出来已久,恐女儿担心,耳听柝声,已交四鼓,便绕道回来。果然玉珍已将父亲夜探敌人之事对云从说知,正准备跟踪前往接应。一见张老四回来,夫妻二人才放了心,忙问如何。张老四连称好险,把当时的事和自己主意,对云从夫妻说了。命云从暂时装作不知,最好借一个题目,少往诸伯叔家去。又说:“听敌人口气,对我们尚在疑似之间,此时我就出门,容易招疑。你可暗禀令尊,说我在江湖仇人太多,怕连累府上,可从明日起,逐渐装作你父母夫妻对我不好,故意找错冷淡我。过个一月半月,装作与你们争吵,责骂珍儿女生外向,负气出走。对方自昨晚闹了刺客,必然每晚留心,说不定还要来此窥探。不到真正侵犯,千万不可迎敌。他见我等既不去探他动静,又不防备,定以为珍儿没有认清。最近期内,他要避峨眉派追寻,必不下手。我却径往成都去寻令师,寻不见便寻邱四叔,转约能人,来此除他,最妙不过。”大家商议已定,分别就寝。
闵小棠、王珊珊两个淫恶等了三天,不见动静,竟把刺客着落在齐登身上。但还不甚放心,第四日夜间,到云从家中探了一次,见全家通没做理会,便自放心走去。子敬并不知个中真相,一则因张老四是全家恩人,加上相处这些日来,看出张老四虽是江湖上人,其言行举止,却一点都不粗鄙,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故由亲家又变成了莫逆至好,哪里肯放他走。说是纵有仇家,你只要不常出门,也是一样隐避,何必远走,再三不肯。经张老四父女和云从再三陈说利害,云从母亲只此一子,毕竟胆小怕事,才依了他们。子敬终是怕人笑话忘恩负义,作不了假。结果先是过了半月,由张老四借故挑眼,和玉珍先争吵了两句。云从偏向妻子,也和乃岳顶嘴。双方都装出赌气神态,接连闹了好几回假意气。周家虽是分炊,等于聚族而居,弟兄们又常有聚会,家中下人又多,渐渐传扬出去。各房都知他翁婿不和,前来劝解。张老四更是人来疯,逢人说女生外向,珍儿如何不对,闹得一个好女婿,都不孝敬他了。自己虽然年迈,凭这把力气,出门去挑葱卖菜,好歹也挣一个温饱,谁稀罕他家这碗怄气饭吃,有时更是使酒骂座,说些无情理的话。
闹不多日,连这一班帮他压服云从夫妇的各房伯叔都说是当老辈的太过,并非小辈的错。内中更有一两个稍持门第之见的,认为自己这等世家,竟与种菜园子的结了亲,还不是因为救了云从一场。如今他有福不会享,却成天和女儿女婿吵闹,想是他命中只合种菜吃苦,没福享受这等丰衣足食。先还对他敷衍,后来人都觉他讨厌,谁爱理他。张老四依旧不知趣似的,照样脾气发得更凶。子敬知道一半用意,几次要劝他不如此,都被云从拦住。张老四终于负气,携了来时一担行李,将周家所赠全行留下,声称女儿不孝,看破世情,要去落发出家。闹到这步田地,子敬不必说,就连平日不满意张老四的人,也觉传出去是个笑话,各房兄弟齐来劝解,张老四暂时被众人拦住,只冷笑两声,不发一言,也不说走。等到众人晚饭后散去,第二日一早,张老四竟是携了昨日行囊,不辞而别。玉珍这才哭着要云从派人往各处庙宇寻找,直闹了好几天才罢。
这一番假闹气,做得很像,果然将敌人瞒过。云从夫妇照醉道人所传口诀,日夜用功。云从虽是出身膏粱富厚之家,娇生惯养,但却天生异禀,一点便透。自经大难,感觉人生脆弱,志向非常坚定。闺中有高明人指点,又得峨眉真传,连前带后,不过三数月光景,已是练得肌肉结实,骨体坚凝。别的武艺虽还不会,轻身功夫已有了根柢。一柄霜镡剑,更是用峨眉初步剑法,练得非常纯熟。就连玉珍,也进步不少。夫妻二人每日除了练剑之外,眼巴巴盼着张老四到成都去,将醉道人请来,除去祸害,还可学习飞剑。谁知一去月余,毫无音信。倒是玉珍自从洞房花烛那天,便有了身孕,渐渐觉着身子不快,时常呕吐,经医生看出喜脉,全家自是欢喜。玉珍受妊,子敬夫妻恐动了胎气,不准习武。只云从一人,早晚用功。云从因听下人传说,二老爷那里现时常有不三不四的生人来往;张老四久无音信,也不知寻着醉道人没有?好生着急烦恼。
有一天晚上,夫妻二人正在房中夜话,忽然一阵微风过处,一团红影穿窗而入。云从大吃一惊,正待拔出剑来,玉珍已看清来人,忙喊休要妄动,是自己人。云从一看,来人是个女子,年约三十多岁,容体健硕,穿着一身红衣。手里拿着一个面具,腰悬两柄短剑,背上斜插着一个革囊,微露出许多三棱钢尖,大约是暗器之类。举动轻捷,顾盼威猛。玉珍给来人引见道:“这位是我姑姑,江湖上有名的老处女无情火张三姑姑。”说罢,便叫云从一同上前叩见。张三姑道:“侄婿侄女不要多礼,快快起来说话。”
三人落座之后,玉珍道:“八年不见,闻得姑姑已拜了一位女剑仙为师,怎生知道侄女嫁人在此?”三姑道:“说起来话长,我且不走呢。侄婿是官宦人家,我今晚行径,不成体统。且说完了要紧话,我先走去,明日再雇轿登门探亲,以免启人惊疑。”玉珍心中一动,忙问有何要事。三姑道:“侄女休要惊慌。我八年前在武当山附近和你父女分手后,仍还无法无天,做那单人营生。一天行在湘江口岸,要劫一个告老官员,遇见衡山金姥姥,将我制服。因见我虽然横行无忌,人却正直,经我一阵哀恳,便收归门下。同门原有两位师姊。后来师父又收了一个姓崔的师妹,人极聪明,资质也好,只是爱闹个小巧捉弄人。我不该犯了脾气,用重手法将她点伤。师父怪我以大欺小,将我逐出门墙,要在五年之内,立下八百外功,没有过错,才准回去。只得重又流荡江湖,管人闲事。因为我虽在剑仙门下,师父嫌我性情不好,剑法未传,不能身剑合一。如今各派互成仇敌,门人众多,不比昔日。所以和江湖上人交手,十分留心。
“上月在贵州入川边界上,荒野之中,遇见你父亲,中了别人毒箭,倒卧在地,堪堪待死。是我将他背到早年一个老朋友家中,用药救了,有一月光景,才将命保住。他对我说起此间之事,我一听就说他办得不对。侄婿是富贵人家,娇生惯养。醉师叔是峨眉有名剑仙,既肯自动收侄婿为徒,他必看出将来有很好造就,岂是中道夭折之人?遇见家中发生这种事,就应该自己亲身前往成都,拜求师尊到来除害才是,岂可畏惧艰险?你父亲早年仇人甚多,却叫他去跋涉长路。侄婿虽然本领不济,按着普通人由官道舟车上路,并不妨事。反是你父亲却到处都是危险。就算寻到醉师叔,也必定怪侄婿畏难苟安,缺少诚敬,不肯前来。怎么这种过节都看不到?你父亲再三分辩,说侄婿父母九房,只此一子,绝不容许单身上路,又恐敌人伺机下手,一套强词敷衍。我也懒得答理。因多年未见侄女,又配的是书香之后,峨眉名剑仙的门下,极欲前来探望。又因你父亲再三恳托,请我无论如何都得帮忙,最好先去成都寻见醉师叔,婉陈详情,请他前来。又说醉师叔如何钟爱侄婿,绝不至于见怪等语。我看他可怜,因他还受了掌伤,须得将养半年,才免残废。我将他托付了我的好友,便往成都碧筠庵去,见着醉师叔门下松、鹤二道童,才知慈云寺已破,醉师叔云游在外。那里原来是别院,说不定何时回来,回来便要带了松、鹤二童同往峨眉。我将来意说了。一想慈云寺瓦解,这里只有闵小棠、王珊珊两淫贼,估量我能力还能发付。等了两三天,又去问过几次,果不出我之所料。这后一次,醉师叔竟然回来又走去。听松、鹤二道童说,醉师叔听了这里的事,只笑了笑道:‘你周师弟毕竟是富贵人家子弟,连门都懒得出,还学什么道?你传话给张三姑,叫她回去,说你师弟虽然今生尚有凶险,只是若做富贵中人,寿数却大着呢。凡事有数,穷极则通,久而自了。’松、鹤二童关心同门,把详情对我说了。
“我一闻此言,只路遇熟人,给你父亲带了个口信,便赶到此地。日里住在黔灵山水帘洞内,夜里连去你二伯父家探了数次。本想能下手时,便给你家除去大害,再来看望你夫妇。谁知到了那里一看,闵、王两淫恶还可对付,因为慈云寺一破,一些奉派在外的余党连明带暗,竟有十三四个能手在这里。你二伯父迷恋王珊珊,任凭摆布,做人傀儡,对外还替他们隐瞒,只说是他妻子娘家乡下来了两三个亲戚,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如今闹得以前下人全都打发,用的不是闵贼同党,便是手下伙计。所幸他们至今还不知侄婿这面有了觉察,因避峨眉耳目,准备先将家中现有金银运往云南大竹子山一个强盗的山寨中存放,然后再借着你二伯家隐身,分赴外县偷盗。末了再借公宴为由,用慢功暗算你全家死穴,你全家主要数十人,便于人不知鬼不觉中,陆续无疾而终。最后才除去你的二伯,王珊珊母子当然承袭你家这过百万的家业,逐渐变卖现钱,再同往大竹子山去盘踞。你道狠也不狠?我见众寡不敌,只得避去。想了想,非由侄婿亲去将醉师叔请来,余人不是对手。他们虽说预备缓做,但是事有变化,不可不防。我一人要顾全你全家,当然不成。若单顾你父母妻子,尚可勉为其难。意欲由侄婿亲去,我明日便登门探亲,搬到你家居住,以便照护。至于侄婿上路,只要不铺张,异派剑仙虽然为恶,无故绝不愿伤一无能之人。普通盗贼,我自能打发。天已不早,我去了。明早再来,助侄婿起程。”
说罢,将脚一顿,依旧一条红影,穿窗而去。云从夫妇慌忙拜送,已经不知去向。因听张老四中途受伤,夫妻二人越加焦急,玉珍尤其伤心。因为三姑性情古怪,话不说完,不许人问,等到说完,已经走去,不曾问得详细,好不悬念。知道事在紧急,云从不去不行,又不敢将详情告知父母,商量了一夜。第二日天一亮,便叫进心腹书童小三儿,吩咐他如有女客前来探望少太太,不必详问,可直接请了进来。一面着玉珍暗中收拾一间卧室。自己还不放心,请完父母早安,便去门口迎候。不多一会儿,老处女无情火张三姑扮成一个中等人家妇女,携了许多礼物,坐轿来到。云从慌忙迎接进去,禀知父母。那轿夫早经开发嘱咐,到了地头,自去不提。子敬夫妻钟爱儿媳,听说到了远亲,非常看重,由云从母亲和玉珍婆媳二人招待。云从请罢了安,硬着头皮,背人和子敬商量,说是在慈云寺遭难时许下心愿,如能逃活命,必往峨眉山进香。回来侍奉父母,不敢远离,没有提起。连日得梦,神佛见怪,如再不去,必有灾祸。子敬虽是儒生,夫妻都虔诚信佛。无巧不巧,因为日间筹思云从朝山之事,用心太过,晚间便做了一个怪梦。醒来对妻子说了,商量商量,神佛示兆,必能保佑云从路上平安,还是准他前去。
云从闻知父母答应,便说自家担个富名,这次出门,不宜铺张,最好孤身上路,既表诚心,又免路上匪人觊觎。子敬夫妻自是不肯。云从又说自己练习剑术,据媳妇说,十来个通常人已到不了跟前。这些家人,不会武艺,要他随去何用?当时禀明父母,悄悄唤了七八个家丁,在后院中各持木棍,和云从交手。子敬夫妻见云从拿着一根木棍当剑,纵跃如飞,将众家人一一打倒,自是欢喜。云从又各赏了一些银子,吩咐对外不许张扬出去,说主人会武。子敬夫妻终嫌路上无人扶持,云从力说无须,只带了小三儿一人。又重重托了张三姑照看父母妻子,然后拜别父母起身,循着贵蜀驿道上路。因为想历练江湖,走到傍晚入店,便打发了轿子,步行前进。
走了有四五天,俱不曾有事。最后一日,行至川滇桂交界,走迷了路,误入万山丛里。想往回走,应往西北,又误入东南,越走越错。眼看落日衔山,四围乱山杂沓,到处都是丛林密莽,蔽日参天,薄暮时分,猿啼虎啸,怪声时起。休说小三儿胆战心惊,云从虽然学了一些武艺,这种地恶山险的局面,也是从未见过,也未免有些胆怯。主仆二人一个拔剑在手,一个削了一根树枝,拿着壮胆,在乱山丛里,像冻蝇钻窗般乱撞,走不出去。头上天色,却越发黑了起来。又是月初头上,没有月色,四外阴森森的,风吹草动,也自心惊。又走了一会儿,云从还不怎么,小三儿已坐倒在地,直喊周身疼痛,没法再走。幸得路上小三儿贪着一个打尖之处,腊肉比别处好吃,买了有一大块,又买了许多锅盔(川贵间一种面食),当晚吃食,还不致发生问题。云从觉着腹饿,便拿出来,与小三儿分吃。小三儿直喊口渴心烦,不能下咽,想喝一点山泉,自己行走不动,又不便请主人去寻找,痛苦万分。云从摸他头上发热,周身也是滚烫,知已劳累成病,好不焦急。自己又因吃些干咸之物,十分口渴。便和小三儿商量,要去寻水来喝。小三儿道:“小人也是口渴得要死,一则不敢劳动少老爷,二则又不放心一人前去,同去又走不动,正为难呢。”云从道:“说起来都是太老爷给我添你这一个累赘。我这几个月练武学剑,着实不似从先。起初还不觉得,这几日一上路,才觉出要没有你,我每日要多走不少的路。走这半天,我并不累。今天凭我脚程,就往错路走,也不怕出不了山去。你如是不害怕,你只在这里不要乱走,我自到前面去寻溪涧,与你解渴。”这时小三儿已烧得口中发火,支持不住,也不暇再计别的,把头点了一点。
云从一手提剑,由包裹中取了取水的瓶儿,又嘱咐了小三儿两句,借着熹微星光,试探着朝前走去。且喜走出去没有多远,便听泉声聒耳。转过一个崖角,见前面峭壁上挂下一条白光。行离峭壁还有丈许,便觉雨丝微濛,直扑脸上,凉气逼人,知是一条小瀑。正恐近前接水,会弄湿衣履,猛看脚下不远,光彩闪动,潺濛之声,响成一片。定睛一看,细瀑降落之处,正是一个小潭。幸得适才不曾冒昧前进,这黑暗中,如不留神,岂不跌入潭里?水泉既得,好不欣喜,便将剑尖拄地,沿着剑上照出来的亮光,辨路下潭。自己先喝了几口,果然入口甘凉震齿。灌满一瓶,忙即回身,照着来路转去。这条路尚不甚难走,转过崖角,便是平路,适才走过,更为放心大胆。如飞跑到原处一看,行囊都在,小三儿却不知去向。云从先恐他口渴太甚,又往别处寻水,他身体困乏,莫非倒在哪里?接连喊了两声,不见答应,心中大惊。只得放下水瓶,边走边喊,把四外附近找了个遍,依然不见踪影。天又要变,黑得怕人,连星光通没一点。一会儿又刮起风来,树声如同潮涌,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云从恐怕包裹被风吹去,取来背在身上,在黑暗狂风中,高一脚低一脚地乱喊乱走。风力甚劲,迎着风,张口便透不过气来。背风喊时,又被风声扰乱。且喜那柄霜镡剑,天色越暗,剑上光芒也越加明亮。云从喊了一阵,知是徒劳,只得凭借剑上二三尺来长一条光华,在风中挣扎寻找。不知怎的一来,又把路径迷失,越走越不对。
因在春天,西南天气暖和,云从虽只一个不大的随身包裹,但是里面有二三百两散碎银子,外加主仆二人一个装被褥和杂件的大行囊,也着实有些分量。似这般险峻山路,走了一夜,就算云从学了剑诀,神力大增,在这忧急惊恐的当儿,带着这些累赘的东西,一夜不曾休息,末后走到一个避风之所,已劳累得四肢疲软,不能再走。暗想:“黄昏时分,曾听许多怪声,又刮那样大风,小三儿有病之身,就不被怪物猛兽拖去,也必坠落山涧,身为异物。”只是不知一个实际,还不死心,准备挨到天明,再去寻他踪迹。此时迷了路径,剑光所指,数尺以外,不能辨物,且歇息歇息,再作计较。便放下行囊,坐在上面,又累又急,环境又那么可怕,哪敢丝毫合眼。只一手执紧霜镡剑柄,随时留神,观察动静。山深夜黑,风狂路险,黑影中时时觉有怪物扑来。似这样草木皆兵的,把一个奇险的后半夜度去。
渐渐东方微明,有鱼肚色现出,风势也略小了些,才觉得身上奇冷。用手一摸,业已被云雾之气浸湿,冷得直打寒噤。云从先不顾别的,起立定睛辨认四外景物。这一看,差一点吓得亡魂皆冒。原来他立身之处,是块丈许方圆的平石,孤伸出万丈深潭之上,上倚危崖,下临绝壑。一面是峭壁,那三面都是如朵云凌空,不着边际。只右方有一尖角,宽才尺许,近尖处与右崖相隔甚近。两面中断处,也有不到二尺空际,似续若断。因有峭壁拦住风势,所以那里无风。除这尺许突尖外,与环峰相隔最近的也有丈许,远的数十百丈之遥。往下一看,潭上白云滃莽,被风一吹,如同波涛起伏,看不见底,只听泉声奔腾澎湃。云从立脚之处最高,见低处峰峦仅露出一些峰尖,如同许多岛屿,在云海中出没。有时风势略大,便觉这块大石摇摇欲坠,似欲离峰飞去,不由目眩心摇,神昏胆战。哪敢久停,忙着携了行囊包裹,走近石的左侧。一夜忧劳,初经绝险,平时在家习武,一纵便是两三丈的本领,竟会被这不到两尺宽,跬步可即的鸿沟吓住,一丝也不敢大意。离对崖边还有两三尺,便即止步,将剑还匣,先将行囊用力抛了过去,然后又将小包裹丢过,这才试探着往前又走了两三步,然后纵身而过,脱离危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