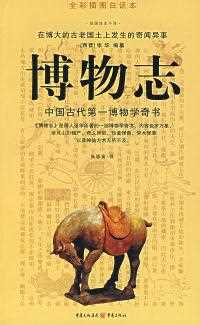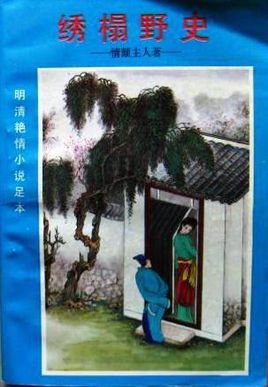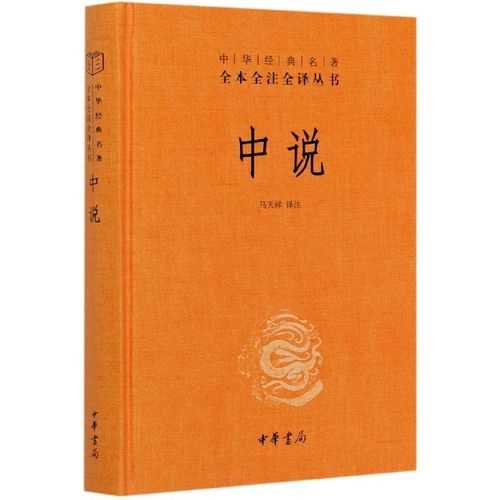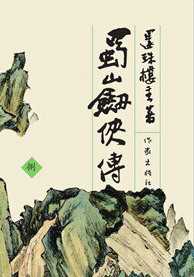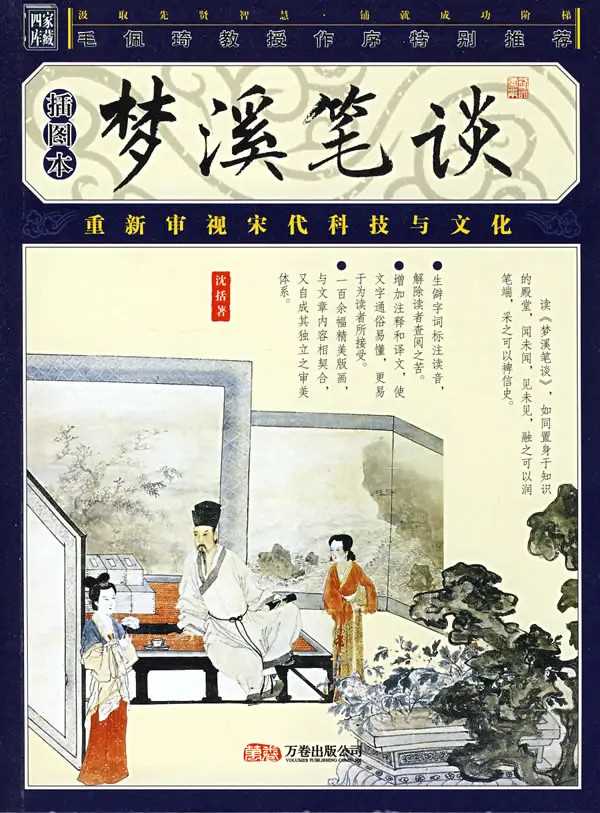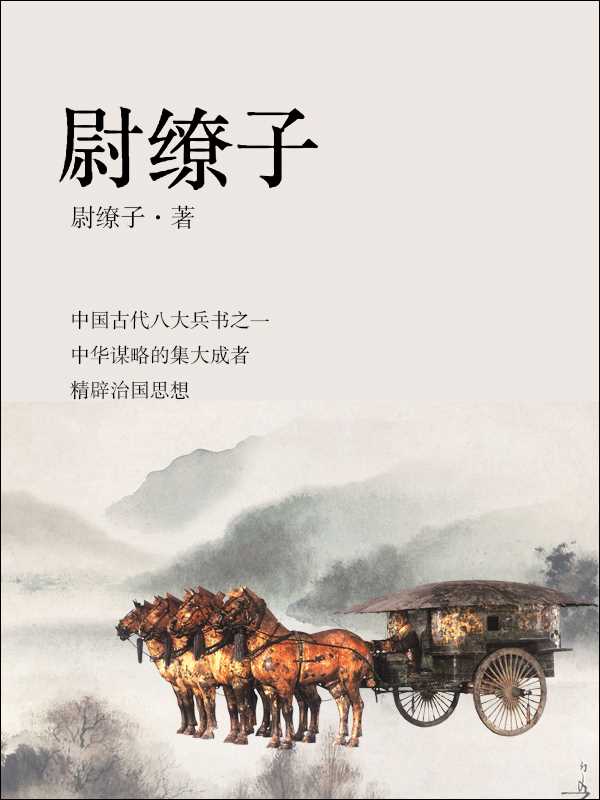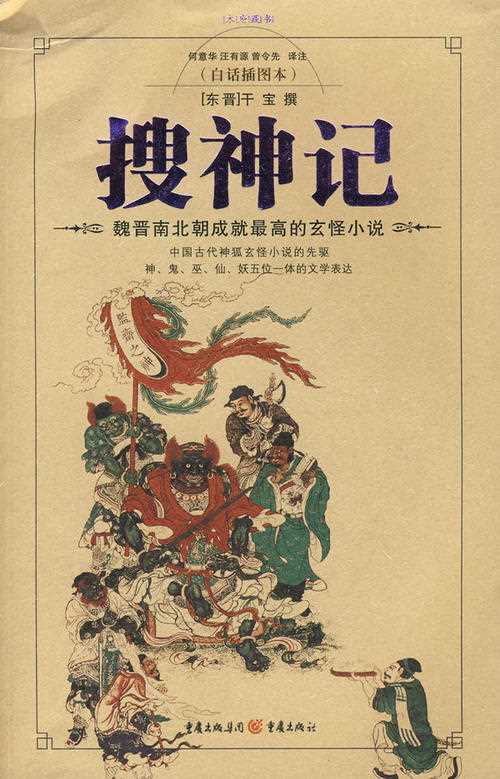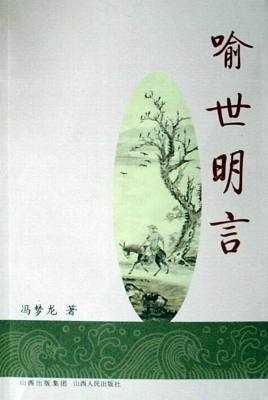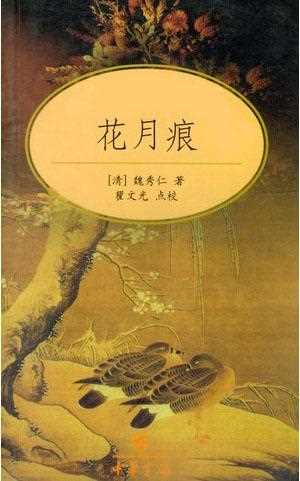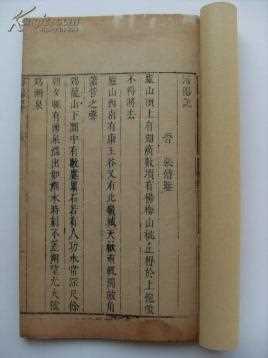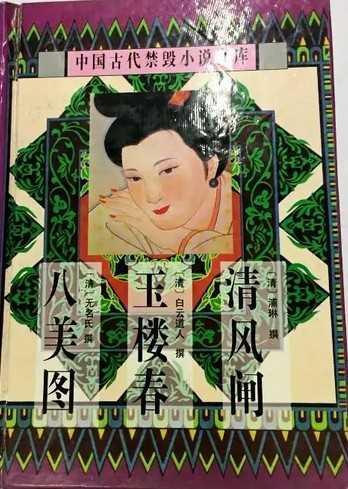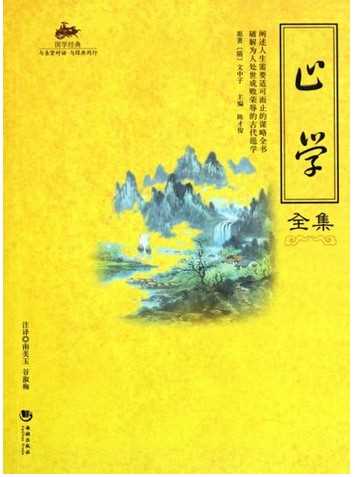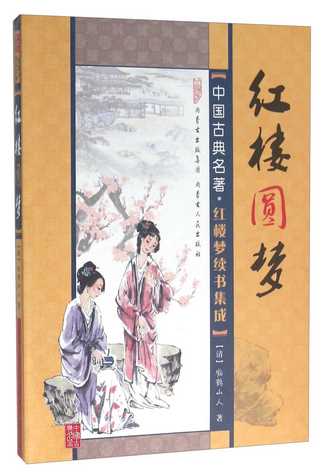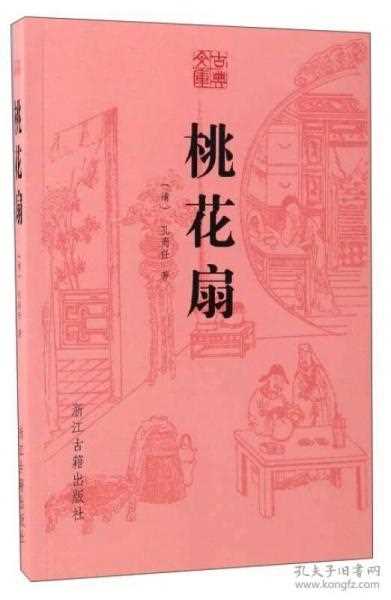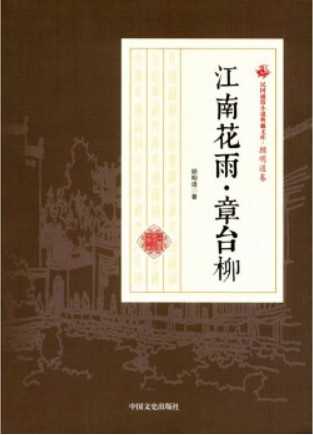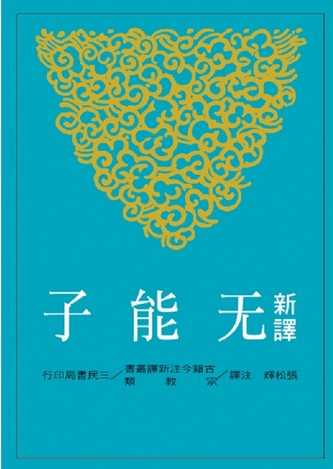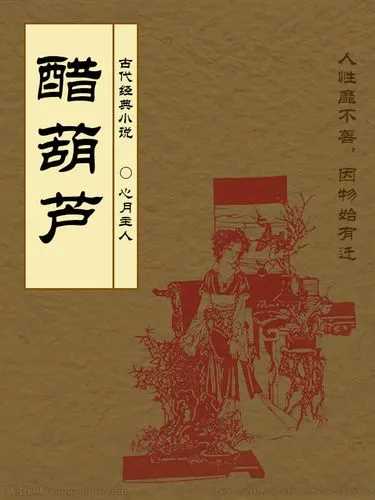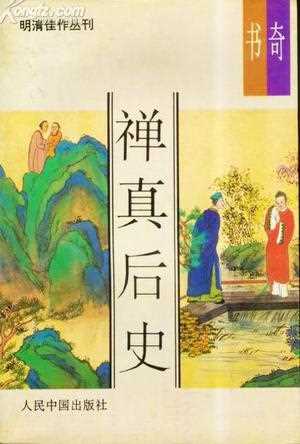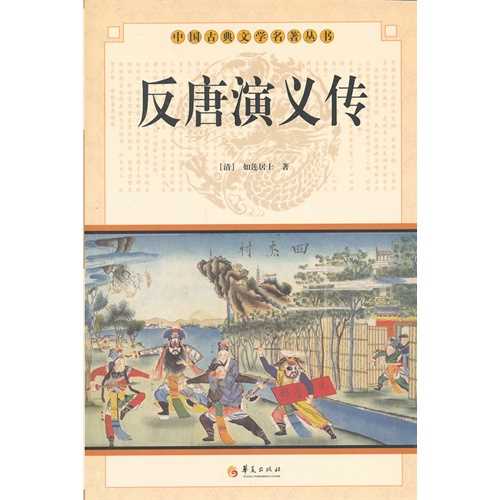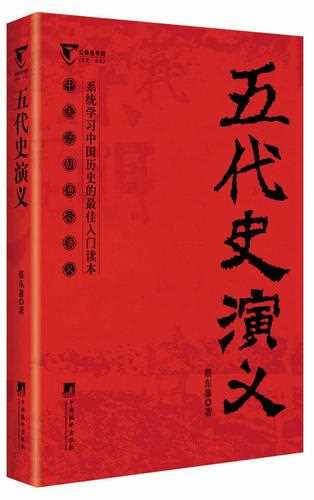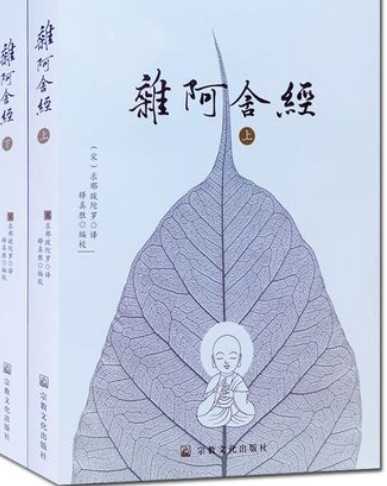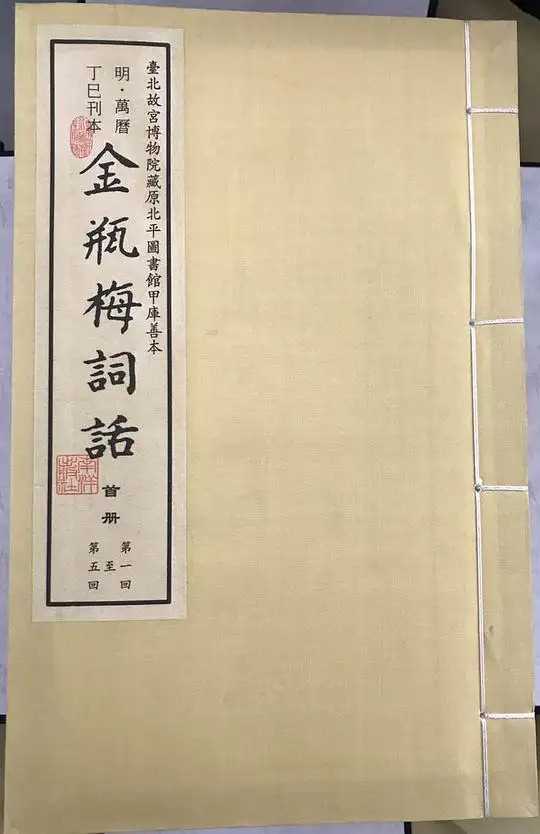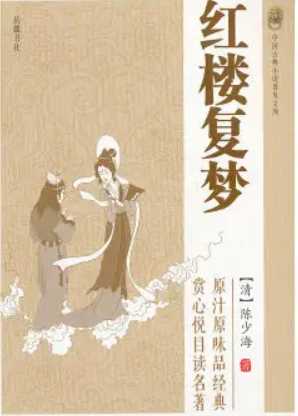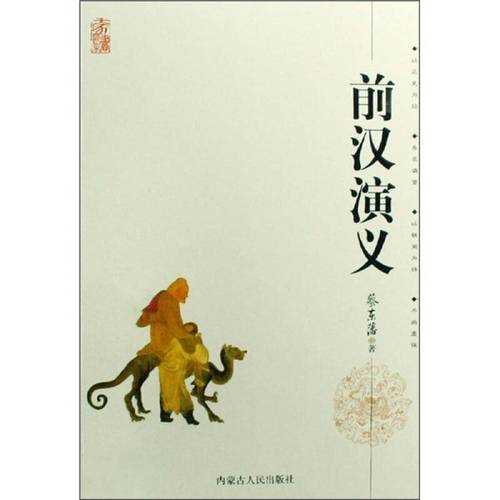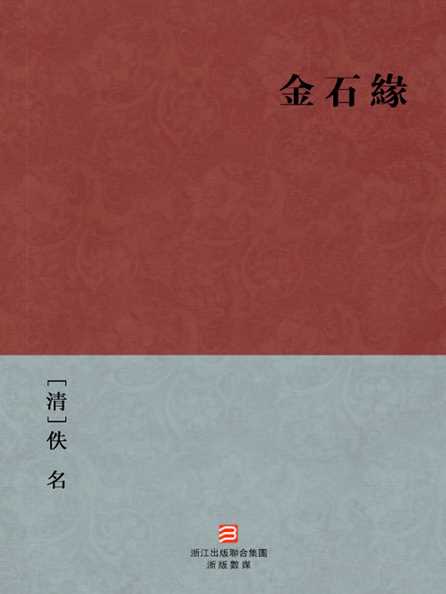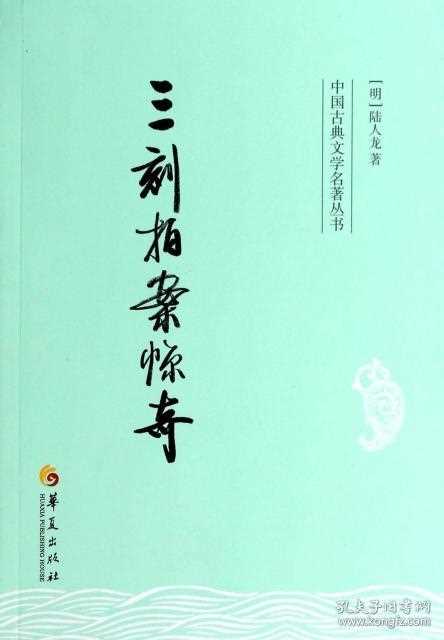却说一班上夜的家将刚走到陆曾的卧房门口,瞥见寿娥笑容可掬地也在房里,大家不由地停了脚步,数十道目光,不约而同地一齐向里面射去。这时把个陆曾弄得又羞又气。他本来是个最爱脸面的人,怎禁得起这众目睽睽之下,现出这种丑态来呢。暗自悔恼不迭地道:“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了。我一身的英名,岂不被她一朝败尽了么?”他想到这里,不禁恨的一声,向她说道:“小姐,夜深了,请回罢!”她见那班家将立在门口,那灼灼的眼睛,向里面尽看,登时一张梨花似的粉脸,泛起红云,低垂螓首,也没有回话,便站起来出了门,扶着楼梯,懒洋洋地走一步怕走一步地上楼去了。
这里众家将见了这样的情形,不由得嘁嘁喳喳的一阵子,离开房门,到了后面。有一个名叫滑因的,向众人先将大拇指竖起,脑袋晃了两晃笑道:“诸位今朝可要相信我的话了罢,我姓滑的并不是夸一句海口,凭他是谁,只消从我眼睛里一过,马上就分别出好的丑的来,就是蚂蚁小虫,只要在我眼睛里一过,就能辨出雌雄来呢。前回这姓陆的和盛大哥作对,我便说过了,无非是争的一个她,那时你们却不肯相信我的话,都说姓陆的是个天底下没有第二个的好人,今天可是要相信我不是瞎嚼了。”他说罢,洋洋得意。
有两个猛地将屁股一拍,同声说道:“我们错极了,方才这样的好机会,反而轻轻地放弃了,岂不可惜么?”
众人问:“是什么机会?”
他们俩答道:“方才趁他们在房间里,何不闯进去,将他和她捆个结实,送到太太那里去,但看她怎生的应付法,这也可以暂替盛大哥稍稍地出一口恶气。”
众人听得这话,一齐将舌头伸了一伸,对他们俩同声说道:“你们的话,说得风凉,真个吃灯草的放轻屁,一些也不费力,竟要到老虎身上去捉虱子,佩服你们的好大胆啊!不要说我们这几个,便是再来一倍,只要进去,还有一个活么?”
他两个又道:“你们这话,未免太长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凭那个姓陆的能有多大的本领,一个人一刀,就将他砍成肉酱了。”
众人都道:“只有你们的胆大,武艺高,可以去和陆曾见个高下,我们自知力量小,不敢去以卵击石,自去讨死。”
滑因笑道:“你们这些话,都是不能实行的话。依我看,不若去将老太太骗下楼梯,叫她去看个究竟,那时既可以揭穿他们的假面皮,并且那个姓陆的,就是通天的本领,到了理亏舌头短的时候,估量他虽明知是我们的玩意,却也不敢当着太太和我们为难的了;等到太太见此情形,还能再让他在这里耀武扬威的么,可不是恭请出府呢。”
众人听了他这番话,一个个都道:“好是好,只可惜是太迟了,现在已经没有效力了。”
还有一个说道:“我看今天还是未曾与他为难的为上着,如果和他为起难来,不独我们大吃苦头呢,而且太太平素很欢喜他的,暗地里难免没有招赘的意思,就是闹得明了,太太倒不如将计就计,就替他们趁此成了好事,我们倒替他们白白地做一回傀儡呢。我们现在未曾揭破他们的私事,倒无意中和姓陆的做一个人情,明天我们再碰见那姓陆的,倒不要过于去挖苦他,免得恼羞变怒,转讨没趣,知道还只当不知道,淡淡的还同当初一样。他也不是一个不明世理的,不独暗暗地感激我们十分,便是平素的架子,说不定也要卸下了。谁没有心,只要自己做下什么亏心的事情,一朝被人瞧破,不独自己万分惭愧,且要时时刻刻地去趋那个看破隐事的人,深恐他露出来呢。
”众人听他这番话,都道:“是极,事不关己,又何必去白白地恼人做什么呢?”大家七搭八搭的一阵子,便各自巡阅去了。
不料陆曾见众家将一阵嘻笑向后面而去,料想一定要谈出自己什么不好的去处了。不由得蹑足潜踪地随着众人听了半天,一句句的十分清楚,没有一字遗漏。他怎能够不生气呢,咬一咬牙齿,回到自己的房里,取了单刀,便要去结果他们。
他刚刚走出房门,猛地转念道:“我也忒糊涂了,这事只怪那贱人不知廉耻,半夜私奔到我这里来,万不料被他们看见了,怎能不在背地里谈论呢。而且他们又不明白内中情形,当然指定我与她有染了。我此刻去将他们就是全杀了,他们还不晓得的。”
他说着,复又回到房中,放下单刀,往床边上一坐,好不懊悔,暗道:“吴大哥今天和我谈的话,我还兀的不去相信,不料事出意外,竟弄出这一套来,岂不要被人唾骂么?如今不要讲别的,单说那几个家将,谁不是嘴尖腮薄的。成日价说好说歹的,无风三尺浪呢,还禁得起有这样的花头落在他们的口内么?岂不要诌得满城风雨么?到那时我虽然跳下西江,也濯不了这个臭名了。那童老太太待我何等的优厚,差不多要将我作一个儿子看待了,万一这风声传到她老人家的耳朵里,岂不要怨恨我切骨么?一定要说我是个人面兽心之辈,欺侮她们寡妇娘儿,我虽浑身是嘴,也难辩白了。”他想到这里,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童老太太,你却不要怪我,你只可恨自己生下这不争气的女儿,行为不端,败坏你的家声罢了。”
他胡思乱想的一阵子,不觉已到五鼓将尽了,他自己对自己说道:“陆曾,也是你命里蹭蹬,和吴大哥在一起度着光阴,何等的快活!不知不觉地为着一只大虫,就落在这里来,将一身的英名败尽了,明天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众人呢?不如趁此走了,倒也干净。随便他们说些什么,耳不听,心不烦。”
他打定了主意,便到床前,浑身扎束,一会子停当了,握着单刀,走出房来,迎面就碰着那一班家将,撞个满怀。众人见他装束得十分整齐,手执单刀,预备和谁动手的样子,大家大吃一惊,互相喊唔道:“不好,不好,我们的话一定是被他听见了。如今他要来和我们厮拼了,这却怎么好?”有几个胆小的听说这话,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接着大家一齐跪下。
滑因首先开口说道:“陆将军,今天千万要请你老人家原谅我们失口乱言之罪。”
陆曾出门碰见大家,正愁着没有话应付呢,瞥见大家一齐跪了下来,不禁心中暗喜道:“既是这样,倒不如趁此表明自己的心迹了。”他便对众家将问道:“诸位这算是什么意思呢?”众人一齐答道:“望将军高抬贵手,饶恕我们的狗命。”
陆曾正色对众人说道:“诸位且请起来,兄弟现在要和诸位告别了。不过兄弟此番到童府上效劳,也不过是因为她家孤儿寡妇,乏人管理家务起见,所以存了一个恻隐之心;不想在这里没有多时,就察破那个盛方不良之徒,兄弟不在这里则已,既在这里,焉能让他无法无天妄作妄为呢,不得不稍加儆戒,不料诸位倒误会我争权夺势了。”
他说到这里,众人一齐辩道:“这是将军自己说的,我们何敢诬陆将军呢?”陆曾笑道:“这也无须各位辩白了,方才兄弟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的了,不知道是哪一位老兄说的?”
众人一齐指着滑因说道:“是他说的,我们并没有相信他半句。
”吓得滑因磕头如捣蒜似地道:“那是我测度的话,并不一定就是指定有这回事的。”
陆曾笑道:“不问你测度不测度,总而言之,一个人心是主,不论谁说谁,我有我主意,却不能为着别人的话,就改了自己的行为的。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自不为。自古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如今天这回事,兄弟我也未尝不晓得诸位不明白内容的,可是背地里议论人长短,就这一点,自己的人格上未免要跌落了。但是诸位眼见本来非假,我又要讲一句翻身话了,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半夜三更,她是一个女孩子家,在我的房中,究竟是一回什么勾当呢。难道只准我做,就不准别人说么,岂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恐怕天底下没有这种不讲情理的人罢。是的,诸位的议论原是有理,兄弟我不应当驳回;但是内里头有一种冤枉,兄弟现在要和诸位告别了,不得不明明心迹。”
众人道:“请将军讲罢。”
他道:“我昨天夜里为着那个盛方,我一夜没有睡觉,所以日里有些疲倦,饭后就要睡觉了。偏生她不知何时,在我的房中,将一部《春秋六论》拿去,那时我也不晓得。到晚上我因为日里已经睡过了再也不想睡了,一直到三鼓左右,我还未登床,不料她在这时候,在楼上将书送了下来。此时我就不客气很严厉地给她一个警告,男女授受不亲,夜阑人静,尤须各守礼节,不应独自下楼。即使送书,也该派个丫头送来就是了,何必亲自送来呢?她被我这一番话,说得无词可答。这也难怪,她虽是名门闺秀,娇生惯养,而且未经世务,不知道礼节,也是真的却断不是有心为此的。我陆曾堂堂的奇男子,大丈夫,焉能欺人暗室,做这些丧心病狂的事呢?我的心迹表明了,诸位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皇天后土,神祗有眼。但是兄弟去后,一切要奉劝诸君,无论何人,不拘何事,皆要将良心发现,我希望全和陆曾一样,那就是了,千万不要瞒天昧己,欺孤灭寡,免得贻羞万代,这就是兄弟不枉对诸君一番劝告了。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说了,再会罢。”
他说罢,大踏步直向吴古房中而去。这里众人,听他这番话,谁不佩服,从地下爬起来,互相说道:“还是我们的眼浅,不识好人,人家这样的见色不迷,见财不爱,真不愧为大英雄,大豪杰哩!”
不说众人在这里议论,再说陆曾到了吴古的房中,只见吴古已经起身,正在那里练八段锦呢,见他进来,浑身扎束,不由得一惊,忙问道:“兄弟,你和谁动手,这样的装扎起来?”
他叹了一口气道:“兄长,悔不听你的话,致有今日的事。
”吴古忙问是什么事情。他便将以上的事情细细地说了一遍。
吴古跌脚叹道:“我早就料到有此一出了。那个丫头,装妖作怪的,每每的在你的面前卖俏撒娇的,你却大意,我早已看出她不是好货了。为今之计,只好一走了事,这里再也不可停留了。”
他说罢,也略略的一装扎,便要动身。陆曾忙道:“大丈夫明去明来,我们也该去通知童老太太一声,才是个道理呢!”
吴古忙道:“那可动不得,我们要走便走,如其去通知她,料想她一定是要苦苦地挽留,我们那时不是依旧走不掉么?”
陆曾道:“你的话未为不是,但是她们是寡妇娘儿,又有这极大的财产,我们走虽然一文未取,但是被外人知道,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为着什么事情走的,如此不明不白,免不得又要人言啧啧,飞短流长了。”
吴古听他这番话,很为有理,俯首沉吟了一会子,便对他笑道:“那么何不去骗她一下子,就说我们现在要到某处某处投亲去,大约在一月之内就来了。我想这样,她一定不会阻止的了。”
陆曾摇头说道:“不妥,不妥,还不是和暗地走一样的吗?我想这样罢,也不要去通知童太太,只消我们写一封信,留下来就是了。”
吴古道:“好极了,就是这样的办罢。”他说罢,便去将笔墨纸砚取了过来。陆曾一面将纸铺下,一面磨墨,一会子提起笔来,上面写着道:仆等本山野蠢材,除放浪形骸外,无所事事。谬蒙青眼,委为保家,俯首衔恩,何敢方命!兢兢终日,惟恐厥职有疏,致失推崇之望。但仆等阅世以来,早失怙恃,所以对于治家之道,一无所长,所经各事,颇多舛误,惶愧莫名。自如汗牛充栋,误事实深,不得已留书告退,俾另聘贤者。负荆有日,不尽欲言!
他将这封信写完之后,吴古便道:“写完了,我们应该早些动身了,免得童太太起身,我们又不能动身。”陆曾道是。
说着,便与他一跃登屋,轻如禽鸟,早已不知去向了,从此隐姓埋名,不知下落。小子这部《汉宫》,原不是为他两个著的,只好就此将他们结束不谈罢。
床话少说,再表童太太。到辰牌时候才起身,忽见一个丫头进来报道:“吴将军和陆将军不知为着什么事情,夜里走了。
”
童太太听说这话,大吃一惊,忙问道:“你这话果真么?”
那个小丫头忙道:“谁敢在太太面前撒谎呢?”
童太太连忙下楼,到了吴古的房里,只见一切的用物和衣服一点也不缺少,桌子上面摆着一封信。童太太忙将信拆开一看,不禁十分诧异地说道:“这真奇了,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十分精明强干,没有一些儿错处,怎么这信上说这些话呢,一定是谁得罪了。”
说罢,便将家中所有的仆妇家丁,一齐喊来,大骂一顿,骂得众人狗血喷头,开口不得,受着十二分委屈,再也不敢说一句。童太太骂了一阵子,气冲冲扶着拐杖径到寿娥的楼上。
只见寿娥晨妆初罢,坐在窗前,只是发愣,见了童太太进来,只得起身迎接。
童太太便向她说道:“儿呀,你可知道吴、陆两将军走了?”
她听说这话,心坎上赛如戳了一刀,忙道:“啊哟,这话果真么?”
童太太道:“还不是真的么,我想他们走,一定是我们这里的佣人不好,不知道什么地方怠慢了人家,也未可知,天下再也找不出这两个好人了。唉!这也许是我孙家没福,存留不住好人罢了。”
寿娥听说陆曾真正地走了,那一颗芳心,不知不觉地碎了,但是当着她的母亲,也不敢过霹形迹。等到她走了之后,少不得哽哽咽咽地哭泣一阵子,自叹命保谁知伤感交加,不知不觉地病倒了,百药罔效。眼见病到一月之久,把童老太太急得一点主意也没有,终日心肝儿子的哭个不祝她的病,却也奇怪,也不见好,也不见歹,老半明半昧的,不省人事,镇日价嘴里终是胡说不已。童老太太不知道费了多少钱,请过多少医生,说也不信,一点效验也没见。童老太太的念头已绝,只得等着她死了。
有一天,正到午牌的时候,家里一共请了有三十几个先生,互相论症用药。到了开饭入席的当儿,只见众人的当中,有一个二十几岁的道士,头戴纶巾,身穿紫罩一口钟的道袍,足蹬云鞋,手执羽扇,面如猪肺,眼若铜铃,但见他也不推让,径从首席上往下一坐,众医士好不生气。孙府里众家将和一班执事的人们见他上坐,还只当他是众医生请来替小姐看病的呢,所以分外恭敬,献茶献水的一毫不敢怠慢。
众医士见孙府的人这样的恭敬道士,一个个心中好生不平,暗道:“既然是将我们请来,何必又请这道士做什么呢?
这样的恭敬他,想必他的医术高强,能够将小姐的病医好了,也未可料定。”
不说大家在那里互相猜忌,单表那道士拖汤带水的大吃特吃,嘴不离匙,手不离箸,只吃得满桌淋漓。众医生不觉十分讨厌,赌气爽性一筷子不动,让他去尽性吃。他见众人不动手,却再也不会客气一声,仍旧大张狮子口,啅啯啅啯的不停手。
一会子席散了,童老太太从屏风后面转了出来,向众医士检衽说道:“小女命在垂危,务请诸位先生施行回天之术。能将小女救活,酬金随要多少,不敢稍缺一点的。”众医士异口同声地说道:“请太太不要客气了,你家已经请得回天之手,我们有何能干?”童太太惊问:“是谁?”众医土一齐指着那个道士说道:“不是他么?”这正是筵上何由来怪客,观中设计骗娇娃。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