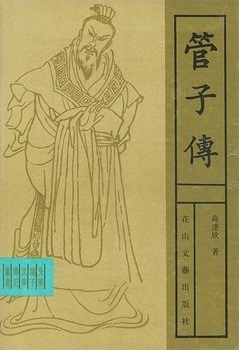德川家康回到三河,京城和大坂的民心为之一变。
武将都在一心一意准备征伐九州,百姓却松弛了许多。大家都已安下心来,准备过天正十五年的新年。城里为了战事费度而处处喧嚣,却无人为战争担惊受怕。这当然是秀吉宣扬得当之故。尤其是家康率大军前来,表明非敌而友的立场,使百姓放下了悬着的心。
“如此一来,关白大人又多了一个帮手。”
“是啊,来年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德川大人是新时代的使者啊!”
“不不,关白大人毕竟是非凡之人。”
“如此一来,九州可一举平定。本来德川大人率大军来,是协助平定九州的,被关白大人笑着谢绝了,说要把东海道托付给德川大人,他对九州一战信心百倍!”
“当然,关白大人不仅要平定九州,还要征伐大明国和天竺哩!”
百姓话语简单粗糙,看法却犀利而准确。他们虽未看透秀吉和家康的心机,却也多少看出了二人的忧喜,看出了此次二人见面,给世间带来了哪些变化。
家康离开京都后第四日,井伊直政便护送大政所一行由冈崎出发,于十一月十八抵达粟田口,京都的街道上热闹得如过大节一般。没人说大政所是人质。当然,那是因为京都和大坂人都偏袒秀吉,既无人告知他们大政所此行是去见朝日姬,也无人下令要他们张灯结彩,可是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着彩灯。人们像庆祝自家喜事一般欢呼雀跃,“恭迎大政所平安归来!”
秀吉在浅野长政陪同下来到粟田口迎接母亲,径直道:“井伊兵部在何处?”来到直政身边,秀吉取下佩刀赠与他,以示谢意。
大政所归来之事亦传到了大坂。她在内野过了一夜,搭船到大坂时,大坂城中的欢乐气氛,比京城高出许多。秀吉终于完全洗刷掉了小牧长久手之役以来的丑名,他的为政手腕也已路人皆知。
但,在这大张旗鼓准备出征的活跃气氛中,唯一人冷静远远超出常人,甚至似超出了家康和秀吉,而陷入闷闷不乐之中。此人非别人,乃秀吉之妻、被世人称为“女关白”的北政所。
当大政所回到大坂城,宁宁请她到自己房中用饭,仔细询问她在冈崎状况。大政所提起城代本多作左卫门时,满面不快:“这种乖僻之人啊,哪家都不少!”她面露责难之色,却又为他辩护,“却莫要过于责怪他,因为这种乖僻人哪,最是可怕!”
“可怕?”
“预料不到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而且朝日还留在那里。”
宁宁立刻感到自己问多了,她只想多知些本多作左的事。侍女们主张不应放过作左,否则会有损关白的威仪。大政所却因担心作左会加害朝日姬而忧心,她主张,以探视己病为由,把朝日姬接回大坂,然后,可从容吩咐作左卫门切腹。“他在别馆四周堆积木柴,喔唷,简直是个疯子。”
宁宁冷静地思量,如家康这般人,本不应让疯子为城代,此事即有两种可能:其一,这些都乃家康的密令;其二,作左为了家康的安全,乃自己想出这一狠招,欲令秀吉投鼠忌器。
第二日晨,宁宁叫来浅野长政,道:“井伊兵部今日当会来此,怕我们的人不能好生款待,干脆让石川数正和他同席吧。”
“让他们同席?”长政惊问,又恍然大悟地拍拍大腿,明白夫人深意----若作左堆柴火乃受命于家康,那么石川数正的出奔,亦极可能是在执行命令,有意让他们二人相见,以便暗中观察,遂道:“在下明白。”
“只在席上还无法完全洞察其心,茶桌上也让他们同处,多给些方便。”
“是。”
“还有…………靠近些。”夫人凑到长政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过后,长政惊愕地看着她,大声道:“一定照办!”
第二日,通过长政,宁宁不仅了懈了直政和数正,还知悉邀直政用餐的秀吉的想法。
在饭桌与茶席上,年轻的直政对数正是一言不发,以轻蔑的目光盯着出奔者。四目相遇,直政瞪得愈狠。数正则尴尬地垂下头,不敢正视。
“那么,关白大人怎样责备直政的?”宁宁急急地问长政。不管怎么说,秀吉到底是关白。直政对丰臣家臣石川出云守数正无礼,当然应不留情面。难道他没有斥责?宁宁想到这里,语气软了下来。
长政果然大摇其头,道:“非但未责备,还要嘉奖他,赐姓羽柴。”
“赐姓羽柴?”
“是。我觉得大人真是器量如天。”宁宁不解地摇头,“直政接受了吗?”
“夫人应清楚。”
“连鸟居新太郎这个侍童都敢违抗大人,大人也真是…………哼!兵部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井伊一门自南北朝以来,便是驰名远江的名门大户,和皇室都有密切的关系。即使主公家康赐姓松平与他,也因不能接受而作罢。若在这里受关白赐姓,便无颜面对天下。”
“哦!既不接受松平,当然也不接受羽柴。”
“是。”
“大人听了,是何态度?是不是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不,在下觉得,大人胸怀如海。”
“长政,一次两次有些度量就够了。本多作左卫门、鸟居新太郎,这一次井伊兵部…………怪不得大纳言(秀长)会动怒。”
“纳言动怒了?”
“对!母亲大政所为质,实乃奇耻大辱!还敢在她住处周围堆上柴火,天理何在!”
长政认真地思量着,沉吟道:“忍耐固然要紧,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则几近谄媚。对作左卫门退让,不可再有第二次!”
宁宁突然呵呵笑了,这些不当让太多人知。她道:“我可能年纪大了,脾气也坏了,实在糟心。这些事到此为止吧。”
“是,在下告辞了。”长政退下后,宁宁又叫来陪侍曾吕利新左卫门:“新左!有什么话能让我开开心?我听了母亲在三河之事,心中不快。”
“有趣的话?”曾吕利新左卫门露出旁若无人的笑容,“讲些本愿寺的上人大哭的事,可好?”
“上人为何大哭?”宁宁惊问。她甚知此人,在曾吕利新左卫门诙谐的话语背后,往往隐藏着对世事的敏锐洞察。有时,他的诙谐甚至可以左右千宗易。即便在堺港人当中,像他这么有才智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因为他终于把礼物送给德川大人了。无论怎么说,兴门寺的上人也是在出使途中,惊惶失措地逃了回来啊!”
“你是说,因为未打仗,他才放怀大哭?”
“只是这样还有何趣,夫人?”
“是,的确无趣。”
“德川大人平安归去后,茶屋四郎次郎去拜访了上人。”
“哦,这也无趣。”
“可是,上人拿出西洋胡椒粉回赠茶屋。但在给茶屋解说能书时,袋子却破了。”
“胡椒粉入眼,上人便大哭?”
“不!屋里弥漫着浓浓的胡椒粉,上人一边掉泪,一边打喷嚏,既有趣又奇怪。”
“这个叫茶屋的绸缎庄老板和你很要好?”
“是。”
“带他来这里,拿一些绸缎给我看看。”夫人淡然道。
“是。不如此,天下便不能统一。”曾吕利新左卫门突然道。
“提起天下统一,你们有什么目标?若天下平定,刀兵入库,以后又会怎样?”
“哈哈,接下来恐要征伐西洋。到那时,在下也会以侍将的身份去极乐岛。”
“最近关白大人有些变化,你看出了吗?不,可能外人还不知其变化。”新左卫门沉默无语。接着,夫人故意压低声音道:“你怎样认为?”
“既然夫人已知,就不怪新左多嘴了。据说,大人出征九州时,似要悄悄把她转移到京城,待凯旋归来,再把她送去内野的聚乐第然后向夫人摊牌。”
“哈哈,你是说茶茶?”
“哦?夫人早已知道?”
“我不问茶茶。我只想知,关白在堺港人眼里,有何变化?”
新左卫门好似胸口被刺了一刀,脸上的诙谐之色顿时消失,脸绷得紧紧的,连一条一条的皱纹都清晰可见。他咽下一大口唾沫,举止依然大方,心中却在紧张盘算:说还是不说?宁宁知他在迟疑,道:“新左,你认为以你的诙谐本领,就足以追随关白大人?”
“夫人。”
“我非有意为难你。身为北政所,我有责任…………不,从秀吉还是木下藤吉郎时,我便已在尽人妻之责。”
“夫人!”曾吕利道。聪明的他知道,一旦说漏了嘴,就会被夫人看不起,而使得堺港众人成为关白内庭的大敌。“夫人到底目光犀利。小人一心为大人着想,必当如实回禀。”
“那么,堺港人也认为大人变了?”
“是。说得明白些,纳屋蕉庵先生和夫人有同感。”
“他怎么说?”
“他说自从小牧之役开始…………”
“小牧之役?你把他所说重述一遍。”
“是。”曾吕利悄悄拭去额头上的汗水,“在小牧之战以前,大人信心十足,时时处处如有神助,征战中国、山崎之役、清洲会议、北伊势之役,无不连战连捷,攻佐佐木、击柴田,有惊无险,对岐阜势如破竹…………关白大人乃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那以后呢?”
“大人似有些陶醉于自己是为拯救苍生而生的神子说法。在小牧之战中,第一次碰壁。此话是纳屋先生说的。”
“何止是碰壁!不,就算是吧。那个纳屋说大人变成了什么样子?是说大人不再有强烈的自信了?”
曾吕利新左卫门眯起眼睛,使劲摇头,道:“不是,但要警惕。换言之大人第一次知道了山外有山,会因心存畏惧而动摇本心,转用谋略压制。”
“他对堺港人也不甚放心吗?”
“是。这也是蕉庵先生的看法。小人不知宗易先生是何看法,不过,结果正如夫人所知,关白大人与德川大人对相见都甚为满意。但追溯到小牧之役,毕竟让大人知,有他武力所不能克之人,正是德川大人。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人终是胜了。”
宁宁听到这里,挑了挑眉毛,“那么,堺港百姓担心什么?说来听听。”
新左卫门已不再那么紧张了,他轻轻点头,悄然环顾四周。“人总有与生俱来的性情。”此时他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谨慎措辞道,“蕉庵先生说,太过任性,自会坚持己见。”
“是说大人太同执?”宁宁目不转睛地看着曾吕利,“他还说了些什么?”
“大人留下德川大人这个对手,日后德川大人定会和他争个不休。以关白大人的性子,只会执意处处使德川大人居于他之下。”
“哦!”
“征伐九州或平定东海道,自会兵不血刃。可是,战事一毕,国事便将是关键了。”
“此后,他们还会一直斗下去?”
“是啊,想停也停不下,因为活生生的对手始终存在。”曾吕利说着,漫不经心地笑了,但突然敛起笑容,“此乃性情使然,关白大人必想把对方压倒,但若在大略上出了差池,不只大人,连日本都会陷入危境。”
“日本…………”
“是,日本已在大人掌中,故,接下来是要征服大明国、天竺,还会远征西洋诸岛…………”
宁宁闭上眼睛,曾吕利所言与她的忧虑完全一致。且不说家康,只秀吉那精力旺盛、一刻也不肯停下的性子,宁宁已放心不下----他定会一直追逐下去,拼着性命,至死方休。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