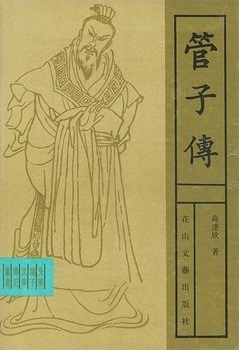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再次会面,完全是丰臣秀吉一手安排的。
家康反复表明,他无意和秀吉为敌,同席的石川数正亦在一边打圆场。家康按照秀吉的安排,领受了从二品权大纳言之职,进宫向天皇谢恩后,便回了三河。行前表示,朝日并不急着回京。若有紧急情况,可以年老的大政所病危为由,接她回来。
“朝日不愿离开骏府?哈哈,她不会是喜欢上那孩子了吧。女人也真是的,给那孩子领受了秀忠的名字回去,朝日应欢悦。这样,她的养子就成了从五品藏人头德川秀忠。”秀吉轻松地笑了,之后便准备迁居聚乐第诸事。
搬迁日期定于天正十五年九月十八。光是运送金银等物就动用了数百艘船,运到码头再换车。动用车辆五百、人夫五千。
北政所在五日前便与大政所从大坂城出发,前往京都。打头的乃是大政所抬物的轿子十五乘、供人乘坐的轿子六乘,伴有四个骑马武士;之后为大约五百名艺人,个个身着红衣,像是神舆通过的场景;接下来为本愿寺住持之妻;随后是北政所宁宁一行。这个行列抬物的轿子百乘,供人乘坐的轿子二百乘,数不清的长方柜子排成了长蛇,之后随有与前边同样装束的骑马武士。
虽然禁止男人及出家人旁观,但路上依然有很多男人和女人在两旁觋看。没有人去盘问或是责备,禁令有名无实。宁宁当然没想严格执行命令,在队伍到达京都之前,她都视若无睹。
虽然宁宁乃初次见到聚乐第,但是从秀吉的言行可以判断,这必是个极尽奢华的府第。但其奢华仍然远超出宁宁的想象。四周建有三千步长的石墙。铁柱支撑着门楼,富丽堂皇的铜门熠熠生辉,左右洞开。恐怕这样的铜门在海内找不出第二扇。宁宁想着,走过大门,只见大玄关门廊上的屋瓦华美得令人叹为观止。在后世的《聚乐第行幸记》中有言为证:瑶阁高耸,几达天际;琼殿含光,直指云霄。檐角玉虎高啄,傲然迎风长啸;又有金龙,盘旋云中长吟。丝柏葺顶,门廊环绕。歌台暖响,其乐融融。维兹屏风,大匠攻之,重葩累绣,其美无以名状。
面对如此豪华的府邸,宁宁无奈地摇了摇头。
到达聚乐第三日,宁宁才从侍女口中听到茶茶姬之事。并非有人主动告密,只是侍女之间的私语,不意间让她听了去。当时一个侍女一边整理夫人随身之物,一边对另一人道:“你知道茶茶小姐为何不和夫人一起进京?”
“茶茶小姐还没有被正式封为侧室。她若来了,就会受到和我们一样的待遇,她当然不愿意了。”
“呵呵呵,其实另有原因。”
“怎的?”
“听说茶茶小姐怀孕了。”
“哦?是大人的孩子?”
“是啊,可听说这里面还另有文章呢。”
“到底是怎回事?”
“这可是个大秘密,你听着。要是大人不答应,茶茶不会和夫人同行。”
“啊?”
“这不是茶茶小姐能想出来的,都是织田大人的主意。他对茶茶小姐被大人夺走一事咬牙切齿,才如此安排,想伺机把茶茶小姐夺回去。”
宁宁听到这里,穿过房问走进大政所房中。她心中并不平静。仅是带茶茶进京一事,就已让她很不快了,现茶茶又自作主张,不与她同行,也难怪她生气。宁宁陪大政所说了会儿话,回到了自己房中,命令女管家:有乐一到京城,就传他立刻过来。
夕阳照在崭新的屋瓦上。一刻半后,有乐来了。“夫人传唤,在下赶紧过来了。”他郑重地向宁宁施了一礼,眯眼打量着右边墙上一幅狩野永德的孔雀图,“哦,好画。像是在和北政所夫人斗妍。”
“有乐,你是说活孔雀在斗妍?”
“活孔雀?”
“呵呵,不就在你那里吗?你准备好地方安置那孔雀了吗?”
“这…………夫人说什么呢?”
“就是那只不知足否真怀了孕的孔雀啊。”
“哦,夫人…………”
“你当已决定怎么做了。哼!那只孔雀虽怀有关白大人的血脉,不过我会让你按你之意照顾她。”
宁宁这么一说,有乐生起戒心,思量起来。对于宁宁的要强和尖刻,他再清楚不过了。他知总有一日事情会曝露,已想好各种解释,但不知为何,就是说不出口。方才关于孔雀云云,宁宁就明显是在逼问。
“为何不说话?织田大人不是无论何时都能想出好主意吗?”
“在下惶恐。”
“哦?这可不像你啊。”
“这…………乃是关白大人的行为,实出在下意料。”
“哼!”宁宁冷笑一声,“你不是连关白吃了何物都知得一清二楚吗?”
“这…………其实在下以前并不知道。”
“你是说什么时候?”
“这…………这…………”
“是二月或三月,关白出征九州以前,对不对?”
“是。但在下那时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如何善后。你有心来和我商量,应早有对策。”
“在下只是半信半疑,尚未向夫人禀报。”
“有乐,你是否觉得关白比我好打发?”
“夫人。”
“你是否对关白说茶茶怀孕了?”
“不,那是…………”有乐额上已经冒出了一粒粒汗珠,“在下怎敢胡言?”他一直觉得,宁宁不过一介女流,要把她从秀吉身边赶走,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如今看来,他还是低估“女关白”了。秀吉还什么都没有对宁宁说,她便已抢先下手。“不是?便是说怀孕之事乃空穴来风?”
“那,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吞吞吐吐,婆婆妈妈!你是明知茶茶本未怀孕,而来欺骗关白?”
“北政所夫人…………”
“说!到底对关白说了些什么?茶茶为何不与我同行?”
“夫人。”有乐急着避开宁宁逼人的锋芒,“在下想跟您商量,到底应拿茶茶怎么办。在下早已方寸大乱。”这倒是有乐的真心话,不过也是一种巧妙的拖延。
宁宁看着有乐,嘴角露出冷笑。他此时还说不知如何是好,让她觉得既可疑又愤怒。也许传言并非毫无依据。难道有乐为了把茶茶从秀吉手中抢回,以致不顾一切?尽管如此,有乐称茶茶可能怀孕,却击中秀吉的命门,这是何等奸诈!宁宁也知这是最能控制秀吉之言。“有乐,接着说。”
“此事非常棘手。”
“是说怀孕的事?这事是茶茶自己说的,还是你的诡计?”
“在下坦白。这是在下束手无策之下,想出来的拙计。”
“为何你会束手无策?”
“因关白大人和夫人都说了要她一起上京,但茶茶不愿。”
“你无法说服茶茶,便去欺骗关白?”
“夫人,请您发发慈悲,此事万不可告诉关白。”
“关白定会知道,哼!你如此轻视关白,更是无礼!”
“夫人!”有乐忍不住叫了起来,跪伏在榻榻米上,“您要是这么说,有乐就无颜再在大人身边待下去了。请夫人发发慈悲,看在有乐一时糊涂才犯下大错的分上,原谅在下吧!”
宁宁一语不发,看着有乐。也许事情确如他所说。但这种传言令无法再生育的宁宁心中生疼。
“事实如此,有乐惶恐之至,无法说服茶茶,只好去哄一哄关白,这实是有乐一生中最大的错。”
宁宁渐渐觉得,虽然自己也很悲哀,而有乐的悲哀更甚于她。他虽是信长之弟,现在却要听命于秀吉,毫无主见,只能和其他侍从一样讨好主子。“我知道了。事已至此,你说该怎生是好?”
“夫人原谅有乐了?”
“我不再责怪你。但是,有乐,你难道不认为自己罪孽深重?”
“有乐追悔莫及。”
“好了。那么你想让茶茶住在哪里?”宁宁压抑着翻腾的情感,以事不关己般的语气道,“要是她来京城,你也得筑一个适合孔雀住的巢啊。”
“恐怕这要看关白大人的意思了,在下哪有什么看法。”有乐已一副完全屈服于宁宁之态。
“关白说,让她暂时留在我处,随后另作打算。”
“暂时留在夫人这里?”
“是,关白似也还未想好。”宁宁淡然道。她停止了追问。事到如今,再怎么责骂有乐也于事无补,能从有乐口中清楚知道怀孕一事是他的计划就够了。“有劳你了。迁居一事也让你颇费心。今日之事我不会放在心上。你也不用介意,去忙你的吧。”
“遵命,多谢夫人。”
有乐退下,宁宁陷入了沉思。事情并非有乐引起,而是秀吉所为。以往宁宁对秀吉的事都是一笑置之,可不知怎么,只有这次放不下,倒也不是不安,多少还出于嫉妒。为何他会对那样一个女子…………想一想,茶茶确实有着其他侧室都没有的禀赋,连宁宁都似有所不如。茶茶对一切都不介意,目中无人。其他侧室都对宁宁谦让几分,她却从茶茶身上感到一股压抑不住的邪气。难道是因为过了太长时间的平静生活,自己少了些锐气?
过人的眼光和才气,让宁宁平时也能反抗秀吉。可她总因自己的出身自卑。信长的外甥女、浅并长政的女儿、柴田胜家的继女…………茶茶任何一种身份,都是宁宁无法比的。宁宁竟对聚乐第产生了恐惧,想到将和茶茶一起住在这里,她便要疯了。
宁宁和秀吉面对面谈此事,是在把诸物从码头运到聚乐第的十八日晚。秀吉兴兴头头来到内庭,眯起眼睛,在夫人面前盘腿坐下,问道:“怎样?这屋子你还满意?”
宁宁微微一笑,低下头道:“我有事想问大人。”她把烛台挪近些,心想,今晚无论如何都要笑容满面,却感到脸颊在不自觉地抽搐。
“想问我…………为这房间作画的画师的名字?他可是号称海内第一画师的狩野永德。”秀吉敏锐地察觉到宁宁的意图,狡猾地岔开话题。
“海内第一有很多。”
“是啊。茶道是利休,茶具则数长次郎,鉴别刀剑首推本阿弥光二,还有歌舞…………各行各业的艺人工匠,都有看家本领。”
“谁的女人最多?”
“女人?”
“在日本国,谁的妻妾最多?”
“这个…………可能是家康吧。”
“哦?为何不是关白?”宁宁平静道。
秀吉眼睛滴溜溜打着转。虽然他从一开始就察觉到气氛不对,却没想到宁宁一面微笑,一面如此尖锐地诘问。“哈哈,你是否又听到什么传闻了?”
“无。”
“哈哈,还真有些无聊之言。说什么我要迎娶利休居士的女儿阿吟。”
“利休居士的女儿?”
“是啊。但这也不无道理。最近利休经常违抗我,出言不逊,说我固执己见。其实不过因为茶具。你也知,我要在聚乐第宴请天皇,也请天皇赏鉴长次郎烧制的茶器。利休说必须用黑色茶具,我不喜黑色,太无韵味。我说用红色,他却当着大家的面责难于我,说红色显得芜杂,黑色才高贵典雅,要我把茶会和茶具之事都交给他经管。”
“呵呵。”
“你别笑。于是我责他自满,生了蔑视关白的念头。当然这只是说笑罢了,我说若他不存二心,就让他的女儿阿吟来侍候我。马上便有人说我要利休交出女儿。说这种话的,也只有宗安或曾吕利了。”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