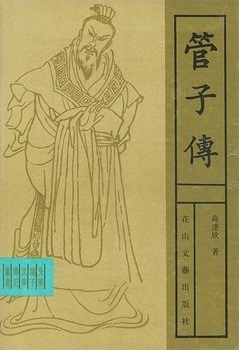曾有一些时日,本阿弥光悦在加贺做细瓷茶碗。
其父光二尚在世时,父子就从加贺的前田氏领二百石。光二去世后,前田利长和光悦约定,继续给他和其父同等待遇。因此,当他和本家发生不快时,就避到了金泽。虽然远离京城,光悦的心情却无法平静,许是积习,他为世间诸事担心,时时传进耳内的消息让他焦躁不已。利长有时会传他去,在闲话时向他打听些世事,以光悦的脾气,他自无法含糊。
“听说有马晴信和长崎奉行商议过后,烧了葡国船。”
听此一问,光悦心下一惊,之前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葡国人常是先派传教士去驯服当地人,再以武力征服。只要我们一出海,他们就派出海盗。有马的船便可能在什么地方被葡国人抢了。”
听了这些,光悦立刻去找高山右近。右近现被称为南坊,亦居于金泽。不料南坊对此竟甚是清楚,他说,此事恐是尼德兰或英吉利通过一浦按针之手,鼓动家康打击旧教。此若确实,日本国内不久就会发生南蛮人和红毛人之争…………
可南坊除了信奉“空寂茶”,决不染指其余诸事。为了坚守信奉,他才躲到茶室。他奉行“和敬清寂”的利休茶道,设置了一间四叠半大小的祈祷间,常为了一件茶器花费心力。在这种超脱的生活中,真正的茶道和信奉乃是唯一能安慰他的东西。他曾道:“利休居士若再活久些,或许会与禅断缘,而将洋教和茶道结合在一起。”照他看,业已故去的蒲生氏乡,以及现居大坂城内的织田有乐斋,从内心来说都已属洋教信徒;其他如牧村政治、芝山监物、古田织部、细川忠兴、濑田扫部等自然亦不必说,甚至前田利长也不例外。他甚至说:“只有心中有信,心才能真正静寂。”似是故意要避开世事。
与高山右近的此次相会,成为促使光悦回京的原因之一。
对于高山南坊所论,光悦心中自有分寸。南坊忠于信奉,这一点或许和本阿弥光悦甚为相似。他既自称是南坊、旧教教徒,就丝毫不会动摇对洋教的信奉。有关佛教和神道,尤其是和禅宗有关的东西,他一概听不进去。或许他曾遇到过自甘堕落的和尚,使得他彻底切断了与佛法的缘分。
我对日莲大圣人,恐亦无这般忠诚啊----光悦马上开始反省,脸稍稍有些泛红。
信奉可使人安心,也会致人盲目。盲目的信奉会沦为迷信,终将给信奉者带来痛苦。一个拥有如此虔诚信奉之人,若感到宗派之危,他会怎生做?
假如大御所说要消灭日莲宗,光悦能够袖手旁观吗?当然不能!南坊等众多洋教徒肯定认为,乃是三浦按针给他们招来了危机,自然不会听之任之。想清楚这些,光悦方从加贺动身。
洋教新旧两派的对立,很可能把众多日本人卷入***。仔细想想,和光刹之争,实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人应有更高的追求。想及此,光悦立刻去拜见利长,告诉他,自己想回京城住。利长大为赞成,他助光悦生计,是想自光悦那里获得京城的消息,绝非要留他在身边服侍。
当光悦离开加贺,抵达京城时,已是庆长十五年入夏。
“好久不见了!长期住在京城的人,住不惯乡下。”光悦去拜访舅父光刹时,道。
光刹将一个精美的绿色小盒变给了光悦,称是武州八王子的阿幸托他转交,还说,他正要写信去加贺。
“阿幸给我的?”光悦有些恍惚地看着盒子。
“光悦,其实阿幸有一封书函和这盒子一起送来,那书函让人有些担心,我就翻了翻盒子,但里边什么也没有。”
光刹乃是日莲宗信徒,以世俗之人眼光看来,他绝非不洁之人。但听说翻过寄给自己的东西,光悦有些不快,他忍住,道:“信函上写了些什么?”
“说是信送到时,她或许已不在世上,故请把信送到的日子当成她的忌日。此外,绝不要到大久保府上去问,若非如此,恐给我们家带来麻烦。你也知,阿幸不争气,把她供在家里倒罢了,到了外边,真不知她还会做出何等事来。”性子刚烈的光刹抚弄着花白的鬓角,“故,请你把此事忘掉。我也未对姐姐说起过。”他口中的姐姐,便是留在京城的光悦之母妙秀。
光悦无语退下。
那小盒子端端正正收于杉木盒中,用颇旧的红锦缎包着。光悦捧着它,到了母亲曾住过的通出水下町茶屋别苑。当日,他只是把盒子放到架上,不想打开。
茶屋主人此时去长崎公干,不在家,光悦悻悻而归。灰屋绍益、角仓素庵和俵屋宗达等人得知光悦回京,便来拜谒。大家叙完旧散去,所司代板仓胜重又来了,和光悦聊了很久,故光悦根本无暇思量阿幸之事。不过,他还是若无其事向胜重问了问长安的情况。
胜重若无其事道:“石见守运道甚强,听说今春中风倒下,我以为他会就此隐退,不料他很快就恢复如初,又在甲州黑川谷挖金山了。”接着,胜重降低声音,提了两句长崎港烧毁葡国船只之事,不过和光悦在加贺听到的大相径庭。加贺那边的说法是:有马晴信为了报复,才烧了葡国船只。可胜重说,放火的人并非有马晴信,而是那洋船的船长。
“其实,有马的船上载了许多兵器,那洋船在受袭击前,似已着火了。”板仓胜重顿一下,又道,“看来,这样还不能消除大久保石见守和此事有牵连的传言啊。”
“长安与此事有牵连?”光悦吃了一惊。
“长安似提议过,若将日本的兵器卖到海外,定会大受欢迎,可大赚一笔。可是,如先生所知,如今的欧罗巴分成了两半,双方战得正酣。我也相信日本的兵器一定会受一些人欢迎,然而无论兵器落入何方之手,南蛮和红毛之间都得出大事。天竺、爪哇、马来,以及吕宋和香料岛,处处都剑拔弩张。因此,班国国主密令葡国船袭击载满兵器的日本船,不只是抢夺货物,还要把船弄沉,杀死所有船员。故有马怒气冲天。然而葡国并不希望自己夺来的兵器,再通过日本人落入敌手,那样之前就是白费力气,故他们自己把船烧掉,把货物统统扔到海里。我想,这些话还是莫要传进大御所耳内为好…………”
家康主张和平交易,出口兵器自会引起海外骚乱,他必不容。葡国人把船烧了,使得长崎奉行和有马晴信均狼狈不堪。
“据说,船上还有生丝。他们载了很多生丝来,其实乃是从日本船上夺来,再卖给日本。这事被我们知道,他们就忙把船烧了。”胜重非常清楚光悦的性情,故,甚至连“莫要禀报给家康”的话也挑明说了。
“可在下还有不明之处。”
“何处不明?”
“葡国船只强夺日本兵器,这个在下明白。这对葡国人而言,亦为大事一件,若兵器落入敌手,自大不利。可他们为何把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兵器又运到日本?又为何要进到危险的长崎港?这一点,在下无法理解。”
“是啊!”胜重蹙眉摇首,“我也疑惑,可世间的传言更离奇。”
“传言?”
“说是班国和葡国已无可避免地要在日本与红毛开战。大御所和将军都被三浦按针瞒骗,已大大支持新教。因此,旧教信徒要把足够的兵器运进大坂,以此为据点,拼死一战。他们运送兵器到长崎,由于有马晴信强烈反对,故又慌慌张张把船烧了。如此一来,就把大久保长安和丰臣秀赖都卷了进去。这个传言可真是来势凶猛啊!”
本阿弥光悦屏住呼吸,看着板仓胜重,其实他也这般想过。
“如此说来,葡国船乃是打算把从日本船上夺去的兵器运回日本,存放于大坂城?”半晌,光悦才道。
胜重忙摇手阻止光悦,“唉,我可未说必是如此,只是这种传言让人很是头痛。”
“唔,这么说,大坂城里有人想与葡国班国结盟,与看似更支持尼德兰和英吉利的大御所一战?”
“是啊!总会有虔诚的洋教徒,那些人被葡国传教士一鼓动,难免这般想。真是麻烦啊!”
“经常出入大坂城的传教士究竟是何入?”
“我也不瞒你了,便是保罗神父。而且,大坂城内的重臣怕都和那神父有些关系。”
“何样的关系?”
“不是信徒,就是后援!织田有乐斋、片桐市正,以及明石扫部、速水甲斐守等,无一例外。有些人想隐瞒此事,就热心建议淀夫人再建大佛殿,暗地里却想把大坂城变成洋教旧教据点…………。嗯,还有传闻说,有一个比斯卡伊诺将军今年要来日本,为去年送回前吕宋总督罗德里格的事道谢。人言可畏啊!若大坂城成了南蛮人的据点,班国国君必不断派出载有大炮的军船到日本来。这不只是谣言,听说此乃南蛮人的惯用伎俩。只是我不会胡乱相信谣言。”
本阿弥光悦甚是清楚板仓胜重的为人。胜重绝非轻信之人,但谣言肯定让他心惊。
“其实,你回到京城,我也松了一口气。不管是茶屋还是角仓与市,都尊你为人生之师。他们若对你说了什么,请一定告诉我。”
胜重言罢,告辞去了。光悦茫然坐了许久,才想起阿幸送来的绿色小盒子,难道里边真藏着什么?
打开来,小盒子是空的,可在耳边摇一摇,就能听到轻微的纸张窸窣声----盒子有两层!光悦小心翼翼检查时,涂满金粉的内盒悄无声息开了。
“啊,果然如此!”
盒中整齐叠放着光悦曾见过的宗达函纸。每张上都密密麻麻写着小字,落了日子。有的纸上还写着“光悦先生亲启”。光悦静静读着。渐渐地,他脸红了,各种情绪令五内翻腾。信中,阿幸毫不掩饰地说起对光悦的情意,感伤流露无遗。她说,她对光悦一往情深,这让性情严谨的光悦几不敢相信。可是他亦感到,阿幸对他大有深意,是一种对骨肉至亲般的依恋之情。总之,正如光悦所想,阿幸并未真正倾心于大久保长安。这个女人的宿命,无比痛彻地流露于字里行间。
光悦花了一个多时辰才读完这些文字。他冷静地思虑着阿幸到底想说什么。对阿幸所言,他并不特别惊讶先前见过板仓胜重,他心中已生出种种猜测。
阿幸在信函中说,由于与政宗发生龃龉,长安方才感到政宗的重要。过去,政宗的支持令他得意忘形;可政宗一旦弃他不顾,他便危在旦夕。
不管怎么说,大御所和将军对政宗另眼相看,何况他还是忠辉的岳父。若政宗对大御所和将军进言,说长安对忠辉毫无益处,长安便可能掉脑袋。政宗变卦之前,长安几未想过此事。
阿幸明言写道:如此一来,最麻烦的乃是联名状,第二便是那些积存的黄金。
光悦寻思,金子产量,完全由长安根据自己的目的安排,问题在于,家康和秀忠对长安究竟有多信任?即使长安乃是为国积财,若引起怀疑,必招致大祸。光凭他那奢糜的生活,就足以令那些仅靠米谷收入过活、口子节俭的大名争而毁之。
长安假装中风不起,欲在此期间把黄金埋藏于黑川谷,等日后再重新挖掘。一旦有急用,黄金随时都可起出;而万一事情败露,八王子的宅子被抄,家中并无多少金银,那便是瞒天过海之计。
阿幸说,知道内情,让她身置险境。长安真正信任的只有阿幸,若知事情败露,他想要杀人灭口,第一个目标便是阿幸。她估计,也许很快就会被带到黑川谷,秘密除掉,若光悦可怜她,希望他能到黑川谷一趟。她甚至说,自己的血可以使那一带的杜鹃开出黑色的花…………
光悦颇为了解阿幸,她从不肯服输,喜戏弄人。因此,对于阿幸的伤感,他并不那般担心。不过,阿幸信中有一段说,长安让她做了另外一个盒子,里边藏有联名状,不知被藏到了什么地方。若是寻常人,恐早已把这种东西烧了个干净,可长安不会。他野心勃勃,欲留名青史,这不仅出于他的虚荣,亦出于自卑----我长安不仅能当个山师与猿乐师!
想及此,光悦愈觉不安,他想起板仓胜重所言,长安似与烧葡国船只之事有关。难道长安装病,不单是为了藏匿黄金,亦是暗中把兵器藏到大坂城?如此想虽匪夷所思,然长安和寻常人不同,他要正大光明出海,因此,恐欲接近出入大坂城的神父。
此事可不能置之不理!到这时,光悦才兴起给阿幸回函的念头。他未提收到绿色小盒一事,只是把自己的意思隐于字里行间,写道:“长安近日开始做生意,可能有些奇妙的故事,希望能陆陆续续说给我听。”
刚封好信函,下人禀报,又有客人来访。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