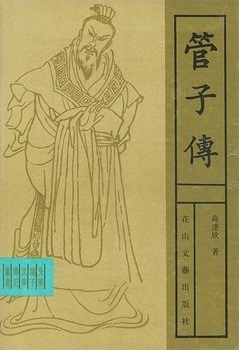第十二回 通脱深美
1.狂者机趣
阳明贬低傲,却赞美狂,他现在已不会有浅层次的自相矛盾了,也就是说狂和傲在他这里是不相连属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傲,是什么都不信,是可怜的自以为是;狂,是大信,信仰超迈现实的更高的价值世界。大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些嫉妒他的阁臣是傲,而他原先是狂,现在则连狂也超越了。他现在常爱标举的意象便是凤凰翔千仞之上,既是自期也是自诩。无论是什么,这个感觉都不坏。
他自知他的狂是他获谤遭忌的原因,但他反省到过去有乡愿的意思,也不能与官僚系统和谐,所以干脆来个直以良知而行,纵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依良知而行。但他总是不厌其地告诫学生必须“除却轻傲”。轻傲是狂的末路,是狂的堕落形态。狂,志存古道,是有理想的英雄主义。傲则是变态自尊,傻乎乎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邹守益自我总结获贬谪“只缘轻傲二字”,阳明马上鼓励他:“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
康德说,除非我愿意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么做。阳明的致良知就是要在行事时找到普遍的道德法则。但他知道依良知也依然不免受毁谤,用他的话说就是圣人也免不了。因为“毁誉在外的,如何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也有轻官重道的人,绍兴知府南大吉,年岁地位都不轻了,近狂而不傲,听说了王学的宗旨,便来当门生。他性豪旷不拘小节,有悟性。一次,他反问王:“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王说“何过?”大吉一一数落,王说“我言之矣”。
南问“何?”王说“我不言何以知之?”南说“良知”。王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
过了几天,南又来忏悔,觉得自己的错误更多了。王说:“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
正因为他忙于入圣,而疏漏了官场规则,考查时被人挑剔,但他给阳明的信只字不提这一套,还是请教如何自新。只以“不得为圣人为忧”。阳明大为感动,让学生传阅他的信,并在回信中相当全面的给他讲了良知的本性:
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浴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 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源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 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
总而言之,良知比上帝更万能,但王也说惟有有道之士,才能见良知本体。
这个南大吉成了王门的功臣,在本年即嘉靖三年,他开辟来稽山书院。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南让山阴县令“拓书院而一新之”,为了让老师来讲学,也为了尊经明道,南很快就王学化了,他认为:“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匿矣。”这年十月,南又辑录了老师的论学书两卷,与薛侃在赣州刻的三卷合成五卷本的《传习录》,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答聂豹「文蔚」》第一书。其实在封信对于已熟识王学的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简练地概括了王的主要想法而已。王在结尾处说:现在“良朋日集,道义日新。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说明王的确很快乐,获大自在。
这个聂豹,《明史》说他是“倾狡之徒”。他是王在江西时,从远处遥望过大师一次,后来到山阴来问过学,但没有入王门。在阳明死后四年,他这个苏州知府,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应该归功于王学,才对着王的木牌,磕头拜师傅。他后来也成为王学后劲中的一派。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王学在王身后的势力。
还有一个六十八岁的民间诗人,来游会稽山水,听了阳明的讲座,就不走了,强拜阳明为师,他问的问题,颇好玩,如帮他弟弟贩粮食,陪了老本,连累了许多人,他认为是自己不老实之过。王答,认识到不老实是致良知的结果,否则,“却恐所谓老实者,正是老实不好也。”但一个将近七十的人,因听到了一直想听而听不到的声音就真诚的当学生,诚如阳明所说,是大勇者。阳明为他写了一篇《从吾道人记》。诗集中有四首与他唱和的诗,说他头发虽白人并不老,“赤子依然浑沌心”,从吾道后已得意忘言,“不是当年只苦吟”。
2.美学天地
阳明在学生的包围中,恢复了诗人的本色,他的守丧期已过,现在是嘉靖三年八月了,中秋节,他在越城区中的天泉桥的碧霞池上设宴让学生会餐。有百十名学生“侍坐”,就象《论语.侍坐章》所描绘的气象一样,只是王这里有酒肉,规模--学生人数也比孔子当年大多了「当然人口总数也大多了」。酒喝得半酣,歌咏声起。人们都敞开了性子,“自由”活动起来,有的投壶,有的击鼓,有的泛舟。阳明心中很舒坦,找到了天人合一的意境,欣然吟出“道”在言说、或者说言成道身的《月夜二首》,用月来喻人,月光喻人的自性--良知,外在的闻见道理便象是遮月的云雾。云雾不碍月体的自性明亮,去掉云雾,月光又会重放光明。他告诫人们要守住自性,莫辜负只有一次的人生,千万不能象汉学家、理学家那样去做制造云雾的工作,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说蒙胧影响的糊涂话,从而死不见道。他想到的合适的人格类型是那位在《侍坐章》说自己的志向就是在春风中游泳唱歌的曾点:“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曾点运用的是意象表达法,用一种生活场面体现出一种生命风格、精神境界,因为当时孔子既不赞同颜回的、也不赞同子路的,却“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居然赞同这个逍遥派的志向,引起后世儒者的百般解释。有的说这是天下归仁、家帮无怨的大同境象,有的说这是天人合德的逍遥气象,等等。阳明复述这一“故事”有以孔子子况之意,孔子的风格就是淡薄宁静、“无可无不可”,既不枉道求荣、降治辱身,也不隐居放言,只是从容中道。阳明认取的只是这个。
第二天,学生来感谢老师。阳明注解性地全面地阐发了自己的意思:当年孔子在陈,想念鲁国的狂士。因为狂士不象世上的学者那样陷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我接受孔子的教义,脱落俗缘,「所以我赞同曾点」。但是人们若止于此,“不加实践以入精微”,则会生出轻灭世故,忽略人伦物理的毛病,虽与那些庸庸琐琐者不同,但都一样是没得了道。我过去怕你们悟不到此,现在你们幸而见识到此地步,则正好精诣力造,以求于至道。千万不要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
阳明已达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的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境界,在动态中达到正好、恰好「“时中”」。有个学生要到深山中静养以获得超越,阳明说:“君子养心之学,如良医治病,随其虚实寒热斟酌补泄之,是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专欲入坐穷山,绝世故,屏思虑,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他的方法论吸取了佛法的精华,但价值观力拒佛教之遗弃现世的态度。他的方法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则是突出个“超”字。进取超越,是他的基本心态,超迈所有的既成体系是他的基本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的体系是超实用而实用,超道德而道德,类似康德说的那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纯粹美。
苛刻的说,阳明的理论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心即理,吾性俱足,有孟子的性善论、陆九渊和禅宗的明心见性。致良知,有《孟子》《大学》《中庸》的同类表述。将我心与天理能合起来的道理则有儒、释、道三家共同的“万物一体”学说。他是自由地在儒释道三家通用的走廊上取我所需的酿造着心学之蜜「秘」。公开地说:“圣学,心学也。”为心学正名,也表示自己高举圣学的大旗,然后在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这也是他被规矩儒者认为狂的一个原因。
凡是发展了正统的没有一个不是被当时指为狂或邪的。***将这个总结为必须“反潮流”。 狂者必简,化约主义是东方哲学的特色,要从东方哲学中找一个化约的典型、榜样,那便是阳明学。他一路提炼过来,最后只有“致良知”三字真经,他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有点后来泰州学派那种傻乐呵的劲头了「如他们的《乐学歌。」,倒是很好的总结了良知学的大意: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面目,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重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3.家庭难题
关于他的家庭生活始终是只见天伦--父子,而没有人伦--夫妻的生活内容。这是不对头的,但业无可如何。正路的资料相当少,间或有些杂撰的记载也多不可信。今年,他五十四岁了,跟着他耽惊受怕的诸夫人驾鹤西游了。她是乎一直住在老家山阴,这也是常有的现象,因为有公婆,媳妇的主要责任就是侍候老人。阳明在外面没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外室,否则早有孩子了。用封建的观点说,诸氏很不合格、很不称职,到死前也没给王家生出个后代。但是王阳明对她很好,她母亲过生日,他还让人画蕃桃,自己配上诗,题序上表示平日不能尽孝的歉意。要说是诸不育吧,守仁弟兄四个在守仁四十四岁时,还都没生孩子。若说是王的问题罢,诸氏死后,续娶了张氏,就在他五十五岁时,即嘉靖五年,生了一个儿子。
他四十四时,因为没有儿子,而且诸氏也没可能生产了,遂由龙山公作主,过继了守仁堂弟守信的儿子,名正宪,字仲肃,过继时已经八岁。阳明常年在外,便委托他的学生给正宪当家教,但这个儿子没找到自己的良知,不但一直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与他弟弟,阳明的亲生儿子处理好关系。阳明死前已有防备,他死后,他的学生在“太夫人”即阳明的继母的主持下,立即给他们分了家。
在正德十六年,因阳明平赣南土匪的功劳,赏赐了正宪一个锦衣卫副千户,实授百户。赏赐的过程极为别扭,王辞了一下,事实上也没马上落实。折腾了好几次,一会儿说已提拨了阳明,还赏银四十两,就算了。有的人说赏不酬功,再为之争取。最后才在正德十六年落实了。还让正宪去锦衣卫赴任。最后,正宪也就是靠这个过着贵族后裔的生活。尤其是在隆庆年间,重新评价、嘉奖阳明时,他子以父贵,风光了一气。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