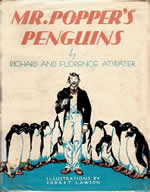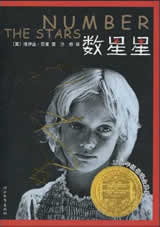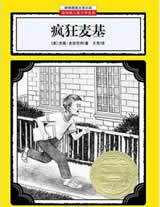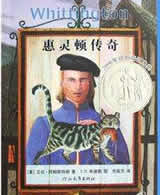入巴黎大学不久,傅雷与刘抗住到了巴黎郊外Nogent Sur Marne一个家庭宿舍。傅雷并不直接从事艺术实践,但他对音乐和文学有良好的修养,刘抗学的是绘画,常有创作活动,俩人朝夕相处,就能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刘抗因了傅雷,在音乐和文学知识方面获益良多;傅雷也由于刘抗的影响,引起了更大的艺术兴趣。他们相偕巡回于各种艺术馆所和画廊之间,观摩着名家们的杰作。也常去歌剧院、音乐厅,欣赏美妙的演出。俩人去得最多的是卢佛尔艺术博物馆。
海粟夫妇是1929年3月中旬到达巴黎的。来后不久,就请傅雷每天上午去教他们学一习一法语。法语比较难学,起初,他们有点儿学不进去。傅雷是尽义务的,教多教少,教快教慢,本可以由着刘海粟夫妇俩的兴致。他却非常认真,执意要他们非学好不可。傅雷诚恳与认真的态度,很使刘海粟夫妇肃然起敬。傅雷与他们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当时,傅雷正在跟一位名叫玛德琳的法国女郎热恋。
来法国之前,傅雷母亲已为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那并非纯属“父母一之命,媒的之言”,傅雷与朱梅馥原系青梅竹马,俩人早就相一爱一了。在来法一年之后,傅雷感情上却有了动荡。
目击者刘海粟、刘抗等人,在回忆文章中,对傅雷这次一爱一情波折的情景,有过详细的叙述——
开始是法国女郎玛德琳比较主动。这位女郎会弹会唱,略通绘画,喜欢探讨艺术,但理解上并不深刻。傅雷的人品、学问,很使玛德琳倾倒;年轻的傅雷,穿着当时艺术家流行的服装,打着花式领结,留着长长的头发,昂首天外的神态,颇有中西合壁的风度,更使玛德琳这位西方女郎所迷醉。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有如地中海的海水一样碧蓝,与傅雷谈起话来,就像赛纳河中的流水声响喁喁不绝。俩人频繁接触当中,感情逐渐炽一热起来。尽管傅雷早就一爱一上了朱梅馥,但现在面对有着共同一爱一好的玛德琳,他觉得,这位迷人的法国女郎,要比表妹可一爱一多了。
傅雷与刘海粟相识时,早已和玛德琳形影不离。刘海粟夫人张韵士见此情景,曾诧异地问刘海粟:“傅雷见了生人那样腼腆,一个一浪一漫的法国女郎,怎么会看中这位文弱的东方青年呢?从气质与禀一性一方面看,他俩怎么也不相配啊!”
刘海粟说;“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风一流的巴黎少女就觉得新鲜有趣。”
刘海粟这样说过后,有点儿后悔,总觉得虽在妻子面前,也不该道朋友之短。不过,傅雷当时坠入情网失魂落魄的情景,也着实使朋友们耽心呢。
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傅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是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解除婚约。但他没有勇气自己去发出这样的信,他把信件一交一给了刘海粟,要他代为寄出。刚把信件一交一给了刘海粟,又旋即要回,在上面加了这样一句:“儿在异国已有意中人。”过了一会儿,又要求涂掉这句话。
刘海粟觉得,傅雷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是在用理想的漆,涂到玛德琳身上,让她通体发出光辉,促使自己狂一热地去一爱一她。这样做,在此时此地的傅雷,或许是情理中事。但正如俗话所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作为旁观者,刘海粟在年龄上也要比傅雷大十多岁,对这类事的后果,毕竟看得清楚一些。提倡或者反对寻找异国配偶,他以为都是没有必要的。但又觉得,这位巴黎小一姐,未必就能远涉重洋嫁给一个中国穷书生吧!正处于热恋中的傅雷,他的种种判断,并不是很理智的。作为朋友,对他这件事,就该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
看完傅雷给他母亲的信,刘海粟一一夜未能入睡。他反复考虑着:傅雷与玛德琳的恋一爱一,好像热情似火,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只不过是一般恋一爱一期中年轻人所常有的那种冲动罢了。如果真按照傅雷的想法去做,对他母亲与梅馥姑一娘一的打击实在太重了。想到这些,刘海粟决定;将傅雷的信件压下来不予寄出。
隔了一天,傅雷就来追问刘海粟:“信寄出没有?”
刘海粟怕他纠缠,回答说:“已经寄走了!”
傅雷一怔,没再说话,颓唐地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傅雷向刘海粟提到:“一直没有收到母亲的复信,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话间,显得六神无主的样子。
刘海粟还 是对他说:“信早就寄走了。”
张韵士见状,问刘海粟:“傅雷究竟怎么了?”
刘海粟说:“谁知道呢?再让他写下去,还 不把他母亲气死了!”
一天,玛德琳突然来到刘海粟住处,告诉他傅雷企图自一杀的消息。还 说:“他变得反复无常,一会儿搂着我亲一热,一会儿又说我害了他。你们快去劝劝他吧!”
玛德琳对傅雷是很迷恋的,称他为“傻孩子”,自然不愿意他去寻什么短见。
刘海粟夫妇一听,事情怕要闹大,于是立即赶去劝说。到那里一看,傅雷正和玛德琳亲一热呢。
就这样一热一冷地过了几个月。大概是由于一边热情似火,披肝沥胆。另一边却意马心猿,别有怀抱吧,俩人始终唱不出一曲合一欢调来。傅雷陷入了极度失望之中。最后,这对一度热恋过的情侣,终于闹到非分手不可的地步。在刘海粟、刘抗看来这本是意料中的事。
导致傅、玛感情破裂的表面原因是,傅雷觉得玛德琳对他不忠实,更深的原因是中西两种道德观伦理观的尖锐冲突。很显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的中国青年,能够接受西方女郎火一样的热情,却未必能够容受她们在感情上的轻率与自一由放任。这也许是东方青年,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异国姑一娘一恋一爱一中最难接受,却又是一种最现实的存在。
这天,旅馆老板一娘一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刘海粟:“你的朋友来了,手里拿着一支槍,看来火气很大……”
傅雷气冲冲地走进刘海粟的住房,只见他面色苍白,两颊下陷,将手槍往桌子上一撂,气得说不出话来。
刘海粟没有立即从桌子上将手槍取走,耽心傅雷抢夺中发生意外。他一温一和地同他讲话,细问着原因。说话中间,刘海粟向张韵士使使眼色,暗示她赶快把桌子上的手槍收起来。
“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玛德琳好像又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随她去好了,不用生这么大的气!”
“不能!我大痛苦了!”
那天,刘抗也在刘海粟家里。俩人商量后,由刘抗去把玛德琳叫来,进行一番劝说。他们的想法是:即使一爱一情破裂,友谊应当存在;不能由冤家变成了仇家。玛德琳来到以后,傅雷又和她吵闹了一阵。一个哭着,一个流着眼泪,俩人都没有和好如初的诚意。
刘海粟和刘抗从旁观察,发现这对年轻人之间,虽不能说没有感情,但更有强烈的个一性一冲突,在阻隔着他们,和好如初的可能一性一已经不大了。
劝说无效,刘海粟夫妇和刘抗陪着他们一起去吃了饭、喝了咖啡。从饭馆中出来,傅雷和玛德琳各奔东西了
玛德琳离去以后,刘海粟夫妇又拉着傅雷到塞纳河畔去散步,继续劝说和安慰着他。
刘海粟坦率和诚恳地对他说:“难道你就为她活着吗?这又何苦呢?当初是她追你的,你尽可以处之泰然。再说,建筑在沙滩上的一爱一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基础,崩溃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说,这种没有前途的一爱一情,被一浪一涛冲毁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何必自找许多无价值的痛苦,妨害身心和事业呢?”
开始,傅雷还 在用一爱一恨一交一加的口吻呼喊着玛德琳的名字,慢慢地,他的情绪平复安定了下来。他道出了使他痛苦不堪的症结所在。他说:“我是在自讨苦吃,谁也不怨,们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一杀,只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还 活得成么?”
“傅先生,你别着急,当时海粟并没有……”张韵士想说那封信并没有寄走,但又犹豫起来,用询问的目光凝视着刘海粟。
刘海粟说:“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吗?”说话中间,把出门前揣在怀中的那封信掏了出来:喏,你的信在这里,当初我就没给你寄出去。”
傅雷接过信件,激动地感谢着刘海粟的考虑周详。并表示不能辜负了海粟的一片苦心与热忱,从今以后,他要与朱梅馥永远在一起。接着,他又痛哭着说:“我究竟写了这么一封信啊,我对不起她们!”
更新于:14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