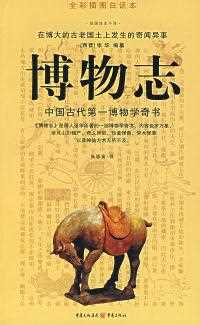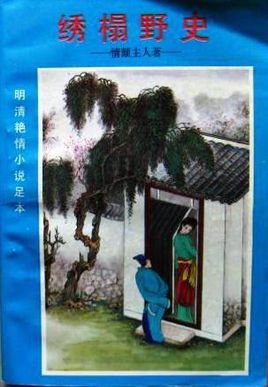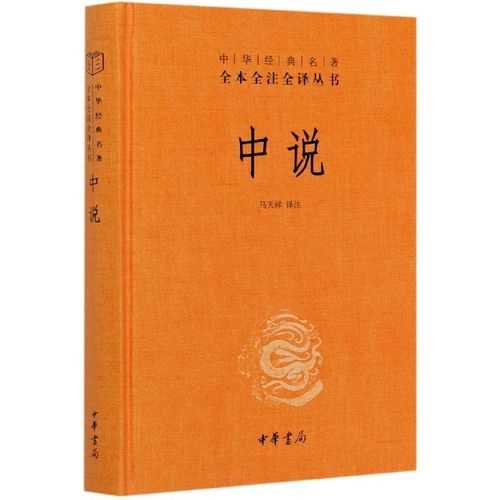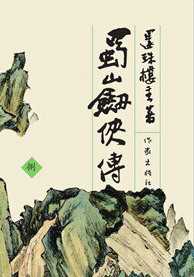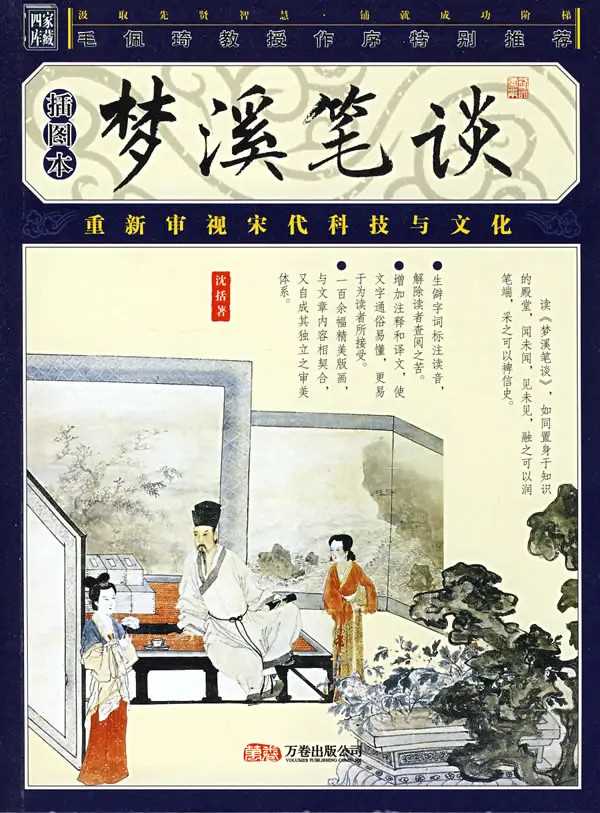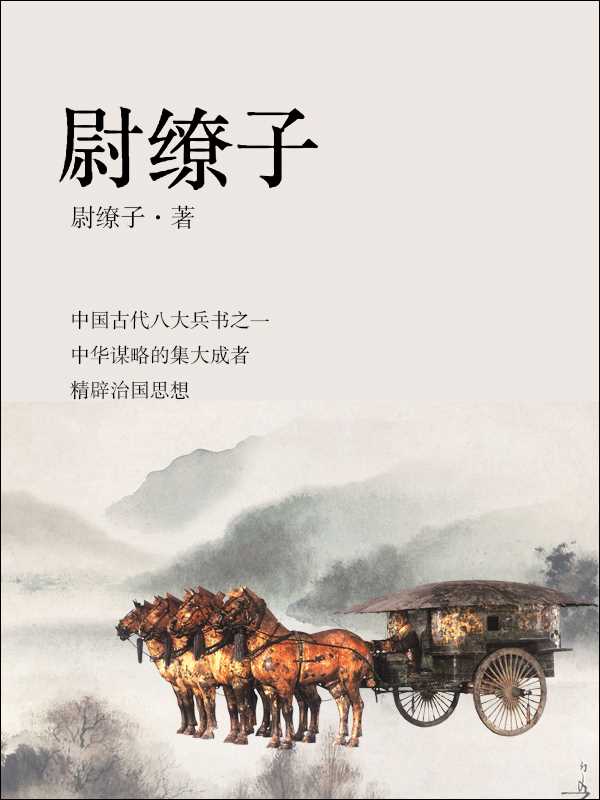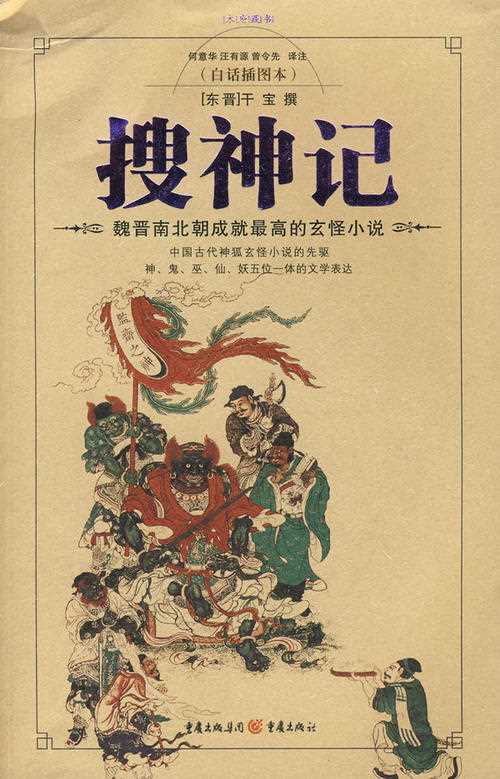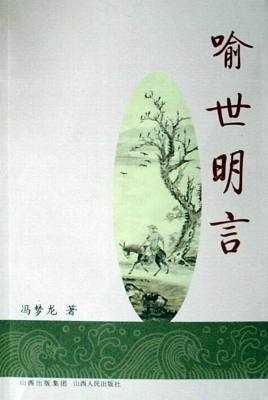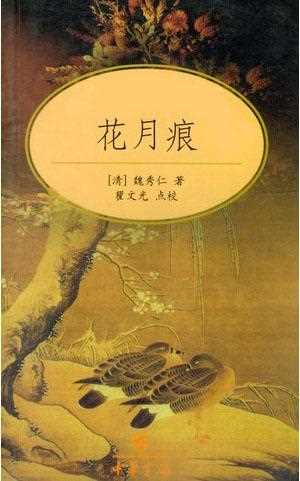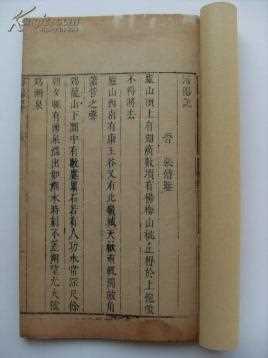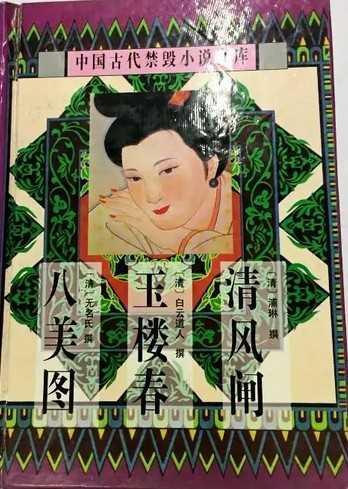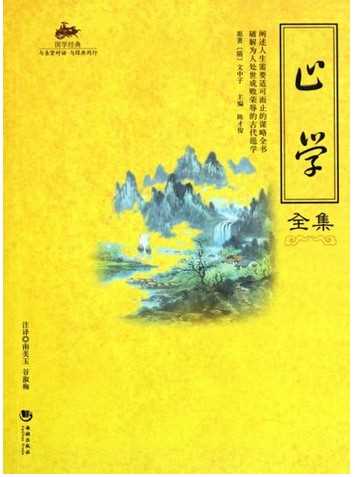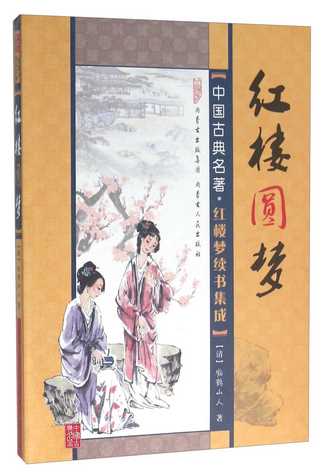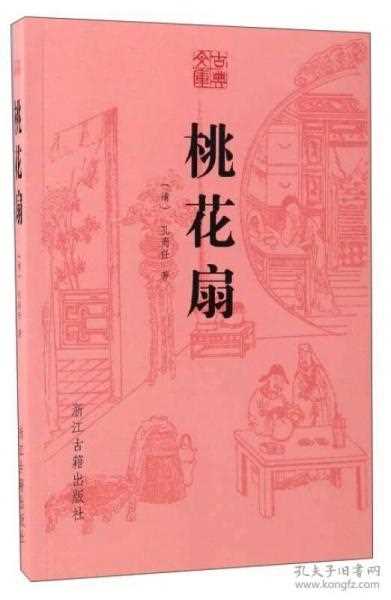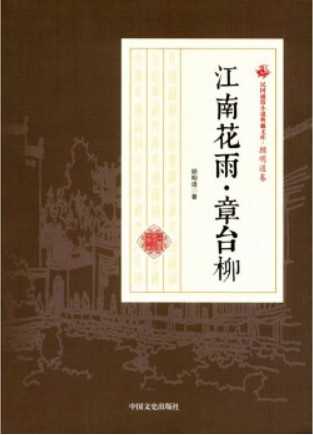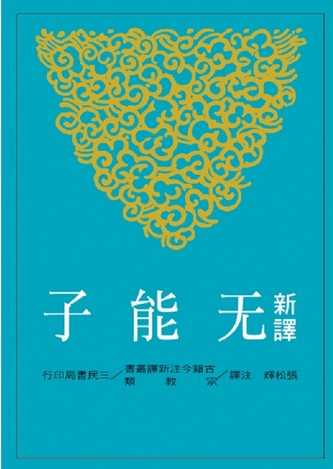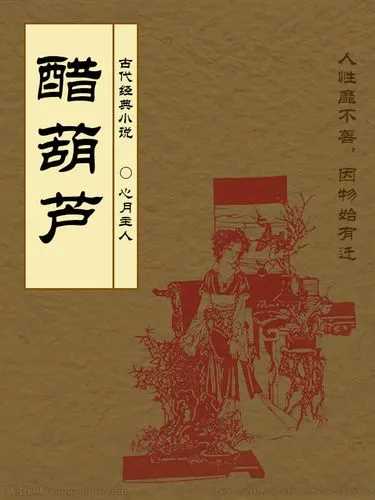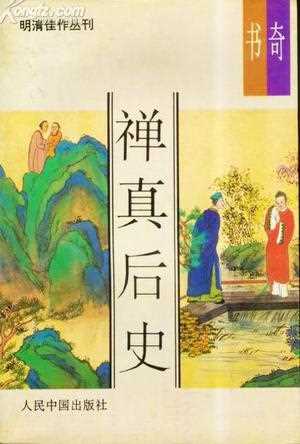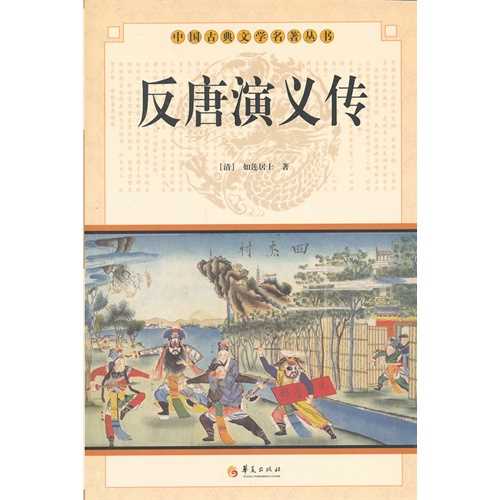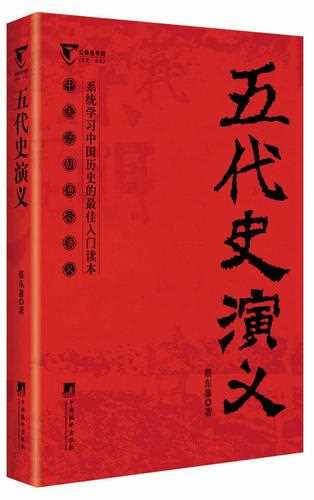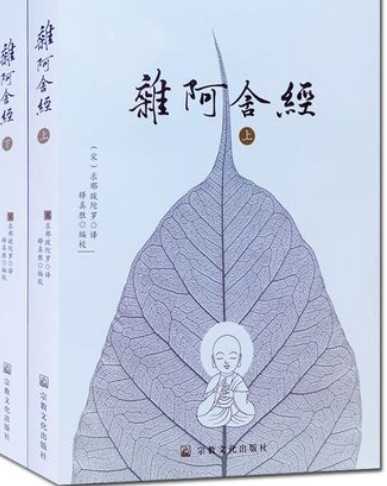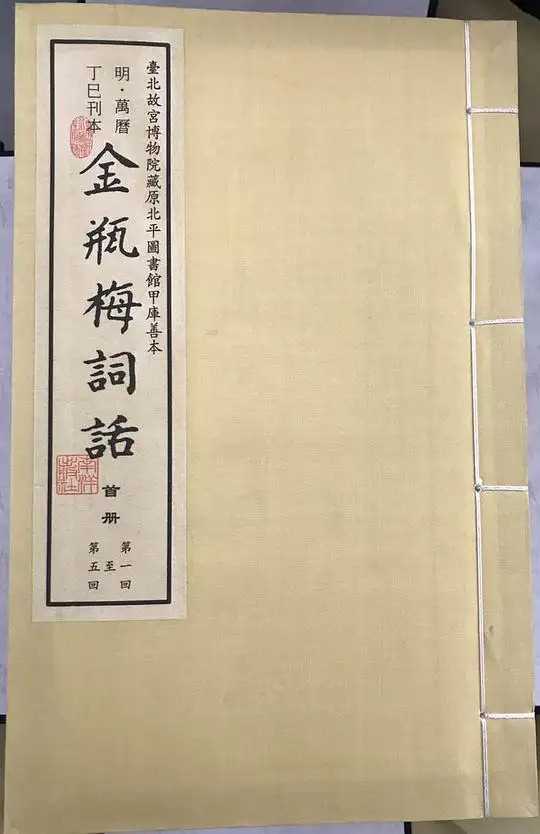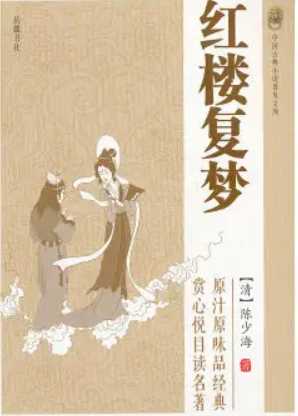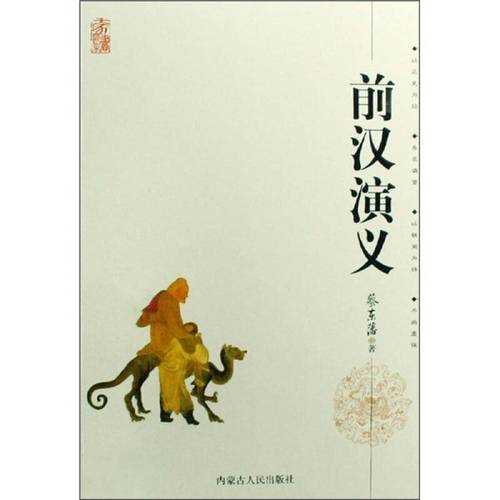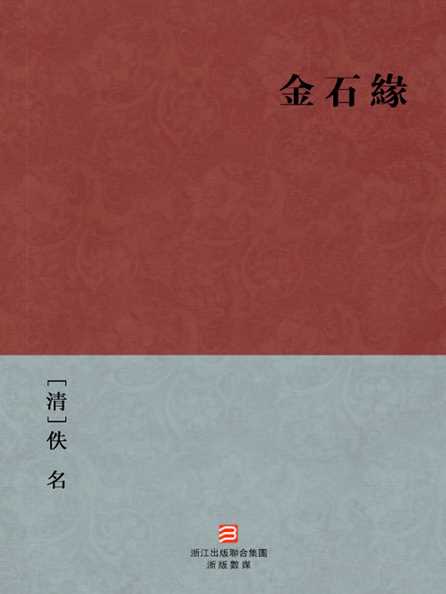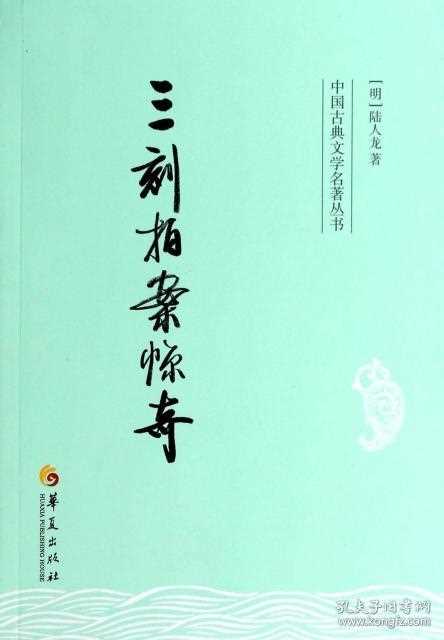「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
世味怜方好,人情淡最长;
因人成事业,避难遇豪强,
今日峥嵘贵,他年身必殃。」
话说一日周守备,济南府知府张叔夜,领人马征剿梁山泊,贼王宋江三十六人,万余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复。表奏,朝廷大喜。加升张叔夜为都御史,山东安抚大使。升守备周秀为济南兵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盗贼。部下从征有功人员,各升一级,军门带得经济名字,升为参谋之职,月给米二石,冠带荣身。守备至十月中旬,领了勅书,率领人马来家。先使人来报与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满心欢喜,使陈经济与张胜、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厅上排设酒筵,庆官贺喜。官员人等,来拜贺送礼者,不计其数。守备下马,进入后堂。春梅、孙二娘接着,参拜已毕。陈经济换了衣巾,就穿大红员领,头戴冠帽,脚穿皁靴,束着角带,和新妇葛氏两口儿拜见。守备见好个女子,赏了一套衣服,十两银子打头面,不在话下。晚夕春梅和守备在房中饮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务:「又娶我兄弟媳妇,费许多东西。」守备道:「阿呀!你止这个兄弟投奔你来,无个妻室,不成个前程道理!就使费了几两银子,不曾为了别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挣了这个前程,足以荣身勾了!」守备道:「朝廷旨意下来,不日我往济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点些本钱,教他搭个主管,做些大小买卖。三五日教他下去查帐目一遭,转得些利钱来,也勾他搅计。」春梅道:「你说的也是。」两个晚夕,夫妻同欢,不必细述。在家只住了十个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时分,守备收拾起身,带领张胜、李安,前去济南到任,留周仁、周义看家。陈经济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经济商议:「守备教你如此这般,河下寻些买卖,搭个主管,觅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费用。」这经济听言,满心欢喜。一日,正打街前行走,寻觅主管伙计。也是合当有事,不料撞遇旧时朋友陆二哥陆秉义,作揖说:「哥,怎的一向不见?」这经济便把亡妻为事,被杨光彦那厮拐了我半船货物,坑陷的我一贫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备府中,又娶了亲事,升做参谋,冠带荣身。如今要寻个伙计,做些买卖,一地里没寻处。陆秉义道:「杨光彦那厮拐了你货物,如今搭了个姓谢的做伙计,在临清马头上谢家大酒楼上,开了一座大酒店。又收钱放债,与四方趁熟窠子娼门人使,好不获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骑着一疋驴儿,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帐收钱,把旧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开赌场,鬬鸡养狗,人不敢惹他!」经济道:「我去年曾见他一遍,他反面无情,打我一顿,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陆三郎入路旁一酒店内,两个在楼上吃酒。两人计议:「如何处置他,出我这口气?」陆秉义道:「常言说得好:『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如今将理和他说,不见棺才不下泪,他必然不受。小弟有一计策,哥也不消做别的买卖,只写一张状子,把他告到那里,追出你货物银子来,就夺了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钱,和谢合伙,等我在马头上和谢三哥掌柜发卖。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帐日。管情见一月,你稳拍拍的有百十两银子利息,强如做别的生意。」看官听说:当时不因这陆秉义说出这庄事,有分教数个人死于非命!陈经济一种死,死之太苦;一种亡,亡之太屈!死的不好相似那五代的李存孝,汉书中彭越?正是:
「非于前定数,半点不由人!」
经济听了,忙与陆秉义作揖,便道:「贤弟,你说的正是了。我到家,就对我姐夫和姐姐说。这买卖成了,就安贤弟同谢三郎做主管。」当下两个吃了回酒,各下楼来,还了酒钱。经济分付:「陆二哥,兄弟千万谨言!有事我谢你去。」陆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这经济就一五一十,对春梅说。「争奈他爷不在,如何理会?」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紧,等舅写了一张状子,该拐了多少银子货物,拏爷个拜帖儿,都封在里面。等小的送与提刑所,两位官府案下。把这姓杨的拏去衙门中,一顿夹打追问,不怕那厮不拏出银子来!」经济大喜。一面写就一纸状子,拏守备拜帖,弥封停当,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两位官府,正升厅问事。门上人禀进,说:「帅府周爷,差人下书。」何千户与张二官府唤周忠进见,问周爷上任之事,说了一遍。拆开封套观看,见了拜帖状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缉捕番捉,往河下拏杨光彦去。回了个拜帖,付与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爷、奶奶,待我这里追出银两,伺候来领。」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复了春梅说话:「实时准行拏人去了。待追出银子,使人领去。」经济看见两个折帖上面,写着侍生何永寿、张懋得顿首拜,经济心中大喜。迟了不上两日光景,提刑缉捕,观察番捉,往河下把杨光彦并兄弟杨二风,都拏了到于衙门中。两位官府据着陈经济状子审问,一顿夹打,监禁数日,追出三百五十两银子,一百桶生眼布。其余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两。陈经济状上告着九百两,还差三百五十两银子。把房儿卖了五十两,家产尽绝,这经济就把谢家大酒楼夺过来,和谢胖子合伙。春梅又打点出五百两本钱,共凑了一千两之数,委付陆秉义做主管,从新把酒楼妆修,油漆彩画。阑干灼耀,栋宇光新,桌案鲜明,酒肴齐整。一日开张,鼓乐喧天,笙箫杂奏,招集往来客商,四方游妓。陈经济道:「那日宰猪祭祀烧纸。」常言:「启瓮三家醉,开樽十里香。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经济上来大酒楼上,周围都是推窗亮隔,绿油阑干。四望云山迭迭,上下天水相连。正东看,隐隐青螺堆岱岳;正西瞧,茫茫苍雾锁皇都;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楼上下有百十座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正是:
从正月半头,这陈经济在临清马头上大酒楼开张,见一日他发卖三五十两银子,都是谢胖子和主管陆秉义,眼同经手,在柜上掌柜。经济三五日骑头口,伴当小姜儿跟随,往河下算帐一遭。若来,陆秉义和谢胖子两个伙计,在楼上收拾一间干净阁儿,铺陈床帐,安放卓椅;糊的雪洞般齐整,摆设酒席,叫四个好出色粉头相陪,陈三儿那里往来做量酒。一日,三月住间,天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红馥馥杏桃灿锦。陈经济在楼上,搭伏定绿阑干,看那楼下景致,好生热闹!有诗为证:
「风拂烟笼锦施杨,太平时节日初长,
能添壮士英雄胆,善解佳人愁闷肠;
三尺晓垂杨柳岸,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儿未遂平生志,且乐高歌入醉乡。」
一日经济在楼窗后瞧看,正临着河边泊着两只剥船。船上戴着许多箱笼卓凳家活。四五个人尽搬入楼下空屋里来。船上有两个妇人:一个中年妇人,长挑身材,紫膛色;一个年小妇人,搽脂抹粉,生的白净标致,约有二十多岁。尽走入屋里来。经济问谢主管:「是甚么人?不问自由,擅自搬入我屋里来?」谢主管道:「此是两个东京来的妇人,投亲不着,一时间无寻房住,央此间邻居范老来说,暂住两三日便去。正欲报知官人,不想官人来问。」这经济正欲发怒,只见那年小妇人敛袵向前,望经济深深的道了个万福,告说:「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胆,一时出于无奈,不及先来宅上禀报,报乞恕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纳房金,就便搬去。」这经济见小妇人会说话儿,只顾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妇人一双星眼,斜盼经济。两情四目,不能定神。经济口中不言,心内暗道:「倒相那里会过,这般眼熟!」那长挑身材中年妇人,也定睛看着经济,说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门老爷家陈姑夫么?」这经济吃了一惊,便道:「你怎的认得我?」那妇人道:「不瞒姑夫说,奴是旧伙计韩道国浑家,这个就是我女孩儿爱姐。」经济道:「你两口儿在东京,如何来在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妇人道:「在船上看家活。」经济急令量酒,请来相见。不一时,韩道国走来作揖,已是掺白须鬓。因说起:「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拏送三法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我等三口儿,各自逃生,投到清河县我兄弟第二的那里。第二的把房儿卖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儿顾船,从河道中来。不想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问:「姑夫今还在那边西门老爷家里?」经济把头一顷,说了一遍,说:「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备周爷府中做了参谋官,冠带荣身,近日合了两个伙计,在此马头上开了个酒店,胡乱过日子便了。你每三口儿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间住也不妨。请自稳便。」妇人与韩道国一齐下礼。说罢,就搬运船上家活箱笼。经济看得心痒,也使伴当小姜儿和陈三儿,也替他搬运了几件家活。王六儿道:「不劳姑夫费心用力!」彼此俱各欢喜。经济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计较!」经济见天色将晚,有申牌时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早送些茶盒与他。」上马,伴当跟随来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韩爱姐不下。过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齐整,伴当小姜跟随,来河下大酒楼店中,看着做了回买卖。韩道国那边使的八老来请吃茶。经济心下正要瞧去,恰八老来请,便起身进去。只见韩爱姐见了,笑容可掬,接将出来,道了万福:「官人请里面坐。」经济到阁子内坐下。王六儿和韩道国都来陪坐。少顷茶罢,彼此叙些旧时已往的话。经济不住把眼只睃那韩爱姐。爱姐延瞪瞪秋波一双眼,只看经济,彼此都有意了。有诗为证:
「弓鞋窄窄剪春罗,香体酥胸玉一窝;
丽质不胜袅娜态,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顷,韩道国下楼去了。爱姐因问:「官人青春多少?」经济道:「虚度二十六岁。敬问姐姐青春几何?」爱姐笑道:「奴与官人一缘一会,也是二十六岁。旧日又是大老爷府上相会过面,如今又幸遇在一处。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那王六儿见他两个说得入港,看见关目,推个故事也下楼去了。止有他两人对坐。爱姐把些风月话儿把勾经济。经济自幼干惯的道儿,怎不省得,一径起身出去。这韩爱姐从东京来,一路儿和他娘也做些道路。在蔡府中答应,与翟管家做妾,诗词歌赋,诸子百家皆通,甚么事儿不久惯!见经济起身出去无人处,走向前挨在他身边坐下,作娇作痴说道:「官人,你将头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经济正欲拔时,被爱姐一手按住经济头髻,一手拔下簪子来。便起身说:「我和你去楼上说句话儿。」一头说,一头走。经济不免跟上楼来。正是:
「饶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
经济跟他上楼,便道:「姐姐,有甚话说?」爱姐道:「奴与你是宿世姻缘,你休要作假;愿偕枕席之欢,共效于飞之乐!」经济道:「只怕此间有人知觉,却使不得。」那韩爱姐做出许多妖娆来,搂经济在怀,将尖尖玉手扯下他裤子来。两个情兴如火,按纳不住。爱姐不免解衣,仰卧在床上,交姤在一处。正是:
「色胆如天怕甚事,鸳帏云雨百年情!」
经济问:「你叫几姐?」那韩爱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爱姐。」说毕话。霎时云收雨散,偎倚共坐。韩爱姐便告经济说:「自从三口儿东京来投亲不着,盘缠缺欠,你有银子,乞借应与我父亲五两,奴按利纳还,不可推阻。」经济应允,说:「不打紧,姐姐开口,就兑五两来。」爱姐见他依允,还了他金簪子。两个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谈论,吃了一杯茶,爱姐留吃午饭。经济道:「我那边有事,不吃饭了。少间,就送盘缠来与你。」爱姐道:「午后,奴略备一杯水酒,官人不要见却,好歹来坐坐。」经济在店中吃了午饭,又在街上闲散。走了一回,撞见晏公庙师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诉说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贤弟在守备老爷府中认了亲,在大楼开大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来,闲中请去庙中坐一坐。」说罢,宗明归去了。经济走到店中,陆主管道:「里边住的老韩,请官人吃酒,没处寻。」恰好八老又来请:「官人,就请二住主管相陪,再无他客。」经济就同陆主管,走到里边房内,早已安排酒席齐整,无非鱼肉菜菓之类。经济上坐,韩道国主位,陆秉义、谢胖子打横,王六儿与爱姐旁边佥坐。八老往来筛酒下菜。吃过数杯,两个主管会意,说道:「官人慢坐,小人柜上看去。」起身去了。经济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饮。又见主管去了,开怀与韩道国三口儿吃了数杯,便觉些醉将上来。爱姐便问:「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罢了?」经济道:「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罢。」王六儿、韩道国吃了一回,下楼去了。经济向袖中取出五两银子,递与爱姐收了,到下边交与王六儿。两个交杯换盏,倚翠偎红,吃至天晚。爱姐卸下浓妆,留经济就在楼上阁儿里歇了。当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莺声燕语,曲尽绸缪,不能悉记。爱姐将来东京,在蔡太师府中,曾扶持过老太太,也学会些弹唱,又能识字会写。经济听了,欢喜不胜,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与他盘桓一夜,停眠整宿。免不的第二日起来得迟,约饭时纔起来。王六儿安排些鸡子肉圆子,做了个头脑,与他扶头。两个吃了几杯暖酒。少顷,主管来请经济,那边摆饭。经济包巾梳洗,穿衣。吃了饭,又来辞爱姐,要回家去,那爱姐不舍,只顾抛泪。经济道:「我到家三五日就来看你,你休烦恼。」说毕伴当跟随骑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儿:「到家休要说出韩家之事。」小姜儿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经济到府中,只推店中买卖忙,算了帐目,不觉天晚,归来不得,歇了一夜,交割与春梅利息银两,见一遭也有三十两银子之数。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聐聐:「官人怎的外边歇了一夜?想必在柳陌花术行踏,把我丢在家中,独自空房一个,就不思想来家!」一连留住陈经济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来。这里韩爱姐见他一去数日光景不来,店中自使小姜儿来问主管讨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银子去。韩道国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儿,又招惹别的熟人儿,或是商客,来屋里走动,吃茶吃酒。这韩道国当先尝着这个甜头,靠老婆衣饭肥家。况此时王六儿年约四十五六,年纪虽半百,风韵犹存。恰好又得他女儿来接代,他不断绝这样行业。如今索性大做了。原来不当官身衣饭,别无生意,只靠老婆赚钱,谓之隐名娼妓。今时呼为私窠子是也。当时见经济不来,量酒陈三儿替他勾了一个湖州贩丝绵客人何官人来,请他女儿爱姐,那何官人年约五十余岁,手中有千两丝紬绢货物,要请爱姐。爱姐一心想着经济,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楼来。急的韩道国要不的。那何官人又见王六儿长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眉铺鬓,大长水鬓,涎邓邓一双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鲜红嘴唇,料此妇人一定好风情。就留下一两银子,在屋里吃酒,和王六儿歇了一夜。韩道国便躲避在外间歇了。他女儿见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楼上,不下楼来。自此以后,那何官人被王六儿搬弄得快活,两个打得一似火炭般热。没三两日,不来妇人家里过夜。韩道国也禁过他许多钱使。这韩爱姐儿见济一去数十日不见来,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边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备府中探听。看见小姜儿,悄悄问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见说:「官人这两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门。」回来诉与爱姐。爱姐与王六儿商议,买了一副猪蹄,两只烧鸭 ,两尾鲜鱼,一盒酥饼,在楼上磨墨挥笔,拂开花笺,写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与经济去。当下把礼物装在盒内,交八老挑着,叮咛嘱付:「你到城中,见了陈官人,须索见他亲收,讨回帖来。」八老怀内揣着柬帖礼物,一路无词。来到城内守备府前,坐在沿街石台基上。只见伴当小姜儿出来,看见八老:「你又来做甚么?」八老与声喏,拉在僻净处说:「我特来见你官人,送礼来了,有话说。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报官人知道。」小姜随即转身进去。不多时,只见经济摇将出来。那时约五月,天气暑热。经济穿着纱衣服,头戴瓦珑帽,金簪子,脚上凉鞋净袜。八老慌忙声喏,说道:「官人贵体好些?韩爱姐使我稍一柬帖,送礼来了。」经济接了柬帖,说:「五姐好么?」八老道:「五姐见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覆官人,几时下去走走?」经济拆开柬帖观看,上面写着甚言词:
「贱妾韩爱姐敛袵拜谨启
情郎陈大官人台下:
自别尊颜,思慕之心,未尝少怠;悬悬不忘于心。向蒙期约,妾倚门凝望,不见降临蓬荜。昨遣八老探问起居,不遇而回。听闻贵恙欠安,令妾空怀怅望,坐卧闷恹。不能顿生尔翼,而傍君之足下也!君在家自有娇妻美爱,又岂肯动念于妾?犹吐去之菓核也!兹具腥味茶盒数事,少申问安诚意。辛希笑纳,情照不宣!外具锦绣鸳鸯香囊一个,青丝一缕,少表寸心!
下书仲夏念日贱妾爱姐再拜」
经济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里面,安放青丝一缕。香囊是鸳鸯双口做的,扣着:「寄与情郎陈君膝下」八字。依先折了,藏在袖中。府傍侧首,有个酒店。令小姜儿:「领八老同店内吃锺酒,等我写回帖与你。」分付小姜儿:「把礼物收进我房里去。你娘若问,只说河下店主人谢家送的礼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礼物收进去了。经济走到书院房内,悄悄写了回柬。又包了五两银子,到酒店内,问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谢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罢。」经济将银子并回柬付八老,说:「到家多多拜上五姐,这五两白金与他盘缠。过三两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银柬下楼,经济送出店门,八老一直去了。经济走入房中,葛翠屏便问:「是谁家送礼物?」经济悉言:「店主人谢胖子打听我不快,送这礼物来问安。」翠屏亦信其实。两口儿计议,交丫鬟金钱儿拏盘子,拏了一只烧鸭 ,一尾鲜鱼,半副蹄子,送到后边与春梅吃。说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问。此事表过不题。却说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门将银柬都付与爱姐收了。拆开银柬,灯下观看。上面写道:
经济顿首字覆
「爱卿韩五姐妆次:向蒙会问,又承厚款,亦且云情雨意,袵席钟爱,无时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趋会。偶因贱躯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顾,兼惠可口佳肴,不胜感激!只在二三日间,容当面布。外具白金五两,绫帕一方,少申远芹之敬!伏乞心鉴,万万!
下书经济再拜。」
爱姐看了,见帕上写着四句,诗曰:
「吴绫帕儿织回纹,洒翰挥毫墨迹新;
寄与多情韩五姐,永谐鸾凤百年情。」
看毕,爱姐把银子付与王六儿。母子千欢万喜等候经济,不在话下。正是:
「得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相投。」
有诗为证:
「碧纱窗下启笺封,一纸云鸿香气浓;
知你挥毫经玉手,相思都付不言中。」
毕竟未知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更新于:5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