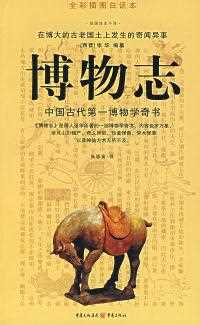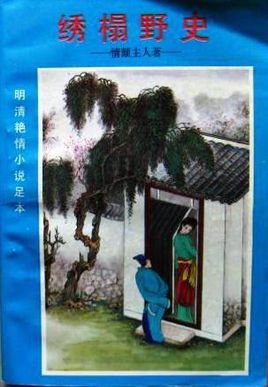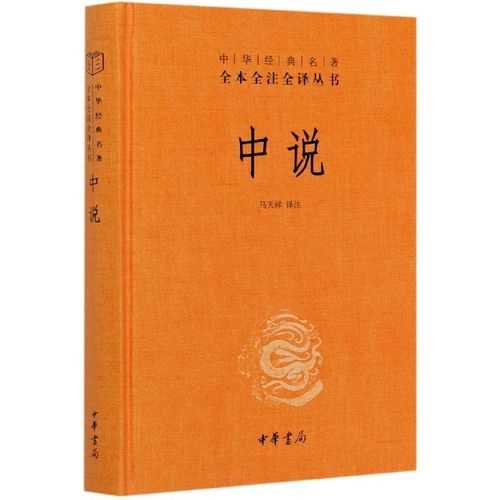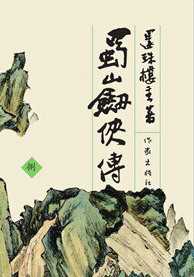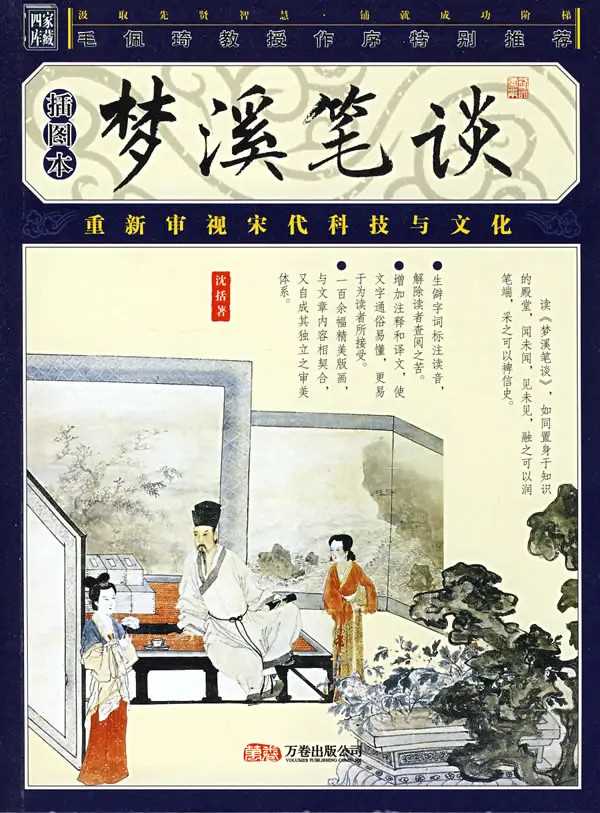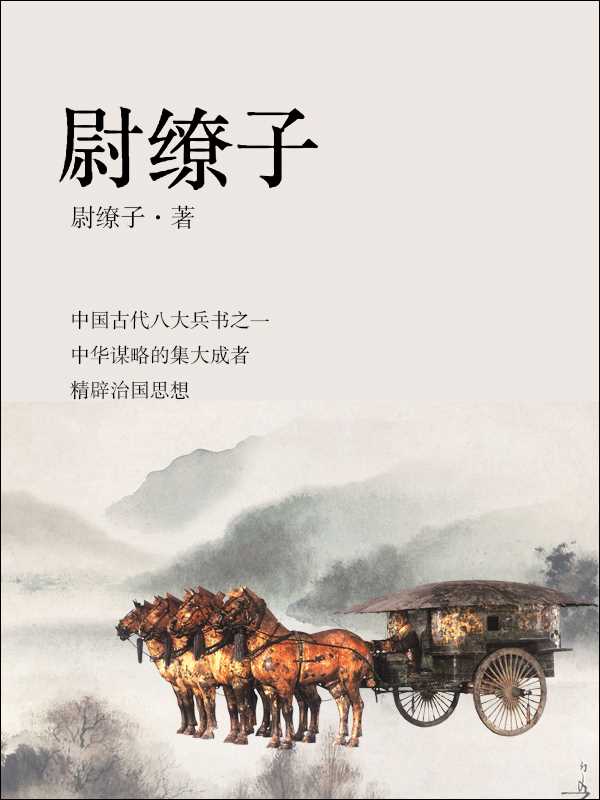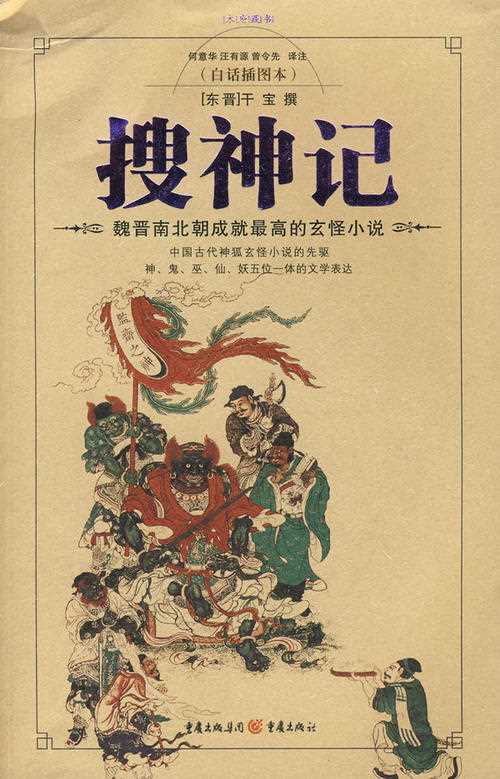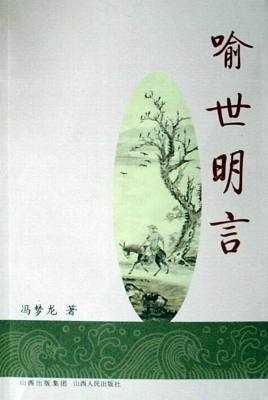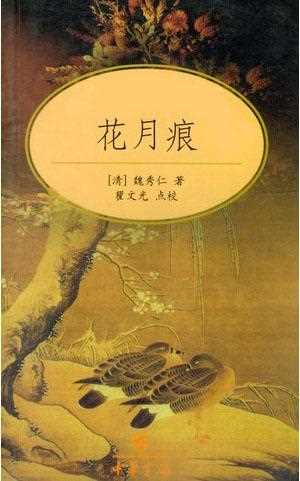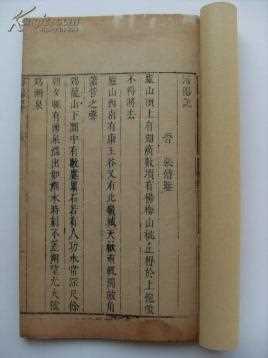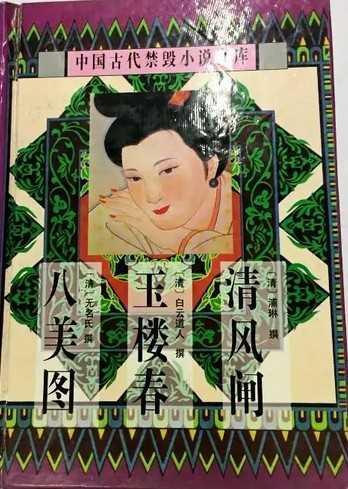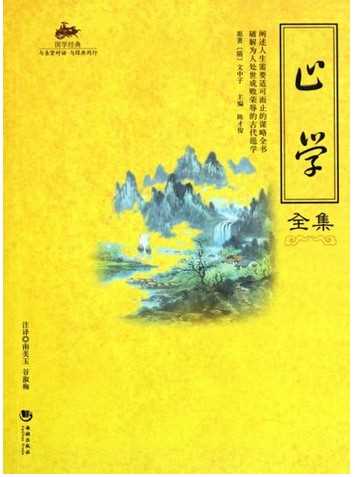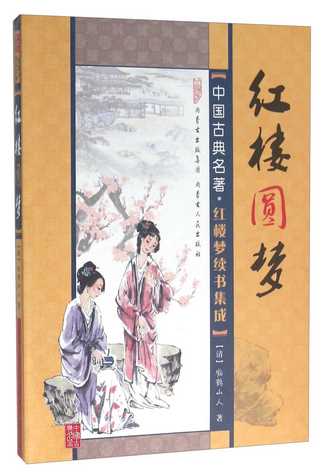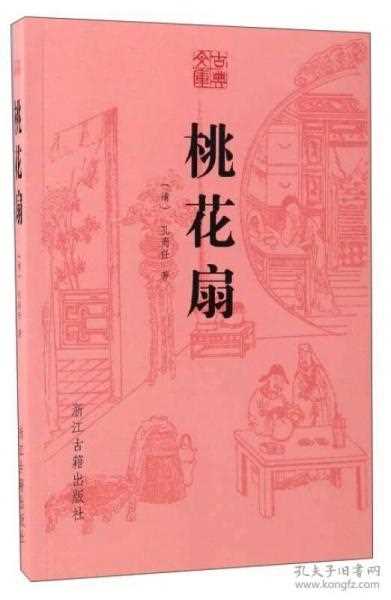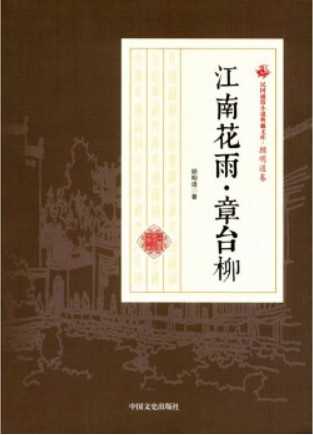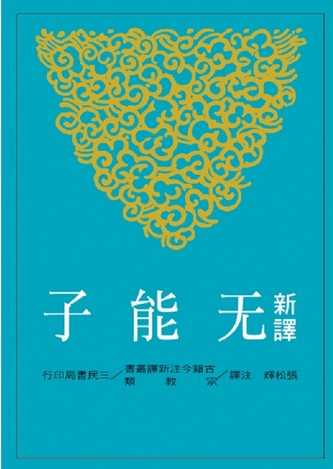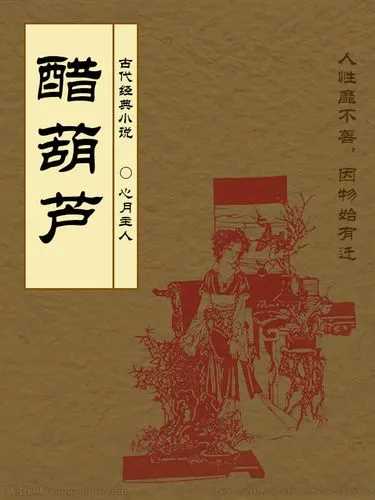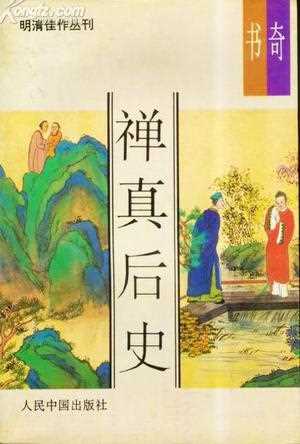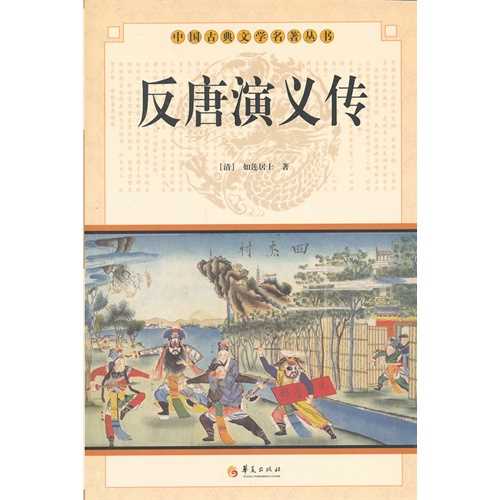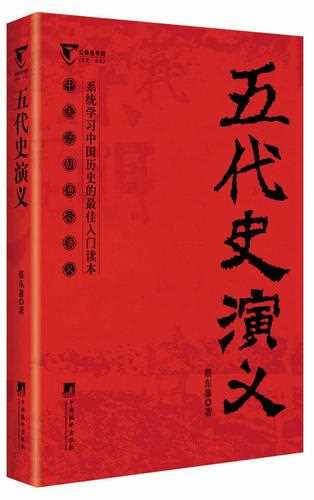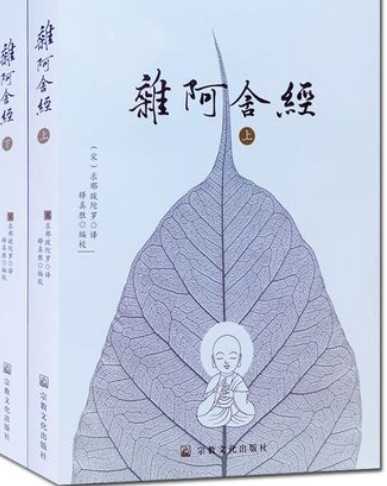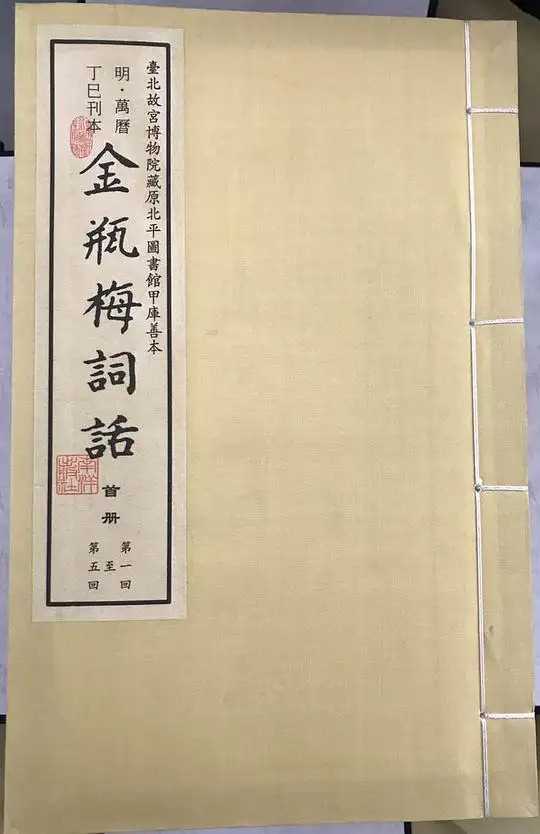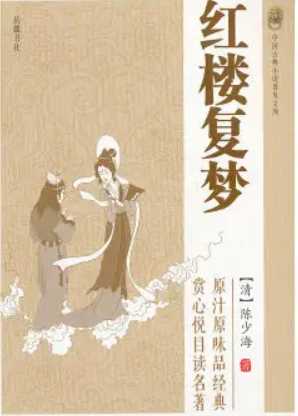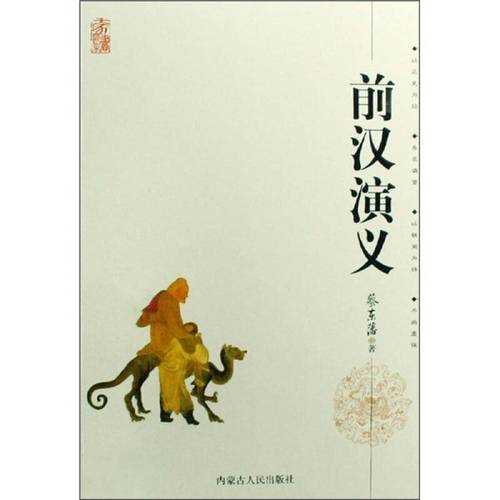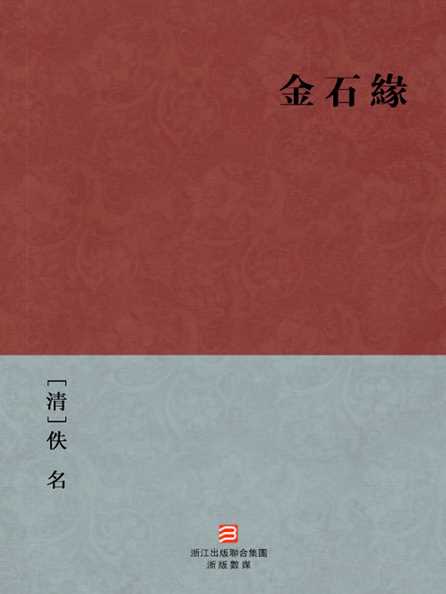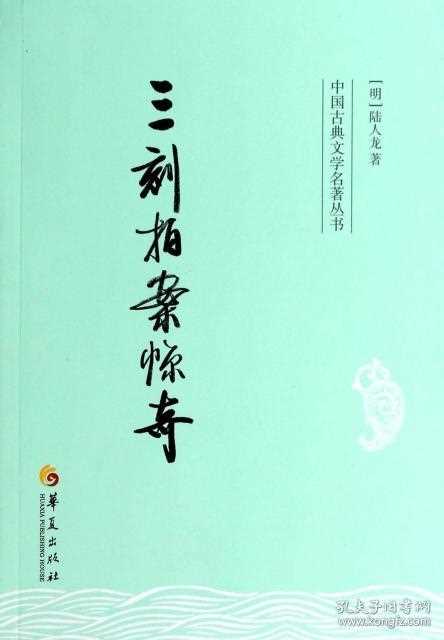却说薛姨妈席散回家,独坐房中,忽见床前箱内露出衣角,因想前郡主所赠之物,除赎当三十余两外,余银俱锁放在内。
忙即开看,见全数已空,并几件心爱玩物,一齐遗失。气得发昏,因问宝蟾道:“我这里丢了几两银子,你知道么?”宝蟾道:“你老只怕糊涂了。你老前番去拜客,还要我们大爷张罗钱赎当,大爷不肯,你还上气。此刻怎么又有钱了?”薛母道:“你想,我房里又没有外人,我这钱又新郡主给的,怎得丢了?”
宝蟾道:“郡主不郡主,我知不道。你的钱鬼鬼祟祟藏着,干什么丢了?正是,太阳在屋子里呢,你老有好亲眷,叫大班儿上查查就是了!”薛母道:“家贼难防,还查什么?”宝蟾道:“你说我是贼,你就是窝家了。我在你家熬得乌鸡似的,还落得个贼名,我也不要命了!”一头撞去,把薛母几乎撞倒,幸得邢岫烟再三解劝,嘴里还是哓哓。薛母听了又气又恨,自此卧床不起。
那薛蟠自同宝蟾偷了这宗东西,手头松动,又去闹赌。无如贾珍新疆回来,一改前非,贾琏又管事甚忙,只得王仁、邢大舅一干人赌了两日,甚没意兴。贾芸道:“闻得蒋琪官家古董铺后也在开赌,何不去试试?”呆子欣然允诺。贾芸又邀贾环同去,做了几场输赢。
贾环忽想起袭人在那里,因说要见,琪官道:“三爷自家人有什么?但我这家里,要就这么叫他出来,不肯的,我有道理。”于是四人打牌时,琪官忽说要到忠顺王府去,这里不便散局,请袭人代一代。袭人见是熟人,又系丈夫叫他暂代,便无可不可的坐下。琪官回来就同在一块儿喝酒而散。
那知忠顺府三阿哥也是淘气的,闻得蒋琪官家的肯出来陪酒,也要来赌,琪官忙加倍备办下供给,请他来赌,说明现钱押梢:薛蟠是五十两现银;三阿哥是一个金镶玉龙佩;贾芸是两只金虾须镯;贾环也有押物。算起帐来,因贾环善于偷张,只他大胜。琪官当着众人将镯、佩交代,又分了十来两银子。
晚间入席。三阿哥执意要见袭人。袭人因他是琪官正主,只得装得花红柳绿出来,递了一回酒,被三阿哥轻薄了一回,才散。
隔了几日,贾政朝回,忽报忠顺府长官要见。贾政道:“忠顺府是那年因宝玉事差人来了,久不往还,今日又打发人来怎么?请厅上坐!”彼此见了礼,长官道:“下官奉命而来,仍有一件事相求,敢烦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爷知情,即下官亦感谢不尽!”贾政忙陪笑道:“又有何见谕?”长官道:“就是前番到府上找着的那小旦琪官,那知他竟诱我们府里三阿哥去赌,同赌的都是尊府令亲。三阿哥将一个御赐玉佩押着了,查究起来,说在令郎处。王爷特命走领,烦老先生转达令郎,将玉佩发还,该钱若干随后奉上。”说罢,忙打一拱。贾政笑道:“小儿原不妥当,如今有了部务,又在枢密,又要轮值书房,此刻尚未回家,那有工夫玩这个?所访恐未必确?”长官道:“大人还道是郡马爷么?说的又是一位小令郎,也行三的。”
贾政忙唤贾环出来,问道:“你这奴才在家种种不妥,又弄出无法无天的事来,王府里三阿哥金枝玉叶何等样人?你敢同赌,还留他赐物。我即刻捆你送官,究出同赌,一并处死!”长官道:“这倒不必,但请将赐物见还,便感恩不尽!至花赌一事,王爷因多是戚友,只将蒋琪送官加责,余者一概不究!”贾环见事已说真,默默无言。贾政又喝道:“玉佩究藏何处?”贾环只得说道:“在书房拜匣内。”贾政即刻叫贾琏取来。及取到看时,尚有虾须镯一对,贾琏认得是平儿之物,且拿来收起,先将玉佩送上,长官见了,便道谢起身。
贾政此时气得目定口呆,一面命贾环不许走动,回来再问,一面送长官出去。回来一叠连声叫:“拿大棍来!拿绳捆着!”
众小厮只得齐声答应,把贾环一如那年宝玉一样,按在凳上,拿着大板,打了十来下。贾环自知不能讨饶,只呜呜的哭。贾政喝令重打,又打了十来下。贾政嫌轻,一脚踢开小厮,拿了板子狠命的打了一二十下。恰好宝玉朝回,同贾琏上来乞恩,按贾环的小厮忙松手走开。贾环已气弱声嘶,动弹不得了。宝玉、贾琏请贾政息怒,且问他如何赌法?同赌何人?贾政道:“你问,你问!”二人下去问时,贾环喘着,并无一语,只得传贾环跟班头儿钱槐来问。钱槐到来,只有磕头。贾琏道:“你这糊涂王八,还不直说,先打一百鞭子!”打到五十,钱槐碰响头求饶,就将如何在蒋家花赌,如何偷张赢钱,如何叫他女人陪酒。说完了,贾政还要打,宝玉已请王夫人出来,一力护祝贾琏道:“这几个小厮,断饶不得,竟革了另挑罢!”
贾政点头,方一面命将贾环送入卧房,一面将钱槐等交赖大发落。
那知内有个是王善家的孙子,就去求他祖母,并将金镯系平儿之物都告诉了。王善家又添上些说话,求邢夫人。邢夫人因巧姐一事,很恶数平儿,便叫贾琏道:“这赌事甚小,何必累及下人!难道你们不赌的,倒是家里金饰赠与外人,这名声儿很难听呢!你也查查!”恰好平儿也来请安,贾琏便问:“我们这虾须镯在么?”平儿道:“给姑娘的,问姑娘就是了。”
随叫巧姐来问,巧姐也说:“有的。”邢夫人道:“如此,去拿来瞧瞧!”巧姐不知就里,拿饰匣来开看时,不但不见了金镯,连一切珠饰已失了好些。巧姐哭道:“这是怎么说?”邢夫人道:“怎么说,问你姨娘便了,给了人还装没事人!”平儿知话有因,也哭道:“我蒙二爷抬举,在房里十几年,从不干坏心的事,求太太说话还斟酌些。”邢夫人道:“是我不斟酌?琏儿把东西给他瞧,你是一顶绿帽子戴定了!”贾琏只得将镯子拿出,道:“你去看,怎么说?”平儿气得战抖抖的道:“这捞什子早说给巧姐儿,怎么来派我?”邢夫人道:“就该打嘴,你还要栽姑娘么?”王善家的道:“平姑娘赖不去了,真赃现获,把余的拿出来,再求太太开条生路正景,苦闹就是自己寻死了!”平儿气极了道:“要死就死,我死了饶那个?”
说罢,就出来寻死,巧姐一面哭,一面赶拉。邢夫人道:“拉什么?拉到屯里去,再拣个小女婿不成!”正没解交,幸亏探春、宝钗等闻信而来,把平儿、巧姐拉到园中去了。
邢夫人吩咐贾琏道:“你就去问环儿,问定了,再容这淫妇在世,我断不依!”贾琏只得答应着出来。问贾环也道:“这是平二嫂子赠芸哥儿,芸哥儿输了暂押我处的。”贾琏听了,气得个发昏章第十一,就要去死问平儿,亏得宝玉挡住,道:“事不三思,必有后悔。这事必问准芸儿再说,岂可冒昧?”
那时荣府中三三两两,有替平儿抱屈的,有为平儿趁愿的,纷纷不一。独有柳五儿感念前情,必要救他,因他母亲柳嫂子做了碗莲叶羹去喂贾环。他从门口走过,听得房里有人,便住了脚,只听得彩云在那里再四盘问。贾环道:“那虾须镯,芸儿告诉我,实是托小红替坠儿借的。因昨晚王善家叫他孙子来说:‘大太太说,叫我认定平嫂子给芸儿的,我便无事。’我才这么说的。”彩云道:“呀!三爷,你亏告诉我。你想侄儿戏婶子什么罪名?芸哥儿肯认不肯认?老爷问起来,你又要受风霜。依我直说为是!”环哥点头答应。柳家遂不去,回来对五儿说了。正想设法去问小红,恰好小红来探消息。五儿道:“小红妹妹,你敢是打听新闻来了?”小红道:“我因听得干连着二奶奶,故来问问。”五儿道:“不但琏二奶奶,连芸二爷只怕都要没命!”小红呆了半晌道:“好姊姊,这是怎么说?”五儿道:“你想,侄儿戏婶子什么罪名?老爷又最恶数这条,问准了还有命吗?”小红听了流泪道:“姊姊,这镯委是我和坠妹妹借来给芸二爷的。今既闹出事来,让我竟去认了罪,省得带累好人;就芸哥儿也不至死。”五儿大喜道:“妹妹若如此,包我们身上,不叫妹妹受委屈。”
二人遂同到上房,恰好都在那里。五儿先向王夫人道:“小红有话回太太。”小红便跪上来,将前事说了一遍。邢夫人道:“既这么,环儿为什么说呢?”正说间,报道贾芸找到。
贾政走出中阁,贾琏带贾芸进来跪下,只有碰头。贾政喝道:“你这该死孽障!你这镯子,平婶子几时给你的?”芸儿又碰头道:“并不是平婶子给的,实是托小红向坠儿借的。”贾政便命叫贾环。不一会,两人扶了环儿来到,跪都跪不住,只好趴着。贾政喝问:“你说,平嫂子赠镯的话,那里来的?”贾环据实供出。贾政大怒,一面喝令二人暂退,一面请郡主出来,道:“家奴结党诬主,罪在不赦!但是女人,我不便用刑。你又有御赐如意,可替我一办。”
郡主得了话,即命太监在缀锦阁设了公座,一面命四儿捧着御赐金如意,冉冉而来。到了阁下,望阙谢恩,然后入坐,叫太监排列刑具,听候审问。叫小红,小红上来将上项事说了一遍。即叫坠儿,坠儿上来那里肯招?郡主叫拶起来,只得招了,问他赃在那里?又不肯说,又叫拶起,才供明寄在王善家那里。郡主一面押坠儿去起赃,一面命将王善家拿下。
王善家恃着大太太陪房,直立不跪。郡主大怒道:“这是什么所块,你敢放肆!”喝叫先打一百皮鞭。太监将他剥去衣裙,只留叉裤,拖翻在地,左右施刑,打得他乱滚求饶,哀声不绝。打完后抓了头发,背剪跪着,喝令速供。那知王善家的打昏了,倒将因晴雯撵逐坠儿,故与袭人设法将他害死先招出来。及问他陷害平儿等话,他又延挨不认,恰好芳官将搜出原赃一一检点呈上,他料抵赖不过,只得认了;又拉大太太叫他这么说的。郡主大怒,重又掌嘴四十,把牙齿都打脱了几个,方没言语。郡主命录了供词,送与二位太太请示发落。邢夫人此时无奈,说:“但凭郡主。”郡主命将王善家押至芙蓉祠下,裙裤重责四十板,打得王善家遍身干白的是肉,鲜红的是血,青紫的是肿,黄黑的是泥,五色斑斓,倒像在染缸里爬出来的。
限令调治十日,好后永罚在净军所当差。坠儿也打四十,即行配人。小红姑念直供不讳,免责完结。后事如何,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