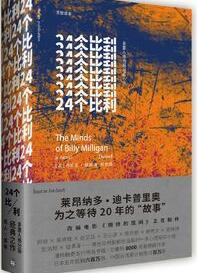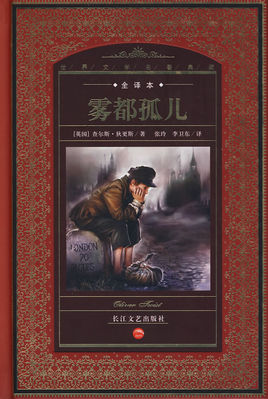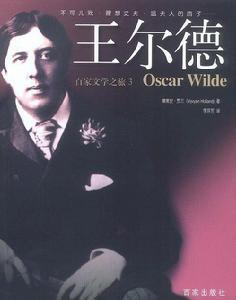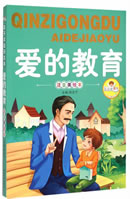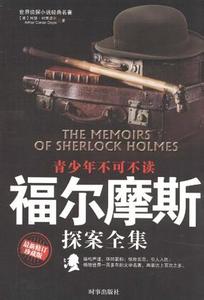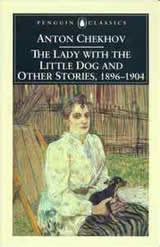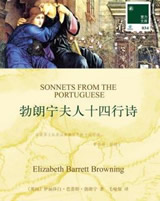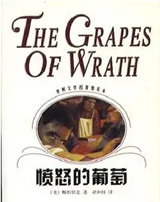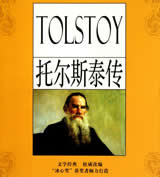大教堂里发生了那件事之后,于连一直沉浸在幽深的梦幻之中,久久不能解脱,一天早晨,严厉的彼拉神甫打发人来叫他。
“瞧,夏斯-贝尔纳神甫写信来了,说您的好话呢。总的来说,我对您的行为相当满意。您极不谨慎,甚至轻率冒失,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您的心是善良的,甚至是宽洪大量的,智力过人。总之,我在您身上看到了一星不容忽视的火花。
“我工作了十五年,就要离开这幢房子了:我的罪过是让神学院的学生们自由判断,没有保护也没有破坏您在告罪亭里对我说的那个秘密组织。我走之前,想为您做点事情,要不是有根据在您房间发现的阿芒达-比奈的地址所作的揭发,此事我两个月之前就该做了,您理应得到。我让您作《新约》和《旧约》的辅导教师。”
于连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真想跪下,感谢天主;但是他油然而生另一种更为真实的感情。他走近彼拉神甫,拿起他的手,举到自己的唇边。
“这是干什么?”彼拉神甫生气地叫道;然而,于连的眼睛比行动表明了更多的东西。
彼拉神甫惊奇地望着他,仿佛一个多年来已不惯于面对细腻的感情的人一样。这种注视泄露了院长的真情,他的声音变了。
“好吧!是的,我的孩子,我对你很有感情。上天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本该公正无私,对人既无恨亦无爱。你的一生将是艰难的。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某种使俗人不悦的东西。嫉妒和诽谤将对你穷追不舍。无论天主将你放在什么地方,你的同伴都不会不怀着僧恨看着你;如果他们装作爱你,那是为了更有把握地出卖你。对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只向天主求助,他为了惩罚你的自负而使你必须受人憎恨;你的行为要纯洁,我看这是你唯一的指望。如果你以一种不可战胜的拥抱坚持真理,你的敌人迟早会狼狈不堪的。”
于连那么久没有听到过友爱的声音了,不禁泪如雨下,我们应该原谅他的软弱。彼拉神甫朝他张开臂膀,这时刻对两个人来说都是甜蜜的。
于连欣喜若狂;这是他得到的第一次提升;好处是巨大的。要想象这些好处,须得曾经被迫几个月内不得片刻的独处,并且跟一些至少是讨厌的而大部分是不堪忍受的同学直接接触。单单他们的吵嚷就足以使体质脆弱的人神经错乱。这些吃得饱穿得暖的乡下人,只有在使出两肺的全部力量大叫才能感到那种吵吵闹闹的快乐,才能觉得表达得完全。
现在于连单独用餐,或者差不多,比其他学生晚一个钟头。他有花园的钥匙,园中无人的时候可以进去散步。
于连大感惊异,发觉人家不那么恨他了;他原本料到会有加倍的仇恨呢。他不愿意人家跟他讲话,这种秘而不宣的愿望仍嫌太明显,给他招来不少敌人,现在不再标志着一种可笑的高傲了。在他周围那些粗俗的人眼里,这是他对自己的职位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感觉。仇恨明显减少,尤其在变成他的学生的那些最年轻的同学中间,他待他们也是彬彬有礼的。渐渐地,他居然也有了拥戴者,叫他马丁-路德已经是不得体的了。
然而,说出他的敌友的名字,有什么用呢?所有这一切都是丑恶的,图画越真实就越丑恶。不过,他们是民众的唯一的道德教师,没有了他们,民众会变成什么呢?报纸难道能够代替本堂神甫吗?
于连就任新职以后,神学院院长装作没有证人在场就绝不跟他讲话。这种作法对先生对弟子都是一种谨慎,但尤其是一种考验。彼拉是个严厉的詹森派,他的不变的原则是:您认为一个人有才能吗?那就对他希望的一切、对他所做的一切设置障碍吧。如果他的才能是真的,他就一定会推倒或绕过障碍。
狩猎的季节到了。富凯心血来潮,以于连的父母的名义给神学院送来一头鹿和一头野猪。两头死兽摆在厨房和食堂之间的过道上。神学院的学生吃饭时从那里经过,都看见了。这成了好奇心的大目标。野猪虽然是死的,也把那些最年轻的学生吓了一跳,他们摸摸它的獠牙。整整一个礼拜,大家不谈别的。
这份礼物把于连的家庭站入社会中应该受到尊敬的那一部分,给了嫉妒一次致命的打击。财富确认了于连的优越。夏泽尔和几位最出色的学生主动接近他,差不多要埋怨他没有把他父母的财产情况告诉他们,害得他们对金钱有失敬之虞。
当时正在征兵,于连是神学院学生,得以免除兵役。这件事使他非常激动。“噍,这个时刻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要是早二十年,我就会开始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生活了!”
他独自一个人在神学院的花园里散步,听见几个修围墙的泥瓦匠在说话。
“喂:该走了,又征新兵了。”
“在那个人的时代,那可好了!泥瓦匠能当军官,当将军,这事儿见过。”
“现在你去看看!穷光蛋才走,手里有几个的人都留在家乡。”
“生下来穷,一辈子穷,就是这么回事儿。”
“嘿,他们说那个人死了,是真的吗?”第三个泥瓦匠说。,
“是大块头们说的,你看,那个人让他们害怕了。”
“多不同啊,在那个时候,活儿干得也顺!说他是被他的元帅们出卖的:叛徒才这么干呀!”
这场谈话使于连稍感宽慰。他离开的时候叹了口气,背诵道:
人民还怀念着的唯一的国王
考试的日子到了。于连答得很出色,他看到夏泽尔也力图显示其全部知识。
第一天,由著名的福科莱代理主教委派的那些主考人就大为不悦,他们不得不在名单上一再将于连列为第一名,至少是第二名,有人向他们指出,这个于连-索莱尔是彼拉神甫的宠儿。在神学院,有人打赌说,在考试总成绩的名单上于连一定会名列第一,这将给他带来与主教大人一道进餐的光荣。但是在一场涉及教父们的考试快结束时,一位狡猾的主考人在问了于连关于圣杰洛姆以及他对西塞罗的酷爱的问题之后,又谈到贺拉斯、维吉尔和其他几位世俗作家。同学们都一无所知,于连却背诵了这几位作者的不少段落。成功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了,根据主考人的一再提问,他满怀激情地背诵和意译了贺拉斯的好几首颂歌。于连上了钩,二十分钟过去了,主考人突然变了脸,尖刻地责备他在这些世俗作家身上浪费了时间,脑子里装了不少无用的或,者罪恶的思想。
“我是个傻瓜,先生,您说得对,”于连谦卑地说,恍然大悟,原来是个巧妙的圈套,他上当了。
主考人的这条诡计,就是在神学院里,也被认为是卑鄙的,然而这并未妨碍德-福利莱先生用他那强有力的手在于连的名字旁边写上198这个数目。德-福利莱先生是个精明人,他如此巧妙地在贝蒙松组织了一个圣会网,其发往巴黎的快报令法官、省长,直至驻军的将领胆战心惊。他这样地侮辱他的敌人、詹森派信徒彼拉,感到很高兴。
十年以来,他的大事就是解除彼拉的神学院院长职务。彼拉神甫真诚,虚诚,不搞阴谋,忠于职守,他为于连规定的行为准则自己也遵循不悖。但是上天在愤怒中给了他一副暴躁易怒的脾气,对侮辱和仇恨特别敏感。对于这颗火热的灵魂,任何侮辱都不会徒劳无功。天主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他就认为自己对这个岗位是有用的,否则他早就辞职一百次了。“我遏止了耶稣会教义和偶像崇拜。”他对自已说。
考试那段时间,他大概两个月未曾同于连说过话,当他接到宣布考试成绩的公报,看到这个学生的名字旁边写着198这个数目,他病例了一个礼拜,他是把这个学生看作本神学院的光荣的呀。对于这个性情严厉的人来说,唯一的安慰是把他所有的监视手段集中用在于连身上。他感到欣喜的是,他在于连身上没有发现愤怒、报复计划和气馁。
几个礼拜之后,于连接到一封信,不免打了个哆嗦;信上盖有巴黎的邮戮。“终于,”他想,“德-莱纳夫人想起了她的诺言。”一个署名保尔-索莱尔的先生,自称是他的亲属,给他寄来一张五百法郎的汇票。信上还说,如果于连继读研究那些优秀的拉丁作家,并且卓有成绩,将每年寄给他一笔同样数目的钱。
“这是她,这是她的仁慈:“于连的心充满了柔情,自言自语道,“她想安慰我,可是为什么没有一句有情意的话?”
这封信他弄错了,德-莱纳夫人在她的朋友德尔维夫人的指导下,已完全沉浸在深深的悔恨中了。她还时常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不寻常的人,与他相遇搅乱了她的生活,但她很注意不给他写信。
如果使用神学院的语言,我们可以承认这笔五百法郎的汇款是个奇迹,而且可以说上天是利用德-福利莱先生本人送了这份礼物给于连。
十二年前,德-福利莱神甫来到贝藏松,带的那只旅行箱小得不能再小,根据传闻,那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如今他是本省最富有的地主之一。在他致富的过程中,他买过一块地产的一半,另一半通过继承落入德-拉莫尔侯财手中。两个人于是大打官司。
尽管德-拉莫尔侯爵先生在巴黎地位显赫,并在宫中担任要职,还是觉得在贝藏松与一位据称可以左右省长任免的代理主教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本来可以请求批准一笔赏赐,以预算允许的随便什么名义为掩盖把这场区区五万法郎的小官司让给德-福利莱神甫,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大光其火。他认为自己有理,而且理由充足!
不过,请允许我斗胆问一句:哪一个法官没有一个儿子或一个什么亲戚需要安插在某个地方呢?
为了让最盲目的人也看得清楚,德-福利莱神甫在赢得第一次裁决一个礼拜之后,乘上主教大人的四轮马车,亲自把一枚荣誉团骑士勋章送给他的律师。德-拉莫尔先生对对方的行动感到有些震惊,并且感到他的律师软下来了,就向谢朗神甫求教,谢朗神甫建议他与彼拉先生联系。
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已持续了好几年。彼拉神甫带着他那炽烈的性格投入到这件事情中去。他不断地会见侯爵的律师,研究案情,确认侯爵的案于有理之后,就公开地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诉讼代理人,与权力很大的代理主教打宫司。这种傲慢无礼,而且还是出自一位小小的詹森派教徒,使代理主教感到了奇耻大辱!
“你们看看这个自以为那么有权势的宫廷贵族是什么东西吧,”德-福利莱神父对他的亲信们说,“德-拉莫尔先生连一枚可怜的勋章都没有给他在贝藏松的代理人送来,而且还要让他灰溜溜地被撤职。但是,有人写信给我说,这位贵族议员每个礼拜都要佩带蓝绶带到掌玺大臣的沙龙去炫耀,不管这掌玺大臣是何等样人!”
尽管彼拉神甫全力以赴,德-拉莫尔先生也和司法大臣,尤其是和他的下属关系好得不能再好,六年的苦心经营也只落得个没有完全输掉这场官司。
为了两个人都热情关注的事情,侯爵不断与彼拉神甫通信,终于品出神甫的那种才智的味道了。渐渐地,尽管社会地位悬殊,他们的通信有了一种亲切的口气。彼拉神甫告诉侯爵,有人采取凌辱他的办法迫使他辞职。那种卑鄙的伎俩使他很生气,他认为是针对于连的,也就向侯爵讲了于连的事情。
这位大贵人虽然很有钱,却一点儿也不吝啬,他始终未能让彼拉神甫接受他的钱,包括支付因办案而花去的邮费。他灵机一动,就给神甫心爱的学生汇去五百法郎。
德-拉莫尔先生还亲自写了那封通知汇款的信。这件事使他想到了神甫。
一天,神甫接到一纸短简,说有急事请他务必到贝藏松郊外一家客店去一趟。他在那里见到了德-拉莫尔先生的管家。
“侯爵先生派我给您送来他的马车,”那人对他说,“他希望您在读了此信后能在四、五天后前往巴黎。请您告诉我时间,这期间我将到侯爵先生在弗朗什-孔泰的地产上跑跑。然后,在您觉得合适的时候我们就启程去巴黎。”
信很短:
“我亲爱的先生,摆脱掉外省的种种烦恼,到巴黎来呼吸一点儿宁静的空气吧。我给您送去我的车,我已命人在四天内等侯您的决定。我本人在巴黎等您直到礼拜二。我需要您的同意,先生,以您的名义接受巴黎附近最好的本堂区之一。您未来的本堂区教民中最富有的一位从未见过您,但对您比您能想象的还要忠诚,他就是德-拉莫尔侯爵。”
严厉的彼拉神甫没有料到,他居然很爱这座遍布敌人的神学院,十五年来,他为它用尽了心思。德-拉莫尔先生的信仿佛一个要做一次残酷而必要的手术的外科医生出现在他面前。他的解职势在必行。他约管家三日后会面。
四十八小时内,他一直犹豫不决,心烦意乱。最后,他给德-拉莫尔先生写了一封信,又给主教大人写了一封堪称教会体杰作的一封信,只是略嫌长了些。要想找出更无懈可击、流露出更真诚的敬意的句子,也许是件困难的事。这封信注定要让德-福利莱先在主子面前难受一个钟头,信中逐条陈述那些使人严重不满的原因,甚至提到了些卑劣的小麻烦,彼拉神甫不得不忍受了六年,终于逼得他离开教区。
有人从他的柴堆上偷木柴,毒死他的狗,等等,等等。
他写完信,派人叫醒于连,于连和其他学生一样,晚上八点即上床睡觉。
“您知道主教住在哪里吗?”他用漂亮的拉丁文风格对他说,“把这封信送交主教大人。我井不瞒您,我是把您往狼群里送。注意看,注意听。您的回答中不许有半点谎言,但是您要想到,盘问您的人也许会体会到一种终于能加害于您的真正的快乐。我的孩子,在离开您之前告诉您这种经验,我感到十分坦然,因为我不想瞒着您,您送的这封信就是我的辞呈。”
于连呆立不动,他爱彼拉神甫。谨慎徒然地对他说:“这个正直的人离去之后,圣心派会贬损我,也许会赶走我。”
他不能只想自己。他感到难办的是,如何想出一句得体的话,这时他真地感到才思枯竭了。
“怎么!我的朋友,您不去?”
“我听人说,先生,”于连怯生生地说,“您主持神学院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任何积蓄,我这里有六百法郎。”
泪水使他说不下去了。
“这也得登记上,”神学院前院长冷冷地说。“去主教府吧,时间不早了。”
正巧这天晚上德-福利莱神甫在主教府的客厅里值班;主教大人去省府吃饭了。所以,于连把信交给了德-福利莱神甫本人,不过他并不认识他。
于连大吃一惊,他看见这位神甫公然拆开了给主教的信。代理主教那张漂亮的面孔立刻显出一种惊奇的表情,其中混杂着强烈的快乐,紧接着又变得加倍的严肃。这张脸气色很好,于连印象极深,趁他读信的工夫,细细地端详起来。如果不是某些线条显露出一种极端的精明,这张脸会更庄重些;如果这张漂亮面孔的主人万一有一刻走神的话,这种极端的精明会显露出一种虚伪。鼻子太突出,形成一条笔直的线,不幸使一个很高贵的侧影无可救药地酷似一只狐狸。此外,这位看起来如此关心彼拉先生辞职的神甫穿戴高雅,于连很喜欢,他从未见过别的教士如此穿戴。
于连只是后来才知道德-福利莱神甫的特殊才能是什么。德-福利莱神甫知道如何逗主教开心。主教是一个可爱的老人,生来就是要住在巴黎的,把来贝藏松视为流放。他的视力极差,又偏偏酷爱吃鱼,于是端上来的鱼就由他先把刺挑干净。
于连静静地端详着反复阅读辞呈的神甫,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一位穿着华丽的仆人急匆匆走过。于连不及转向门口,就已看见一个小老头儿,胸前佩带着主教十字架。他忙跪倒在地,主教朝他善意地笑了笑,走过去了。那位漂亮的神甫跟上去,于连独自留在客厅里,从容地欣赏起室内虔诚的豪华。
贝藏松主教是个风趣的人,饱尝流亡之苦,但并未被压垮;他已然七十五岁,对十年后发生的事情极少关心。
“我觉得刚才经过时后见一个目光精明的学生,他是谁?”主教问,“根据我的规定,这个时候他们不是该睡觉了吗?”
“这一位可清醒着哪,我向您保证,主教大人,而且他带来一个大新闻:还呆在您的教区的唯一的詹森派教徒辞职了。这个可怕的彼拉神甫终于懂得了说话意味着什么。”
“那好哇!”主教笑着说,“可我不相信您能找到一个抵得上他的人来代替他。为了向您显示这个人的价值,我明天请他来吃饭。”
代理主教想趁机说句话,谈谈选择继任者的事。主教不准备谈公事,对他说:
“在让另一位进来之前,先让我们知道知道这一位如何离开吧。给我把那个学生叫来,孩子口中出真言。”
有人叫于连。“这下我要处在两个审问者中间了,”他想。他觉得他从未这样勇气十足。
他进去的时候,两个穿戴比瓦勒诺先生还讲究的贴身男仆正在给主教大人宽衣。这位主教认为应该先同问于连的学习情况,然后再谈彼拉先生。他谈了谈教理,颇感惊奇。很快他又转向人文学科,谈到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这些名字,”于连想,“让我得了个第一九八名。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且让我出个风头。”他成功了,主教大喜,他本人就是个优秀的人文学者。
在省府的宴会上,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姑娘朗诵过一首歌颂玛大肋拉的诗。他正在谈文学的兴头上,很快便忘记了彼拉神甫和其它公事,和这位神学院学生讨论起贺拉斯是富还是穷的问题。主教引证了好几首颂歌,不过他的记忆力有时不大听使唤,于连马上就把整首诗背出来,神情却很谦卑。使主教惊讶不止的是于连始终不离闲谈的口吻,背上二、三十首拉丁诗就像谈神学院里发生的事一样。他们大谈维吉尔、西塞罗。最后,主教不能不夸奖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了。
“不可能学得更好了。”
“主教大人,”于连说,“您的神学院可以向您提供一百九十七个更配得上您的盛赞的人。”
“怎么回事?”这数字使主教很惊讶。
“我可以用官方的证据支持我有幸在主教大人面前说的话。在神学院的年度考试中,我回答的正是此时此刻获得大人赞赏的题目,我得了第一百九十八名。”
“哈!原来是彼拉神甫的宠儿呀,”主教笑着叫道,看了看德-福利莱先生;“我们早该料到的;您是光明磊落的。我的朋友,”他问于连,“是不是人家把您叫醒,打发到这儿来的?”
“是的,主教大人。我一生只走出过神学院一次,就是在圣体瞻礼那天帮助夏斯-贝尔纳神甫装饰的大教堂。”
“0ptime,”主教说,“怎么,表现出那么大的勇气,把几个羽毛束放在华盖上的就是您吗?这些羽毛束年年让我胆战心惊,我总怕它们要我一条人命。我的朋友,您前程远大;不过,我不想让您饿死在这儿,断送了您那突然光辉灿烂的前程。”
主教命人拿来饼干和马拉加酒,于连又吃又喝,德-福利莱神甫更不示弱,因为他知道主教喜欢看人吃得胃口大开,兴高采烈。
这位高级神职人员对他这一夜的余兴越来越满意,他谈了一会儿圣教史。他看出于连并不理解。他转到君士坦丁时代诸皇帝治下罗马帝国的精神状态。异教的末日曾伴有不安的怀疑的状态,这种状态现又折磨着十九世纪精神忧郁厌倦的人们。主教大人注意到于连竟至于不知道塔西陀的名字。
对于这位高级神职人员的惊异,于连老老实实回答说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没有这位作者的书。
“我的确很高兴,”主教快活地说,“您帮助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十分钟以来我一直想办法感谢您让我度过一个可爱的夜晚,当然是出乎意料。我没想到我的神学院的学生中会有这样一位饱学之士。我想送您一套塔西陀,尽管这礼物不大符合教规。”
主教让人拿来八册装璜考究的书,并在第一卷的书名上方亲自用拉丁文给于连-索莱尔写了一句赞语。主教向以写得一手漂亮拉丁文自炫;最后,他以一种与谈话截然不同的严肃口吻对他说:
“年轻人,如果您谦虚谨慎,有一天您将得到我的辖区内最好的本堂区,而且并非距我的主教府百里之遥,但是必须谦虚谨慎。”
于连抱着八册书出了主教府,大为惊奇,这时,午夜的钟声响
主教大人跟他没有一句话说到彼拉神甫。于连尤其感到惊奇的是主教极其客气。他想不到如此的文雅竟能与一种如此自然的庄严气派结合在一起。于连看到彼拉神甫正沉着脸不耐烦地等着他,那对比给他的印象尤其深刻。
Quicltibidixerunt?(他们跟您说了些什么?)”他一看见他就高声同道。
于连把主教的话译成拉丁文,越译越乱。
“说法语吧,重复主教大人的原话,不要增也不要减,”神学院前院长说,口气严厉,态度也十分地不雅。
“一位主教送给一个神学院的年轻学生一份多么奇特的礼物呀!他说,一边翻着精美的塔西陀全集,烫金的切口似乎使他感到厌恶。
两点钟响了,他听完详细汇报,让心爱的学生回房间了。
“把您的塔西陀的第一卷留给我,那上面有主教大人的赞语,”他对于连说,“我走后,这一行拉丁文将是您在这所学校里的避雷针。Erittibi,filimi,successormeustamquamleoquoerensquemdevoret.(因为对你来说,我的儿子,我的继任者将是一头狂暴的狮子,它将寻找可以吞食的人。)”
第二天早晨,于连在同学们和他说话的方式中发现了一桩奇怪的事情。他于是便不多说话了。“看,”他想,“这就是彼拉神甫辞职的后果。整个学院都知道了,我被看作是他的宠儿。在这种方式中一定含有侮辱。”不过,他看不出来。相反,他沿走廊碰见他们,他们的眼中没有了仇恨。“这是怎么回事?这肯定是个圆套。可别让他们钻空子啊。”最后那个维里埃来的小修士笑着对他说:“Cor-neliiTacitioperaomnia(塔西陀全集)。”
这句话让他们听见了,他们于是争相恭维他,不仅仅是因为他从主教那儿得到这份精美的礼物,也因为他荣幸地与主教谈话达两个钟头之久。他们连最小的细节都知道。从此,不再有嫉妒,他们卑怯地向他献殷勤:卡斯塔奈德神甫头一天还最为无礼地对待他,也来挽住他的胳膊,请他吃饭。
于连本性难移,这些粗俗的人的无礼曾经给他造成许多痛苦,他们的卑躬屈膝又引起他的厌恶,一丝儿快乐也没有。
快近中午,彼拉神甫向学生们告别,少不了又-番严厉的训话。“你们想要世间的荣誉,”他对他们说,“社会上的一切好处,发号施令的快乐,还是永恒的获救?你们中间学得最差的只要睁开眼睛就能分清这两条路。”
他一走,那些耶稣圣心派的教徒就到小教堂去唱TeDeum。神学院里没有人把前院长的训话当回事儿。“他对自己被免职极感不快,”到处都有人这么说,神学院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会天真地相信有人会自愿辞去一个与那么多大施主有联系的职位。
彼拉神甫住进贝藏松最漂亮的旅馆,借口有事要办,想在那儿住两天,其实他什么事也没有。
主教请他吃过饭了,为了打趣代理主教,还竭力让他出风头。吃饭后甜点时,传来一个奇怪的消息,彼拉神甫被任命为距首都四法里远的极好的本堂区N……的本堂神甫。善良的主教真诚地祝贺他。主教把整个这件事看成是一场玩得巧妙的游戏,因此情绪极好,极高地评价了神甫的才能。他给了他一份用拉丁文写的、极好的证明书,并且不让竟敢提出异议的德-福利莱神甫说话。
晚上,主教在德-吕班普莱侯爵夫人处盛赞彼拉神甫。这在贝藏松的上流社会中是一大新闻;人们越猜越糊涂,怎么会得到这样不寻常的恩宠。有人已经看见彼拉神甫当了主教了。最精明的那些人认为是德-拉莫尔先生当了部长了,所以那一天敢于嘲笑德-福利莱神甫在上流社会作出的跋扈神态。
第二天早晨,彼拉神甫去见审理侯爵案子的法官们,人们几乎在街上尾随他,商人们也站在自家店铺的门口。他第一次受到礼貌的接待。严厉的詹森派信徒对他看到的这一切非常愤怒,跟他为侯爵挑选的那些律师们仔细地讨论了一番,就启程去巴黎,只有两、三个中学时代的朋友一直送他到马车旁,对马车上的纹章赞叹不己。他一时糊涂,竟对他们说,他管理神学院十五年,离开贝藏松时身上只有五百二十-法郎积蓄。这几位朋友流着泪拥抱了他,私下却说:“善良的神甫本可以不说这谎话,这也太可笑了。”
庸俗的人被金钱之爱蒙住眼睛,本不能理解,彼拉神甫正是从他的真诚中汲取必须的力量,六年中单枪匹马地反对玛丽-阿拉科克、耶稣圣心派、耶稣会士们和他自己的主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