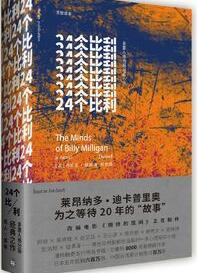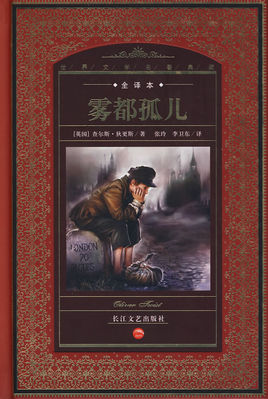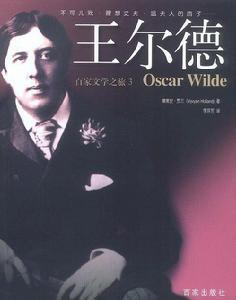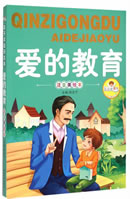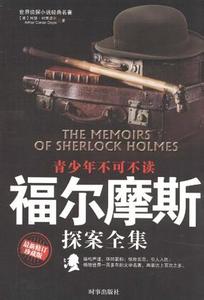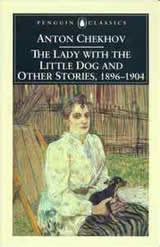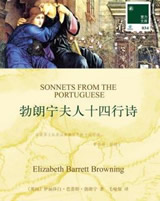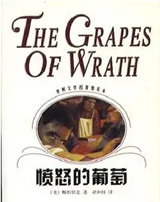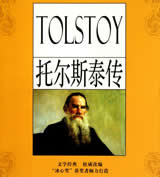装载过重的旧哈得逊车吱咯吱咯上了公路,向西开会。奥尔专心致志地把握着方向盘。十奶十奶十在他旁边的座位上迷迷糊糊打瞌睡。十妈十坐在十奶十奶十身边,望着前方。奥尔叹气说:“载这么重,天晓得怎么开上山去。十妈十,这几去加利福尼亚,路上有山吗?”
“听说要过几座山,”十妈十说,“甚至有大山。很大的山。”
“爬山的话,这辆车马上会起火。咱们只好扔掉几件东西了,”奥尔说。
接着又问:“十妈十,你担心吗?去那个新地方,你担心吗?”
“有点儿,”十妈十沉思他说。“不过也不怎么担心。我在这儿等着,万一出了什么事,要我做点儿什么,我就尽力去做。”
“你有没有想咱们到了那儿会怎么样?担不担心事情不象咱们料想的那样顺利?”
“不,”她很诀回答。“头绪太多,没法想。往后有种种可能,不过最后无非是那么回事,要是事先都想过来,实在太多了。你年轻,有奔头,我呢,只有在一旁看着,只能顾到什么时候该让大家再吃点肉骨头。我只能想这些,不能想别的了。要是我想得太多,大伙儿就得着急了,他们就指望我只顾到这一点儿。”
十奶十奶十打了个呵欠,睁开眼睛,四下望望,慌张他说:“我要下去。”奥尔说,前面不远有个林子,一到那儿就让她下去。十奶十奶十哭叫着:“管林子不林子,我得下去,我得下去。”奥尔加快速度,在树林边上煞住车。十妈十半扶半拉地把十奶十奶十搀进树林,又扶着她蹲下十身去。其余的人都下车活动活动。爷爷醒来。汤姆问:“你想下来吗,爷爷?”“不,我不走,”那双老眼里又露出了凶相,“我要象慕莱那样耽在这儿!”然后又心灰意懒,不说话了。十妈十扶着十奶十奶十回来了。她让汤姆分些肉骨头给大家吃,爸想喝水,可是找来找去没找着那只盛水的瓶子。温菲尔德也嚷起渴来,引起大家一阵小小的恐慌。奥尔说:“到站头就能弄到水。咱们还得买点汽油。”一家子重新上车,奥尔开动了马达。公路旁有所小屋,屋前有两个汽油泵,篱笆边上还有个装着皮管的水龙头。奥尔把车开过去。一个胖子从汽油泵后面的椅子上站起身,向他们走来,露出一副凶相。“你们打算买东西吗?买汽油还是什么?”
“加点汽油,老板,”奥尔下车说。
“有钱吗?”
“当然有。你当我们是来向你讨呜?”
胖子脸上那副凶狠的神气消失了。“那就好,老乡。你们尽管用水。”
他解释说,过路的人多极了。他们啥也不买。来这几用了水,把茅房搞得稀脏,临了讨一加仑汽油就赶路。温菲尔德衔十住皮管喝了水,接着又冲头冲脸。汤姆和凯绥也先后冲洗了一会。十妈十从车栏的横挡中间伸出手来,用洋铁杯接了水给十奶十奶十喝,然后把杯子递给爷爷。爷爷只润了润嘴唇,摇摇头,不想喝了。奥尔旋开卡车的水箱盖,一股蒸汽直住上冲。车顶上那条受罪的猎狗怯生生地爬到行李边上,望着水汪汪地叫。约翰叔叔爬上去,揪住颈十毛十把它提下车子。那条狗十腿十都僵了,摇摇晃晃地走到水龙头底下,去喝那泥浆水。公路上,一辆辆汽车飕飕地飞驰而过。康尼和罗撒香站在皮管旁边。康尼洗干净洋铁杯,先用手指试了试水的温度,盛满水递给罗撒香说:“这水不凉,还好喝。”罗撒香望着康尼,笑了笑。她自从怀了十孕十,一举一动都有点几神秘的意味。对罗撒香的怀十孕十,康尼充满了惊奇的感觉,每逢罗撤香俏皮地微笑,他也就俏皮地微笑起来。他们俩咬着耳朵说知心恬,世界紧紧地围绕着他们,他们俩成了世界的中心,或者不如说,罗撒香成了世界的中心,康尼在她的周围转着圈子。
那条狗喝够水,垂着耳朵低头走开。它一路嗅着走到公路边,抬头住对面看了一眼,朝对面窜去。罗撒香惊叫一声,一辆大汽车飞快开来,轮胎叽地一响,那条狗躲也来不及了,一声尖十叫,车轮拦腰辗了过去。罗撒香睁大双眼,哀求地问:“你看会不会吓出十毛十病来?会不会吓出十毛十病来?”康尼用一条胳膊搂住她,说:“快坐下,不要紧。”
“可是我觉得吓坏了。我喊的时候,肚子里好象动了一下。”
汤姆和约翰叔叔走到血肉模糊的死狗身旁,汤姆拉着一条狗十腿十,把它拖到路边。约翰叔叔十内十疚他说:“我该把它拴起来的。”爸低下头朝死狗望了一会,就转过脸说:“咱们离开这儿吧。反正不知道怎么养活它,压死了也好。”胖子说:“你们别为这事难过。我来照料这条死狗,把它埋在玉米地里。”
罗撒香坐在卡车的踏板上:还在哆嗦。十妈十走到她眼前问,“你觉得不好过吗?”“我吃了一惊,你看会不会出十毛十病?”“不会。要是你老难受,拼命往坏处想,那也许会出十毛十病,把肚子里的宝贝暂且忘掉一会儿,它会照顾自己的。”
汤姆说:“咱们走吧,还得赶许多路呢。”
后来这段路,奥尔上了车顶,由汤姆开车。车子穿过俄克拉何马市区,不多一会就上了六六公路。汤姆对十妈十说:“往前去咱们就一直在这条公路上走了。”十妈十说:“最好在天黑以前找个地方停车。我得把猪肉煮一煮,再做点面包。”汤姆同意说:“行。反正不是一下子就到得了的,不妨早点儿休息。”
太十陽十渐渐沉落。十妈十猛地抬头说:“汤姆,你爸跟我说起过你越过州界的问题——”
汤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答活:“有啥问题呢,十妈十?”
“我担心这一来你好象成了逃犯,说不定要抓你。”
“别担心。我想过了。要是我在西部出了什么事给抓起来,那么他们就会把我的照片和手印调来,把我押解回去。要是我不犯法,也们也就不会管我了。”
“我哪能不担心。有时候一个人说是犯了法,他自己还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只伯加利福尼亚有些罪名,咱们压根儿没听说过。说不定你做的并没有错,在加利福尼亚却是犯法的。”
“就算我不是具结释放的,事情不也是一样。无非我要是给抓起来,罪名比别人重一些罢了。你先别愁,可愁的事已经够多了。”
“我只伯你越过州界就算犯罪。”
“那总比留在乡下俄死的好。咱们还是找个地方停车吧。”
一辆旧旅行车停在田野上,车旁支着个帐篷,帐篷顶上的烟筒里冒着烟。一个中年男人揭开了旅行车的车盖,在那里检查马达。汤姆把卡车开过去,从车窗里探身出去问:“有没有禁止在这儿停车过夜的规定?”那中年男人回答说:“不知道。车子开不动了,我们只好停在这儿的。”
“这儿有水吗?”
那人指着前面不远一个服务沾的小屋。“那儿有水,肯给你用一桶。”
“咱们能把车子停在上块儿吗?”
“这不是我们的地方。”
“你们已经停支这儿了。你有权说是不是愿意要我们做邻居。”
那张显得有些为难的瘦脸露出了笑容:“当然愿意。下公路来吧。绥莉,有几个人要来眼咱们搭伴。你出来打个招呼吧。”他向帐篷里喊道,又补了句:“绥莉不大舒服。”
帐篷的门帘撩十开,走出一个惟悻的妇人来,轻柔他说:“欢迎他们来吧。非常欢迎。”
汤姆把军子开进田野,和那辆淀行车并排停下。车上的人立刻下来。十妈十解下水桶,让露西和温菲尔德去服务站抬水。爸和那瘦子攀谈说:“你们不是俄克拉何马人吧?”“我们是迦仑那人。我叫威尔逊,艾威·威尔逊。”“我们姓约德。从萨利凛附近来的。”
诺亚、约翰叔叔和牧师扶爷爷下车,让他坐在地上。爷爷有气无力地坐下,直愣愣地瞪着眼睛。“你病了吗,爷爷?”诺亚问。“不错,病了。都快死了。”
绥莉·威尔逊走到爷爷身边。“上帐篷里去吧,你可以躺在我们床垫上歇歇。”爷爷被那温和的声音吸引了,抬起头来看看;忽然下巴颤十抖,瘪嘴闭得紧紧的,呜呜地哭起来了。十妈十连忙过去,用宽阔的背背起爷爷送进帐篷。约翰叔叔说:“这病不轻,我一辈子没见他哭过。”他跳上卡车,搬下一条床垫来。十妈十从帐篷里出来,走到凯绥眼前,说:“你过去常接近病人。爷爷病了,你去看看好吗?”凯绥急忙走进帐篷。爷爷仰面躺在一条双人床垫上,两颊通红,喘着气。绥莉·威尔逊跪在一旁。帐篷里还有只铁皮炉,一桶水,一箱粮食和一只当桌子用的木箱,此外啥也没有了。凯绥捏住老人皮包骨头的手腕,问:“觉得累吗,爷爷?”老人的那双通红的眼睛寻着声音传过来,并没看见他,颤十抖的嘴唇仿佛要说话,可是没说出声来。绥莉轻轻对凯绥说:“你知道这是什么病?”
“你是说一他可能是中风?”凯绥问。
“也许是,这种病我见过三回。”
十妈十撩十开帐门向里张望:“十奶十奶十要进来,行吗?”
“别让她进来,她会着急的。”凯绥说。
“你看爷爷不要紧吧?”
凯绥缓慢地掇摇头。十妈十看青老人那张痛苦的充十血的脸,退出去对十奶十奶十说:“他好了,十奶十奶十。他只是要歇会儿。”
十奶十奶十沉着脸说:“我要看看他。他是个老滑头,从不说真话。”她钻进帐篷,站在床垫边上弯腰问:“你怎么啦?”爷爷的眼睛又朝她的声音转过来,嘴唇十抽十动着。十奶十奶十说:“他生气呢。我早说他很滑头。今儿早上他想溜,不肯来。这会儿又发脾气。过去他不理人家的时候就这个样。”凯绥轻声对十奶十奶十说:“不是发脾气,他病了,病得很童。”十奶十奶十迟疑了一会,忙说:“那你千吗不做祷告?”你不是牧师吗?”凯绥说:“我跟你说过,我已经不是牧师了。”
爷爷手脚乱动,仿佛在挣扎。忽然,他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刺耳地一声叫,就安静地躺在那里,停止了呼吸。他的脸渐渐变成紫黑十色十。绥莉推推凯绥的肩膀,悄悄说:“舌头,他的舌头。”凯绥点点头。“你挡住十奶十奶十。”他扳十开爷爷紧闭的牙床,仲手去掏舌头。他把舌头一拽,喉咙里就发出呼噜呼噜的呼吸声。凯缓在地上找到根小棍,用小棍按住那舌头,不匀的呼吸声呼噜呼噜地延续着。十奶十奶十踉小鸡似的跳来跳去。大声嚷道:“祷告吧,求求你。我求你做祷告,你这家伙!”
凯绥抬头朝她望了一会。“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圣名——”
“好,好!”十奶十奶十喊。爷爷张开的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喘十息,然后又叫了一声,就断气了。“接着祷告呀,”十奶十奶十说。
“亚门。”凯绥说。
十奶十奶十不做声了。帐篷外所有嘈杂的声音也都停了下来。绥莉扶着十奶十奶十的臂膀,把她牵到外面。十奶十奶十庄严地移动脚步,把头抬得高高的。她代表全家这么走,代表全家这么昂着头。帐篷里寂静无声,凯绥终于撩十开帐门,踱了出来。
爸低声问:“什么病?”
“中风,”凯绥说。“急十性十中风。”
现在爸是一家之长了。他向威尔逊夫妇表示了谢意。然后说:“咱们想想该怎么办,接法律得去报丧,他们要收四十元,安葬费,不然就把他当叫花子处理。咱们只有一百五十块钱,给他们拿走四十块去葬爷爷,咱们就到不了加利福尼亚了——”
男人们焦躁不安地望着眼前那片逐渐暗下去的地面。爸柔声他说:“爷爷亲手埋了他的爸,搞得很体面。那时候,一个人有权让亲生的儿子埋葬他,做儿子的也有权埋他的父亲。”
“法律如今不同了。”约翰叔叔说。
“有时候只好不管法律,”爸说。“我是说,我有权埋葬我的父亲。谁有话说吗?”
凯绥说:“不得不做的事,你有权去做。”
爸问约翰叔叔:“你也有权呀。你反对吗?”
“不,不反对。只是这好象把他偷偷藏了起来。爷爷做事向来是光明正大的。”
爸不好意思他说:“我们没法照爷爷那么做了。我们得趁钱没花光前赶到加利福尼亚。”
汤姆插嘴说:“政十府对死人比活人关心,要是有人挖出了十尸十体,他们会大惊小怪当作谋杀案,调查他是谁,怎么死的。我主张写张纸条放在瓶里,跟爷爷埋在一起。讲明他是谁,怎么死的,为什么葬在这儿。”
爸认为汤姆的办法很好,爷爷知道跟自己的名字埋在一起,也不会过于觉得凄凉。
十妈十问爸要了两枚半元的银币,端了盆水进帐篷去给爷爷装殓。帐篷里几乎全黑了,绥莉进来点上支蜡烛,又出去跟罗撒香一起做晚饭。十妈十低头看了一会死去的老人,满怀怜恤地从自己的围裙上撕下一条布,把爷爷的下巴捆起来,把他的两只手交叉放在十胸十前,又给他十摸十平眼皮,每只眼睛放上一枚银币。
绥莉探进头来问:“要我帮忙吗?”十妈十说:“请进来,我正想我你。我想给爷爷全身抹一抹,可是没有农裳好换了。再说,你的被子也弄脏了。就用你的被子把爷爷裹起来吧。我们另赔给你一条。”绥莉说:“哪儿的话,我们很乐意帮忙。我心里好久没有觉得这样踏实了。谁都该帮助别人。”
十妈十仔细包裹好爷爷,扯起一个被角,蒙住爷爷的头。绥莉递给她六七很大别针,说:“老太太倒还想得开。”十妈十用别针把被子别牢,说:“她年纪太大了,只怕还不太清楚出了什么事。再说,我们这些人忍耐惯了。爷爷这样落葬也不坏了,有牧师看着他进坟墓,亲人也都在身边。”她站起来,忽然身十子一晃,绥莉连忙把她扶住。十妈十不好意思他说:“没啥,困了,你知道,前一阵收拾动身就忙得够呛。”
她们俩走出帐篷。罗撒香在篝火旁烧开水,见十妈十出来,上前问道:“十妈十,我问你——”十妈十说:“又受惊了?唉,你想一点不愁,太太平平渡过九个月,那是办不到的。”“这会不会影响孩子?”“有句老话,‘愁里生下来的孩子日后有福气’。是吗,威尔逊太太?”“我还听说过另一句话:‘生出的时候太快活,长大了十爱十发愁’。”绥莉说。
男人们轮流在刨坑。刨到齐肩深的时候,爸让汤姆去写那纸条,其余的人继续往下刨。绥莉借给汤姆半截铅笔,还拿来本《圣经》,说:“这书前头有张白纸,你写在那上头,撕下来就是了。”汤姆在书后的扉页上写了些老大的字,写好了念给十妈十听:“这人叫威廉·詹姆士·约德,他的家人没钱交丧葬费,把他葬在这儿,他不是给杀害的,是中风死的。”十妈十觉得写得不坏,让添上几句《圣经》里的话,增加点宗教意味。找来找去,选了这么一句:“过失被饶忽的人,罪恶被遍掇的人,有福了。”十妈十洗干净一只水果瓶,把纸条装进瓶里,把瓶子塞十进裹十着爷爷的那个被子包里。十奶十奶十好象睡着了,其余的人都站在墓十穴十边。爸对凯缓说:“你肯不肯讲几句?我们乡里安葬死人,从来不兴不做祷告。”凯绥不愿意冒充牧师骗人,可是很想给这一家子帮个忙,答应说:“我来说几句吧。”他低下头,大伙儿跟着都低下头来。凯绥庄严他说:“这位老人度过一生,死了。如今,他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们却有上千条路,还不知道该走哪条。做祷告的话,我应当给那些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的人做祷告。爷爷走上了平坦的大道。给他盖上土,让他去干他的事吧。”凯绥抬起头来。爸说了声:“亚门。”其余的人都轻轻说了声:“亚门。”于是一个接一个在墓十穴十里撒上。露西和温菲尔德在一旁聚十精十会神地看着。露西严肃他说:“爷爷躺在那下十面了。”温菲尔德惊恐地看看露西,然后到篝火边,坐在地上,暗自哭起来。
两家人围着篝火一起坐下来吃晚饭。十奶十奶十躺在离火远一点的床垫上哇哇地哭了。十妈十说:“这会儿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罗撒香,乖,躺在十奶十奶十身边去陪陪她吧。”罗撒香去了。诺亚说:“真怪。爷爷死了,我并不比先前更难受。”凯绥说:“爷爷和老家是一回事。他不是刚才死的。你们带他离开老家那时候,他就死了。他想着家乡的土地;离不开那儿。”
威尔逊说,他们也不得不把哥哥甩在老家。他哥哥本来也买了辆汽车打算走的,可是他和威尔逊一样不会开车,临时我了个小伙子教他开。一天下午,他去试车,到了大路转弯的地方,他“哎哟”一声喊,猛一退,车子撞进了篱笆:又“哎哟”一声喊,打开油门,车子翻进沟里再也开不动了,他气得发疯,简直没了主意,却又不肯跟威尔逊走。威尔逊只有八十五块钱盘缠,不能耽在那儿等,只好顾自动身。动身没走一百哩,车后面的一个齿轮就坏了,花三十块钱配了一个,后来又得配条车胎,后来火花塞又炸裂了,绥莉又病倒了,不得不停下来十天。这样走走停停,已经走了三星期了。奥尔问了问车子的情形,自告奋勇,愿意帮威尔逊修车。威尔逊感激不尽,说:“不会修车,真觉得自己就象小孩那样不中用。等到了加利福尼亚,我一定要买辆好车,也许就不会抛错了。”爸说:“难就难在怎么到得了那里。”
这时候,奥尔限汤姆同时想到个主意。奥尔对汤姆说:“你跟大家说吧。”
汤姆说:“我们的车子装得过重了,威尔逊夫妇的还不太重。我们分几个人坐在他们的车上,把他们轻便的行李分些到卡车上来,我们的车就能爬山了。
对汽车,我和奥尔都十内十行,保管能叫那辆旧旅行车走好。咱们一路在一起开,大家都好。”
威尔逊夫妇高兴极了,却叉担心自己只剩三十块钱,会不会拖累了约德一家。十妈十说:“不会拖累我们的。咱们互相帮忙,就都能到达加利福尼亚。”
绥莉说:“要是半路上我又病倒了,你们就赶你们的路,我们可不能拖累你们。”十妈十说:“我们会照顾你的。你不是说过,不能眼看着别人有困难不帮忙吗?”
商量定当,两家人各自去睡觉。十妈十说:“爷爷——他好象死了有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