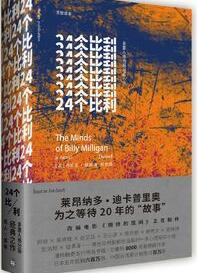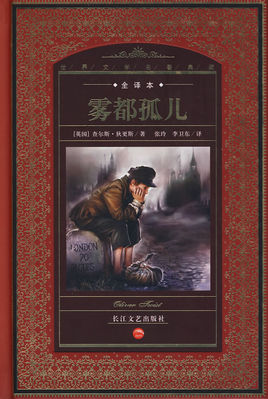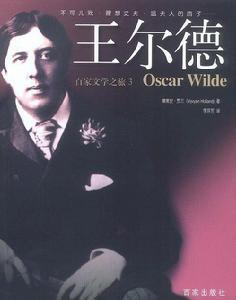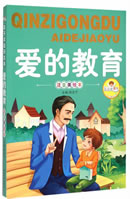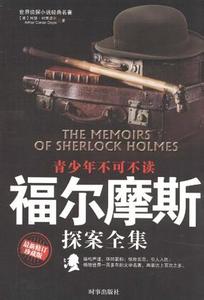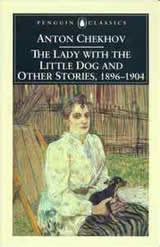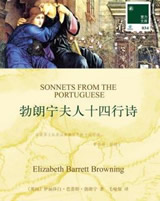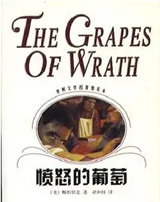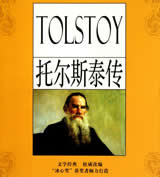过了两天以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照她所答应的,带着她家的所有年轻人来到了瓦西利耶夫村。小姑一娘一们立刻跑到花园里去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懒洋洋地到所有房间里看了看,对一切都懒洋洋地称赞了一番。她认为自己来拜访拉夫烈茨基是十分体谅他,几乎是一种善举。当安东和阿普拉克谢娅按照一奴一仆的老一习一惯来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和蔼可亲地微微一笑,――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带着鼻音要求喝茶。戴了一副针织白手套的安东感到极为懊丧的是,给前来做客的夫人献茶的不是他,而是拉夫烈茨基雇用的侍仆,用这个老头子的话来说,一个什么规矩也不懂的家伙。然而吃午饭的时候安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坚定地站到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安乐椅后面――已经不肯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任何人了。瓦西利耶夫村里很久没有客人来了,现在破天荒地来了客人,这既让老头子感到惶恐不安,也让他觉得愉快:他很高兴看到,有些很好的老爷太太们与他的主人来往。不过那天心情兴奋的不仅是他一个人:列姆心情也很兴奋。他穿了一件后面拖着条小尾巴、有点儿嫌短的、淡褐色的燕尾服,紧紧地打了一条领带,而且不断地咳嗽一下,清清嗓子,脸上带着愉快和亲切的表情谦让着退到一边去。拉夫烈茨基很高兴地发觉,他和莉莎的接近仍然在继续:她一进来就友好地向他伸出了手。午饭后,列姆不时把一只手伸到燕尾服后面的口袋里,从里面掏出不大的一卷乐谱纸,闭紧嘴唇,默默地把它放到了钢琴上。这是他昨晚谱写的一首抒情歌曲,歌词是一首已经不流行的德文诗,里面提到了星星。莉莎立刻坐到钢琴前,看着谱弹奏这首抒情歌曲……可惜!乐曲显得紊乱,紧张得让人感到不快;看来,作曲者努力想表现某种极其强烈、深厚的感情,可是什么也没能表现出来:努力仍然只不过是努力而已。拉夫烈茨基和莉莎两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列姆也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一言不发,把自己的抒情歌曲放回口袋里去,对莉莎再弹一遍的提议,却只是抓了摇头,作为回答,意味深长地说:“现在――
完了!”说罢,弯腰拱背,全身蜷缩起来,走开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大伙儿一起去钓鱼。花园后面的池塘里有许多鲫鱼和红点鲑鱼。在池塘边树荫下放了一把安乐椅,让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坐在安乐椅上,在她脚下铺了一块地毯,给了她一根最好的钓竿;安东作为有经验的钓鱼老手,表示愿意为她效劳。他热心地装上钓饵,用一只手拍拍它,朝它吐口唾沫,甚至姿态优美地全身俯向前面,亲手把钓竿甩出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当天对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谈起他的时候,用贵族女子中学里学生腔的法语说了如下的一句话:“IIn’yaplusmaintenantdecesgenscommecacommeautrefois”①。列姆和两个小姑一娘一走得远一些,一直走到了池塘堤边;拉夫烈茨基坐到莉莎旁边。鱼不断地上钩;拉上来的一条条鲫鱼划过空中,有时金光灿灿,有时银光闪闪;两个小姑一娘一高声赞叹,欢呼声从未间断;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也文雅地尖一叫过两次。拉夫烈茨基和莉莎那儿,鱼儿上钩的次数最少;大概这是因为他们最不注意钓鱼,让自己的浮子漂到池塘岸边的缘故。微微发红的芦苇在他们周围轻轻地籁籁作响,前面,一池止水静静地闪闪发光,他们的谈话也是轻声细语,平静安详。莉莎站在搭在岸边的一个小木台上;拉夫烈茨基坐在一棵弯向水面的爆竹柳树干上;莉莎穿一件白色连衫裙,腰间系一条也是白色的宽带子;一顶草帽挎在她的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有点儿吃力地扶着容易弯曲的钓竿梢。拉夫烈茨基望着她轮廓清晰、神情有点儿严肃的面部侧影,望着她撩到耳后的长发,望着她像孩子那样红通通的、娇一嫩的面颊,心想:“噢,你站在我的池塘边,看上去多可一爱一呀!”莉莎没有转过脸来看他,而是望着水面,不知是眯缝着眼呢,还 是在微笑。附近一棵椴树的树荫落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①法语:意思是:“现在再没有以前那样的仆人了”。
“您知道吗,”拉夫烈茨基开口说,“对我和您的最后一次谈话,我想得很多,而且得出结论,您非常善良。”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莉莎不同意他的话,而且感到不好意思了。
“您是善良的,”拉夫烈茨基又说了一遍。“我是个笨人,可是我也觉得,大家一定都会喜欢您。就拿列姆来说吧;他喜欢您简直是喜欢得入迷了。”
莉莎的眉一毛一与其说是皱了起来,倒不如说是抖动了一下;
每当她听到什么感到不快的话时,她总是会这样。
“今天我觉得他很可怜,”拉夫烈茨基接着说,“他的抒情歌曲写得不成功。要是还 年轻,而不善于谱曲,――这还 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年老了,还 没有能力了――这就让人难以忍受了。不是吗,一精一力在慢慢消失,你却感觉不到这一点,这是让人很难过的。老人很难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当心,您那儿鱼上钩了……据说,”稍沉默了一会儿,拉夫烈茨基又补上一句,“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写了一首很好听的抒情歌曲。”
“是的,”莉莎回答,“这是首小玩意儿,不过还 不错。”
“怎么样,照您看,”拉夫烈茨基问,“他是个很好的音乐家吗?”
“我觉得,他很有音乐才能;不过至今还 没在这上面好好地下过功夫。”
“是这样。可是他这个人好吗?”
莉莎笑了起来,朝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很快地看了一眼。
“一个多么奇怪的问题!”她提高声音说,把钓竿往上一拉,又把它远远地甩了出去。
“为什么奇怪呢?我是作为一个不久前才来到这里的人,作为您的亲戚,才向您问起他的。”
“作为亲戚?”
“是啊。不是吗,我好像是您的表叔①吧?”
“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有一颗善良的心,”莉莎说,“他聪明;maman②很喜欢他。”――
①前面拉夫烈茨基曾对列姆说,莉莎是他的“表妹”。
②法语,意思是:“一妈一妈一”。
“那您喜欢他吗?”
“他是个好人;我为什么要不喜欢他呢?”
“啊!”拉夫烈茨基低声说,然后不说话了。一种半是忧郁、半是嘲讽的神情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他那目不转睛凝望着她的目光让莉莎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她仍然微笑着。“好吧,愿上帝赐给他们幸福!”最后他仿佛自言自语似地,低声含含糊糊地说,于是扭过头去。
莉莎脸红了。
“您弄错了,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她说,“您这样想是没有根据的……可难道您不喜欢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吗?”她突然问。
“不喜欢。”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心肝。”
笑容从莉莎脸上消失了。
“您一习一惯严厉地指责别人,”沉默了好久以后,她犹豫地说。
“我倒不这样认为。得了吧,既然我自己需要别人一体谅,我还 有什么权利严厉地指责别人呢?莫非您忘了,只有懒汉才不嘲笑我?……怎么,”他又加上一句,“您履行自己的诺言了吗?”
“什么诺言?”
“您为我祈祷了吗?”
“是的,我为您祈祷过,而且每天都为您祈祷。可是,请您不要轻率地谈这件事。”
拉夫烈茨基开始向莉莎保证,说他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说他深深尊重各种信仰;随后他又谈起宗教来,阐明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基督教的作用……
“人应该是基督徒,”莉莎并非一点儿也不紧张地说,“并不是为了明白天上……还 是……人间……,而是为了,每个人都有一死。”
拉夫烈茨基带着不由自主的惊讶神情抬起眼来看莉莎,正好碰到了她的目光。
“您这是说了句什么话啊!”他说。
“这话不是我说的,”她回答。
“不是您说的……可是您为什么说起死来了?”
“我不知道。我常常想到死。”
“常常?”
“是的。”
“瞧您现在这个样子:您的面容这么愉快,这样开朗,您在微笑……您是绝不会说这种话的……”
“是的,现在我很愉快,”莉莎天真地回答。
拉夫烈茨基真想抓住她的两只手,紧紧攥一住它们……“莉莎,莉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大声喊,“到这儿来呀,你看,我钓到了一条多大的鲫鱼。”
“就来,mamam,”莉莎回答,于是到她那里去了,拉夫烈茨基却仍然坐在他那棵爆竹柳上。“我跟她说话,好像我并不是一个已经心灰意冷的人,”他想。莉莎走开的时候,把自己的草帽挂在了一根树枝上;拉夫烈茨基怀着一种奇怪的、几乎是一温一柔的感情瞅了瞅这顶帽子,瞅了瞅帽子上有点儿一揉一皱了的长飘带。莉莎很快回到他这里来,又站到了那个小木台上。
“您为什么觉得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没有心肝?“稍过了一会儿,她问。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可能看错了;不过,时间会证明一切。”
莉莎沉思起来。拉夫烈茨基谈起了自己在瓦西利耶夫村的生活情况,谈起了米哈列维奇,谈起了安东;他觉得自己渴望和莉莎说话,渴望把心里想到的一切都告诉她:她是那么可一爱一,那么注意地听着他说话;她偶尔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不同看法,他觉得是那么单纯和聪明。他甚至把这一点告诉了她。
莉莎感到惊讶。
“真的吗?”她低声说,“可我常这么想,我和我的使女娜斯嘉一样,没有自己的话。有一次她对自己的未婚夫说:你跟我在一起大概会觉得无聊;你对我说的话都那么好听,可我却没有我自己的话。”
“说得真好!”拉夫烈茨基心里想――
转载请保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