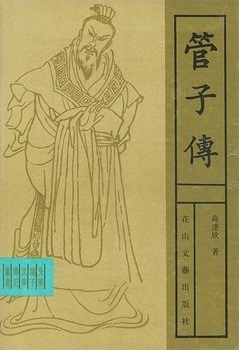第三部(1) 灯火楼台 第六章(1)
十天以后,罗四姐接到了家信;罗大娘照她的话,是请乌先生代写的。这乌先生是关帝庙祝,为人热心,洞明世事,先看了罗四姐的来信,心头有个疑问,何 以回信要指定他来写。再原罗大娘眉飞色舞地谈胡雪岩来看她的情形,恍然大悟,罗四姐大约不能确定,胡雪岩会不会亲自来看罗大娘,所以信中不说信件等物托何 人所带。不过胡雪岩的动静,在她是很关心的;既然如此就要详详细细告诉她。她之指明要自己替罗大娘写回信,她正是这个道理。
这完全猜对了罗四姐的心思,因此,她的信也就深符她的期待了。乌先生的代笔,浅显明白;罗四姐先找老马来念给她听过,自己也好好下了一番工夫,等大致可以看得懂了,才揣着信支看七姑奶奶。
“七姐,”她说,“我有封信,请你给我看看。”“哪个的信?”
“我娘的信。我一看信很长,当中好象提到胡大先生,我怕有要紧话在里头,不方便叫老马给我看。”
“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你看不明白,我也未见得看得懂。不过,不要紧,一客不烦二主,当初你是托应春替你写的,现在仍旧叫他来看好了。“七姐夫在家?”
“在家。”七姑奶奶答说:“有个洋人来看他,他在等。”于是古应春找了来,拿信交了给他;他一面看,一百讲:“东西都收到了,胡大先生还送了一份很厚的礼,一共八样,火腿、茶叶、花雕----”
“这不要念了。”七姑奶奶插嘴问道:“他信里称小爷叔,是叫胡大先生?”
“是啊!杭州人之中,尊敬小爷叔的,都是这样叫他的。”“好!你再讲下去。”
“五月初七胡大先生去看你母亲,非常客气,坐了足足有一个时辰,谈起在上海的近况----”讲到这里,古应春笑笑顿住了。
“咦!”七姑奶奶诧异地问:“啥好笑?”
“信上说,你母亲知道你认识了我们两个,说是欣遇贵人。”古应春谦虚着,“实在不敢当。”
“我娘的话不错。你们两位当然是我的贵人。”罗四姐问道:“七姐夫,信上好象还提到我女儿。”
“是的。你母亲说,胡大先生很喜欢你女儿,问长问短,说了好些话。还送了一份见面礼,是一又绞丝的金镯子。”“你看!”罗四姐对七姑奶奶说,“大先 生对伢儿们,给这样贵重的东西,不过,七姐,我倒不大懂了,大先生怎么会将这双镯子带在身边?莫非他去之前,就晓得我有个女儿?”“不见得。”七姑奶奶答 说,“我们小爷叔应酬多,金表、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遇到要送见面礼,拿出来就是。”“原来这样子的。”罗四姐的疑团一释,“开姐夫,请你再讲。”
“你娘说,你说要回去,她也很想念你;如果你抽不出工夫,或者她到上海来看你。”
罗四姐还未开口,开姑奶奶先就喊了出来,“来嘛!”她说,“把你娘接了来歇夏,住两三个月再回去。”“上海是比杭州要凉快些。”罗四姐点点头:“等我来想想。”
“后面还有段话,是乌先生附笔,很有意思!”古应春微笑着,“他说,自从胡大先生亲监府上以后,连日庙中茶客议论纷纷,都说胡大先生厚道。照他看,胡大先生是你命中的贵人,亦未可知。”
这话触及罗四姐心底深处,再沉着也不由得脸一红;七姑奶奶非常识趣,故意把话扯了开去,“什么庙中茶客?”她问:“什么庙?”
“关帝庙,就在我家邻近。替我娘写这封信的乌先生,是那里的庙祝,靠平常摆桌子卖茶、说大书,关帝庙的香火才有着落。”
正谈到此处,洋人来拜访古应春了。在他会客时,罗四姐与七姑奶奶的话题未断,她也很想接她母亲来住,苦夫便人可以护送。七姑奶奶认为这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写信给胡雪岩就是。
“不好!”罗四姐只是摇头,却不说为何不好,及至七姑奶奶追问时,她才答说:我欠他的情太多了。”“已经多了,何防再欠一回”
“我怕还不情。”
“那也有办法----”
七姑奶奶想一想,还是不必说得太露骨,罗四姐也没有再问,这件事就暂且搁下来了。
谈了些闲话,到了上灯时分,七姑奶奶提议,早点吃晚饭;饭后去看西洋来的马戏。罗四姐答应在她家吃饭,但不想去看马戏;因为散戏已晚,劳她远送回家,于心不安。“那还不好办?你住在我这里好了。我们还可以谈谈。”
罗四姐想了一下,终于接受邀约。饭后看马戏回来,古应春也刚刚到家。
“阿七,请你替我收拾收拾行李。”他说:今天来的洋人,是德国洋行新来的总管。他说要专程到杭州去拜访小爷叔,顺便逛西湖,我只好陪他一趟。”
“怎么?”七姑奶奶高兴地说:“你要到杭州!好极,好极!你把罗四姐的老太太带了来。”
古应春楞了一下,想到罗大娘信中的话,方始会意,欣然答说:“好、好!我一定办到。”
他们夫妇已经这样作了决定,罗四姐除了道谢,别无话说。接着便谈行程;古应春计算,来到约须半个月。七姑奶奶便又出了主意。
“你索性搬到大英地界来住,我们来去也方便。”她说:“寻房带搬家,有半个月。尽够了。”
“嗯,嗯。等我想一想。”
“你不必想等我来替你想。”七姑奶奶是在想,有什么熟人的房子,或租,或买,一切方便;思索了一回,想到了,“老宓不是在造弄堂房子?”她问,“完工了没有?”“老早完工了。”
“他那条弄堂,一共廿四家,算是条很长的弄堂,我想一定有的。”
“那好。”七姑奶奶转脸对罗四姐说:“老宓是阜康的二伙,现在也发财了。是他的房子,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搬进去住。”“看看,看看!罗四姐急忙否定,“我想另外寻,比较好。”“为啥呢?”
罗四姐不答,只是摇头,七姑奶奶终于想到了,在此她跟胡雪岩的关系,正当微妙的时刻,她是有意要避嫌疑,免得太着痕迹。
七姑奶奶觉得四罗姐人虽精明能干,而且也很重义气交情,但不免有些做作。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遇到这种情形,有她一套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是罗四姐所 做不到的。“我不管你那颗玲珑七巧心,九弯十转在想点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你搬家了。房子呢,或租、或典或买下来,我来替你作主,你不必管。”
罗四姐反倒服帖了,“七姐,”她说:“我就听你的话,一切不管,请你费心。”
于是七姑奶奶独断独行,为她买了阜康钱庄二伙老宓新造的“弄堂房子”。这条弄堂名叫富厚里,二十四户,望衡对宇,两面可通,七姑奶奶挑定的一户,坐 北朝南,楼下东西厢房,大客厅;后面是“灶披间”、下房、储藏室。扶梯设在中间,楼上大小五个房间,最大的一个,由南到北,直通到底,是个套房,足供妖。 另外四间一间起坐,一间饭厅,两间客房具摆设藏家具摆饰,亦都是七姑奶奶亲自挑选,布饰得富丽堂皇,着实令人喜爱。
前后不过十天工夫,诸事妥帖,七姑奶奶自己也很得意。第十一天早上,派马车将罗四姐接了来,告诉她说:房子我替你弄好了。现在陪你去看看。”
一看之下,罗四姐又惊又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断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只怕我同有福气,住这么好的房子。”
七姑奶奶不理她这话,光是问她还有什么不满意之处,马上可以改正;罗四姐倒也老实说了,还应该加上窗帘。“窗帘已经量了尺寸,叫人去做了,明天就可以做好。”七姑奶奶接着又问:“你哪天搬?”
“慢点!”罗四姐拉着她并排坐下,踌躇了一下说道:七姐,说实话,房子我是真欢喜。不过,我怕车量办不到,房子连家具,一起在内,总要四千银子吧?”
“四千不到。我有细帐在那里。”七姑奶奶说:“你现在不必提心买不起。这幢房子现在算是我置的,白借给我住;到你买得起了,我照原价让给你。”
“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吗?”
“你不相信,我自己都不相信呢!”七姑奶奶笑道:“看起来,吴铁口的话要应验了。”
罗四姐记得很清楚,吴铁口断定她要“做小”,如果“偏要做大”就会“嫁一个克一个”。假使不愿“做小”,又不能“做大”,本身就会遭殃,性命不保。 倘或如此,八字中前面那四个字的“财”、“官”、“印”、“食”,自然都谈不到了。所以只有心甘情愿“做小”,才会有福气。这样一想,七姑奶奶话中的意 思,也就很明显了。
话虽如此,罗四姐却不愿表示承认,可也不愿表示否认。这一来,唯一办法便是装作未听清楚而忽略了她的弦外余音,故意言他。
“七姐,搬家是件蛮麻烦的事,恐怕----”
“你用不着顾前想后。这里家具摆设都有了;你那里的木器,能送人的送人,没人可送,叫个收旧货的来,一脚踢。收拾收拾衣服、首饰、动用器具,不过一天的工夫,有啥麻烦?“这那班客户呢?”
“这倒比较麻烦。”七姑奶奶沉吟了一会说:“我劝你也不必再做了----”
“不!”罗四姐抢着说道:“不光是为我自己。人家也是养家活口的一项行当,我不能不管。”
“那也容易,你找个能干的人,做你的替手。说不定,还可以要一笔顶费。七姑奶奶又说:“新旧交替,难免接不上头,老马可以慢慢搬过来。或者老马投了新东家,你就更加省事了。”
听七姑奶奶为她的打算,简捷了当却又相当周到,罗四姐实在无话可说了,“七姐,我真服了你了。”她说:“如今只剩下一件事:挑日子。”
“对。”七姑奶奶说:“到我那里去,一面挑日子;一面再好好商量。”
回到古家,略为歇一歇,七姑奶奶叫人取了皇历来挑日子。很不巧,一连八、九天都不宜迁居,最快也得十天以后。“那时候老太太已经来了。”七姑奶奶 说:“我的想法是:顶好这三、四天以内就搬停当,老太太一来就住新房子,让她老人家心里也高兴;而且也省事得多,四姐,你说呢?”
“话自然不错。不过,日子不好,没有办法。”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有办法。俗语道得好:拣日不如撞日。撞法哪天是那天,你说好不好?”
“怎么撞法?”
“以老太太到上海的那天,就算你撞到的日子。老太太到了,先在我这里歇一歇脚,马上进屋;你也把要紧东西先搬运了来,晚上摆两桌酒,叫一班髦儿戏,热闹热闹,顺便就算替老太太接风,不是一举两得。”
罗四姐觉得这样安排也很好,便即问道:“七姐夫不晓得哪天回来?”
“快了。大概还有四、五天工夫。”
古应春回来了。便得罗四姐深感意外的是:她的母亲没有来,倒是乌先生来了。
那乌先生有五十多岁,身材矮胖,满头白发,长一个酒糟鼻了,形容古怪,但那双眼睛极好,看人时,眼中两道光芒射过来,能把人吸引住,自然而然地觉得此人可亲且可信赖。因此,七姑奶奶一会便对他有好感。
在古应春引见以后,自然有一番客套;七姑奶奶问到罗四姐的母亲何以不来,乌先生乘机道明了来意。“罗四姐的娘因天气太热,又是吃观音素,到上海来作客,种种不方便,所以不来。不过她娘倒有几句要紧话,要我私下跟她说,所以沾古先生的光,携带我到上海来开开眼界。”
“蛮好,蛮好。”七姑奶奶说:“罗四姐,我跟她一见如故,感情象亲姊妹一样;乌先生是她敬重的人,到了这里,一切不必客气。现在,乌先生看,是把罗四姐接了来呢?还是你支看她。”
“她娘还有点吃的、用的东西给罗四姐,还是我去好了。”“那末,我来送你去。”
“不敢当,不敢当,决不敢当。”
“乌先生,你不要客气。为啥要我亲自送你去呢?这有两个缘故。”说到这里,七故奶奶转眼看着丈夫说:“你恐怕还不晓得,罗四姐搬家了。是老宓的房 子,我一手替她料理的。”“好快!”古应春说了这一句,便又对乌先生说:“罗四姐的新居在哪里,我都不知道:那就非内人送你去不可了。”“我送了乌先生 去,顺便约一约罗四姐,今天晚上替乌先生接风,请她作陪。”
听得这么说,乌先生除了一再道谢以外,再无别话,于是舍车会轿,一起到了罗四姐那里。七姑奶奶把人带到,又约好罗四姐晚上陪乌先生来吃饭,随即匆匆忙忙赶回家,因为她急于要听古应春谈此行的经过。
“他是女家的大冰老爷----”
原来胡雪岩一回杭州,略得清闲,便与老母妻子谈罗四姐的事。本来娶小纳妾,胡雪岩原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但罗四姐的情形不同,好些有关系的事,都要预 先谈好,最要紧的,第一是虚名,第二是实权。杭州官宦人家的妾待,初进门称“新姑娘”,一年半载亲党熟悉了,才会称姓,假如姓罗,便叫“罗四姑娘”;三年 五载以后,才换称“姨奶奶”的称呼。至于熬到“姨太太”总要进入中年,儿女成长以后。可是胡雪岩却为罗四姐提出要求,一进门就要称“太太”。“那末,”胡 老太太问道:“你的元配呢?这个也是太太,那个也是太太,到底是叫哪个?”
“一个叫了二太太好了。
胡老太太沉吟了一会道:她怎么说呢?”胡老太太用手遥指,这“她”是指胡太太。
“我还没有跟她谈到这上头。先要娘准了,我再跟她去说。”
胡老太太知道,媳妇贤惠而软弱,即便心里不愿,亦不会贸然反对;但她作为一家之主,却不能不顾家规,所以一时不便轻许,只说:“我要好好儿想一想,总要在台面上说过去才可以。”
“台面上是说得过去的。为啥呢”胡雪岩正好谈“实权”,他说:“目下这种场面,里头不能没有一个人来抓总,媳妇太老实,身子又不好;以至于好 事,还要老太太来操劳,做儿子的心里不安。再说句老实话,外头的情形,老太太并不清楚,有时候想操心,也无从着力。我想来想去,只有把罗四姐讨了来当家, 既然当家,不能没有名分,这是所谓“从权办理”。台面上说得过去的。”
“你要她来当家,这件事,我就更加要好好想一想了。你总晓得,当家人是很难做的。”
“我晓得。罗四姐极能干,这个家一定当得下来。”“不光是能干。”胡老太太说:“俗语说: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做当家人要吃得起哑巴亏。丫头 老妈子、厨子轿班,都会在背后说闲话,她也有没有这份肚量,人家明明当着和尚骂贼秃,她只当没有听见脸上有一点懊恼的神气都没有?”
“这一点----”胡雪岩说:“我当然要跟她说清楚,她一定会答应的。”
胡老太太大摇其头,“说归说,答应归答应,到时候就不同了。”她说:“呢菩萨都有个土性,一个忍不住闹了起来,弄得家宅不和,那时候你懊悔嫌迟了。
这是人的看法不同。胡老太太以前也见过罗四姐,但事隔多年,是何面貌都记不清楚了,当然只就一般常情来推测;胡雪岩心想,这不是一下子可将老母说服的,惟有多谈一谈罗四姐的性情才具,渐渐地让母亲有了信心,自然水到渠成。
就在这时候,古应春陪着洋人到了杭州,谈妥公事,派人陪着洋人去逛六桥三竺,古应春才跟胡雪岩详谈罗四姐所托之事,以及乌先生代笔信中的内容,认为事机已成熟,可以谈嫁娶了。
“我们老太太还有顾虑。”胡雪岩说,“老太太是怕她只能任劳,不能任怨。”
“那末,小爷叔,你看呢?”
“这要先看我们怎样子待人家,”胡雪岩说:“罗四姐不肯拉倒,如果肯了,她总也知道,我不能拿元配休了,讨她做大太太,而只有做小。做小称太太,只让她掌权;她只要这样想一想,就算有闲言闲语难听,一口气咽得下去,自然心平气和了。”
“小爷叔的话很透彻。”古应春自告奋勇,“我来跟老太太说。”
说当然有个说法,根本不提胡雪岩,只谈七姑奶奶跟罗四姐如何投缘,以及罗四姐如何识好歹,因为七姑奶奶待她,所以言听计从,情如同胞姊妹。
胡老太太很尊重患难之交的古应春夫妇,对开姑奶奶更有份特殊的感情与信心,当时便说:“七姐中意的人,一定不会错的。这个媒要请七姐来做,我也要听了七姐的话才算数。”
一桩好事,急转直下,看来成功在望了。但古应春心思细密,行事谨慎,觉得乐观的话以少说为宜。
“老太太也不要太高兴,不家肯不肯,还在未知之数。”
古应春接下来细谈七姑奶奶陪罗四姐去算命,几乎与吴铁口吵架的趣事;当然,他决不会透露,这是他们夫妇事先跟吴铁口说通了的秘密。
胡老太太听得很仔细,而且越听笑意越浓,“原来她有这样一副好八字,看来真是命中注定了。”她接着又说:“这种人的脾气是这样的,要嘛不肯,要肯了,说的话,一定有一句、算一句。”
“小爷叔,”古应春又想到一件事:“不知道婶娘的意思怎么样?”
“她肯的。”胡老太太接口,“我跟她谈过了,她要我作主,现在,七姐夫,这桩事情,我就拜托你了。”
“只要老太太作主,婶娘也不会埋怨,我同阿七当然要尽心尽力把这件事办圆满来。”
于是古应春为胡雪岩策划,男家的媒人是七姑奶奶,女家的媒人不防请乌先生承乏。胡雪岩自然同意,便发了一份请帖,请乌先生吃饭。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