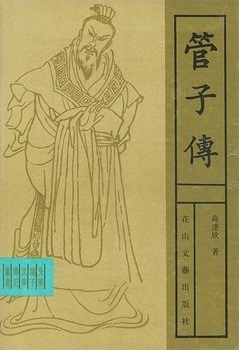酒井左卫门尉忠次没有在冈崎逗留,却直接回滨松去了,这令信康深感不安。“事情比我预想的可能还要糟糕。”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想到已大难临头。纵然 信长一时误解,到底是自己的岳父,滨松那边又有父亲,所以不大可能出事。进行种种交涉之后,自己的清白必会显露,但母亲的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现在看来, 减敬这人确实相当可疑,大贺弥四郎应也与母亲大有牵连。正如野中重政所说,如果母亲写给胜赖的密函真的到了信长手中,无论如何辩解,恐怕都是没用的。对, 必须当面和母亲对质!
这一天,信康在马场待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他在绵绵细雨中去了筑山夫人的住处。
自从出事之后,夫人的侍女好像完全变了样。出来迎接的是一个叫阿早的小姑娘。阿早一见信康,吃了一惊,赶忙把他带到了夫人的房间----是不是少主又要来责骂人了?
“母亲,身体可好?”
夫人大概是刚起床不久,房间里还铺着毛毯,放着梳妆台,以及染发盒。“哦,是三郎啊,真是稀客。快,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夫人边说边整理了一下被褥。
母亲不知何时已经进入了女人的黄昏期,松弛的皮肤令人感到悲凉,人性的真实和固执也毫无遮掩地显露出来。
“母亲。”
“啊啊,我给你倒茶,你每天殚精竭虑那么辛苦。”
“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心事。”
“心事?”夫人很兴奋的样子,侧耳倾听,“是不是你终于领悟到,没有一房小妾看来是不行了,都过了二十了,可传宗接代之人还不见影子…………这样就会愧对先祖,所以…………”
信康转移视线,望着外面的雨幕出神。“母亲,安土的右府大人给咱们出了一道意想不到的难题。”
“什么,你叫他右府大人!三郎,他就算是你的岳父,也不能在你母亲的面前叫他右府大人!信长可是你母亲的仇敌!”
信康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听说信长那里来了命令,要将母亲…………还要我切腹自裁。”
“啊?”夫人似乎没有明白,端起侍女送来的茶水,“你刚才说,信长那里来了命令,要你母亲怎样?”
“要将母亲您…………斩首,让我切腹。”信康又静静地说了一遍,轻轻地把目光从母亲的身上移开。
他们二人说话之时,家康的队伍已经到达本城的前门,信康对此尚一无所知。筑山夫人听了,如遭雷击一般,愣在那里,抬头直直地看着信康。
“信长要将我斩首?”
“还要我切腹。”
“到底是对…………对谁这么说的?”
“父亲。”信康极力想使母亲莫要激动,“具体情况还没有弄清楚,我已经把平岩亲吉派到滨松去了,他现在还没回来。”
“跟你父亲说的?”筑山夫人又嘟囔了一遍,然后大笑起来,“哈哈哈,你滨松的父亲从何时起,已经成了信长的家臣?要杀自己的妻子,还要让儿子切腹,难道信长如此蛮横,你父亲也一声不吭吗?哈哈哈…………”
“母亲。”
“三郎,你父亲不是说过要和信长一战吗?再说,你身边不是还有德姬这个人质吗?”
“母亲!”
“如果连这样的决心都下不了,那还算是什么武将!三郎,你应赶紧准备。”
信康再也无法忍受,使劲地拍打着自己的大腿。“关于此事,孩儿有些事情想问一问母亲。”
“你想痛快淋漓地打一仗吗?”
“那是以后的事。母亲给胜赖发去的内应密函,还有收到的回函,这些母亲都还记得吗?”
“什么?”
“安土那边有母亲的密函的抄本,是从给母亲梳头的那个琴女手里,转交给她妹妹喜奈,再通过一个小侍从送到信长那里去的。盛传这些就是我们母子谋反的证据。所有这些,母亲到底还记不记得?”
筑山夫人脸上顿时失去血色。
“如果真有这么回事,就请母亲痛痛快快地告诉我,然后再作对策。如果是误解,即使别人说什么背叛父亲,做敌人的内应,孩儿也知道绝没有。”
“哈哈哈…………”夫人突然又笑了,“我要是说真有这回事,那你要怎的?”
“那么,母亲…………”
“确实收到过回函,可这些全都是蒙蔽敌人的策略。”
“蒙蔽敌人的策略?”
“弥四郎和减敬是敌人的密探,所以,为了探听虚实,表示我也是和他们一伙的,就故意写信,做给他们看,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信康盯着母亲的脸,身体一阵抽搐。欺骗敌人之类的事,母亲是做不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证据已经被人拿走,可怜的母亲已无药可救了!
这时,带来的下人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禀告少主,滨松的主公已经来到本城,平岩亲吉大人来通报,请少主速去迎接。”
信康一怔,看了母亲一眼,站了起来。筑山夫人被减敬和大贺弥四郎等人利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到底还是大意了…………信康急匆匆地向前门走去,一边走一边后悔不迭,既可怜母亲,又恨自己疏忽。
捕风捉影的谣传也曾多次钻进他的耳朵。可他坚信母亲决不会行谋反之类的不忠之事,一听到这些,一碰到痛处,总觉无关痛痒,甚至反过来安慰自己,结果竟 适得其反。现在,武田胜赖又缓过劲来,一有机会,就来挑战骏河、远江。此时,居然发生密函之类的事情,信康自己还可以想办法应付,可是母亲似已无药可救。
出了筑山御殿,信康在赶往本城的路上遇见了平岩七之助亲吉。亲吉站在那里,浑身湿漉漉的,任凭雨水浇在头发上,洒在肩膀上。不过才几天的工夫,亲吉已经变成一个衰弱的老人,快要辨认不出来了,眼睛里也长出一块大大的黑斑。
“少主…………”亲吉等信康过来之后,用手指了指远方,“少主,请看那边。”亲吉指着树丛那边正门的方向。
信康的心头不禁咯噔一下。家康带来的军队似已把正门团团围住。
“亲吉,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主…………决不要反抗主公。”
“难道父亲真听从了右府大人的命令?”
“是,啊不,主公的心中很是痛苦…………先到大厅里,和主公见见面吧。”
信康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名怒火,父亲难道连血肉相连的亲骨肉都信不过吗?这种不满溢满胸腔,如热汤沸腾。
“少主,请摘下刀。”站在那里的神原小平太立刻上前,卸下信康的佩刀。
“你…………”信康回头看着亲吉。亲吉无可奈何地注视着他,“怎么会这样?难道父亲要剥夺我在此城的兵权?”
“主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好了,前面带路。”
家康坐在大殿上,冷冰冰地看着信康走进来。
“父亲大人,恕孩儿未能远迎…………”信康瞪着父亲跪了下去,一股难以言表的悲凉袭上心头。
满屋鸦雀无声,连声咳嗽都听不到。坐在上座的本多作左卫门像在自言自语地说道:“从今日起,作左受主公之命,负责冈崎城守备。”
作左说完,家康才开口:“从今日起,将信康驱逐出冈崎城,幽禁在大滨。”
一句话像巨石一样砸下来,不带一丝感情。
信康一听,顿时怒目圆睁,抬头瞪着父亲。突然,他放声大笑。受到如此打击,他似乎已无法自控了,笑声中带着哭腔。
“怎么突然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事。侮辱、诋毁父亲大人云云,信康…………哈哈…………想不到父亲居然会听信那样的谣言,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战事,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在大滨钓钓鱼,打打猎吧。父亲行事可真是独特啊。”
“信康,你给我老实点!”家康不忍看着儿子疯狂下去,“亲吉、重政、小平太,早些把信康押到大滨去。信康,休要违背命令,在大滨等候处置。”说完,家康站起身来,准备离去。
“等等!”信康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刚才还在笑的脸庞,现已痛苦得扭曲变形,眉梢和唇边的肌肉一个劲儿抽搐。
“还觉得冤枉?你还想说你无罪?”
“是,我没有罪。”信康向前膝行了两三步,“三郎是父亲的儿子…………”
“住口!”家康红肿的眼睛愤怒地瞪着信康,“你沉迷于亡国的舞蹈,斩杀衣衫破旧的百姓,你都忘记了?”
“这…………这,因为这些人想谋害我…………”
“住口!在打猎回来的途中,无端把僧人拴在马鞍上,活活地把人拖死的,是谁?”
“这…………这我已向您认错了…………”
“拔出雁尾箭,要射向神原小平太的,又是谁?你不会也忘记了?还有,斩杀尾张过来的小侍从…………不只这些,和武田胜赖里应外合,与筑山一起企图讨伐我德川家康…………这个败类!亲吉,把他拉下去!”
“啊,父亲!父亲!这太过分了…………父亲…………”
然而,此时家康已经离去。野中重政和平岩亲吉抓住信康的两只手,泪水涌了出来。满座的人无不垂头丧气,只有本多作左卫门一人凝神沉思,极力地抑制着感情。
突然,冈本平左卫门禁不住号啕大哭。跟家康一起过来的松平家忠也在嘟囔,声音就像从喉咙里挤出来似的。“少夫人也太残忍了。”他似乎认为这场悲剧都是由于德姬向信长告状引起的。
信康的情绪好像也渐渐稳定,他重新坐了起来。“现在不要反抗。到大滨再说…………”
亲吉在信康的耳边嘀咕了几句,信康点了点头,像个听话的婴儿。“那么,出发去大滨吧!”
“好!”
“今天是八月初三…………就不要见夫人和女儿们了,今天不是个好日子。”
冈本平左又号啕大哭。
谁都不忍心看信康一眼。信康就像掉了魂一样,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让大家为我担心了,可是…………不能胡闹,不能再让父亲生气了。”在信康的眼里,家康现在好像只剩下怒气了。他站起来,侧耳倾听屋檐上的雨声,竭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近侍来报信康动身的消息之时,家康仍然端坐,一动不动。
虽然这时雨越来越大,可是,气温却像在不断上升。似乎是台风带来的大雨,风也渐渐地大起来。
家康默然坐在书房里,这里昨天还是信康的书房。家康回忆起自己三十八年的人生,简直就是一个噩梦,惨不忍睹。造成如此惨烈的今日,究竟是何原因?
其原因是和筑山的不和吗?家康虽不愿去想这些,但原因之一,恐是今川义元把脑袋交到了信长的手上。但若信长不讨伐义元,义元也必定讨伐信长…………难道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因,又都有果,因果就这样永远流转不息,不断地进行悲哀的循环吗?
“主公。”本多作左向家康道。他像一具木偶似的,坐在书房的门口。“天要黑了。”
“我知道。作左,孽缘这个东西,你说到底有没有?”
“不仅主公一人有此遭遇。在下也一样,我家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那还是在三方原会战的时候…………此事一直令我念念不忘。不过这次比上次还要险恶。”
“哦。立刻包围筑山的宅院,禁止任何人进入!”
“已经安排好了。”
“哦,德姬的身边也要加强警卫。”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