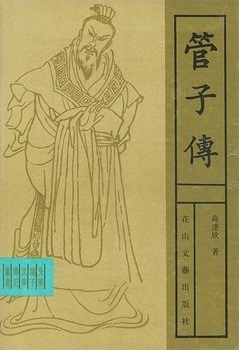明智日向守光秀憎恨信长残暴的性格,把天下卷入了一股可怕的飓风之中。理想常常把现实赶上悲惨的不归路,这次也不例外。
从获知光秀谋叛信长的那一刻起,无论是大名、市民还是农夫,脑中都再次浮现出乱世之景象,并且行动起来。
家康从守口附近的笹塚采取行动时,这一带众人不信赖光秀、觉得光秀还不及信长,抢劫、暴乱者已经蠢蠢欲动了,农夫先把谷物藏匿起来,忙着磨刀霍霍。靠 战乱吃饭的土豪劣绅,还有一些邪恶僧兵,以为机会来了,便大肆造枪造炮,等待买主。从被称作“落入狩”的趁火打劫者到起来自卫的农民军兵,还有那些对领主 不满、揭竿而起的起义之众,或善或恶,都带着各自的想法起事,天下顿时乱成一锅粥。
家康一行从守口取道东北,向北河内郡的津田方向进发时,淀川的边上,早就有大大小小的强盗团伙撤下一张大网,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等待猎物。
“喂,听说有一伙人向北河内那边去了,快追!”
“如果是这条路,目的地一定是木津川的对岸。咱们从前面绕过去,在渡口来一次偷袭最合适不过。”
这样的窃窃私语随处都能听到,所有的官道、渡口、山路,都成了熟悉当地地形的无赖之徒的伏击场所。
家康一行从沿寝屋川的上马伏一带转向北面时,已有三四伙豺狼悄悄地跟踪上了。幸运的是,正要渡过寝屋川之时,强盗发现了比家康他们更好的猎物,于是离去。
“又有一队人在赶路,好像是奔近江去的。”
“那么,我们分成二伙,分别追赶。”
“不,我看另一伙穿着打扮都阔气得多,而且人也多,人夫也多,定是个肥主儿。”
“好,那就跟着这一伙。”
后来一想,那一伙人应该是穴山梅雪一行。大概梅雪估计家康会避开美浓,所以,就另外雇带路人从宇治桥翻越木幡,进入江州,再到美浓,从岩村经甲信回去。
家康一行在茶屋四郎次郎的安排下,与消息灵通的商人混在一起,二人一组,前前后后,遥相呼应。忽见一名报信人神色匆匆地赶了来。“请先暂停一下,前面 有一伙商人正在厮杀。”这名吓得脸色苍白的报信者赶来时,已经接近黎明,他们刚刚出了北河内山,正排成一队走在甘南备山险峻的山路上。
“旅人遭到贼人偷袭?”最前面的神原小平太闻听,不禁咂舌,“这条山谷可不能停留。如果在这样的地方遭袭,则进退两难。再去打探一下,看看有多少人。这些蟊贼,就是抢人,也得找个放得开手脚的地方啊。”
此地确实凶险。右边是高峻的悬崖,左边是浓密的竹林。半夜里,阴沉沉、黑黢黢的天空中下起了细雨。
“照你的说法,天这么黑,就是靠近了敌人,也分不清敌我。不一会儿天就要亮了,在此之前…………”
“万一遇到什么不测,你们又不清楚地形,停在这里,一旦遭袭…………”
还没等小平太说完,家康已经开口了:“不要说了,小平太。我们的战争已经成了和光秀的战争。一旦轻举妄动,容易被敌人发现,先歇息一下。”此时能骑的马一匹也没有了,只有两匹驮着行李的马累得奄奄一息。就连家康都默默地步行着,已经难以辨认。
队伍停了下来。加上茶屋四郎次郎雇佣的人夫,还有商人,一共五十多人,从堺港带来的饭团已经吃完,饥饿折磨着每个人的肚子。天亮之后,一定会有不少人磨破草鞋,只剩一双光脚板了。
“松丸在吗?于龟、小源太,你们没有累趴下吧?”停下来之后,家康随便摸了个地方坐下,问起侍卫的情形来。
“在。松丸就在主公身后。”鸟居的儿子回答道。
“于龟也在。”
“小源太也在。”虽然每个人都毫不示弱地回答,却可以明显听出饥饿和疲劳之感。
“我家康记忆中最艰难的时候,是在三方原会战之时。那时真是饥寒交迫,武田的人马强悍无比,死了一个又站出来一个,刚报出名字来,立刻就将其斩杀。可 是,我一点儿也不妥协,挥动长枪,左挑右刺,从早上一直战到深夜。和那时迷迷糊糊地赶回城里相比,这点儿困难算得了什么。”黑暗中,不知谁扑哧一声笑了。
“谁在笑?”
“大久保忠邻。”
“我在给侍卫们讲故事,有什么好笑的!”
“哈哈…………听父亲说,那时,主公在马上大便了。”
“混账,那不是大便,是酱汤。哈哈…………如果一个人奋斗到连屎尿都忘记的程度,那他定是个了不起之人。”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莫要笑,莫要笑。说不定这次的困难比上次还大呢。但是,困难再大,我们也决不屈服。”
这时,从路的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吵嚷声。对方一定不知这里有人在歇息,是撞上了。
“哎呀,人数不少,不要掉以轻心。”
“点上火把,快。”
这伙人分明是刚刚于前面偷袭的暴徒。当看见对方燃起的明亮火把时,这边的人早已把手按在刀柄上。“主公,主公,快到后面去。受伤可不得了。”
周围一阵骚动,负责断后的渡边半藏发疯似的从狭窄的路跑来。“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何要和我们作对?若不退后,格杀勿论!”
“等一下,半藏。”家康叫住了他,“对付这些人,茶屋最拿手了。茶屋,你去交涉一下。”
此时长谷川秀一早已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和暴徒交涉。
“喂喂,我们是前面甲贺郡的领主多罗尾四郎右卫门光俊的手下,你们半路杀出,把我们苦苦追到这里来的猎物给劫走了,你们说怎么办?”
“半路杀出?你们是强词夺理。我们一直从河内追踪而来。若是你们被别人抢走了猎物心有不甘,为何不到前面去打埋伏?”
“说的也是…………”秀一先避了避对方的锋芒,“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仔细一想,却不合情理。”
“哪里不合情理?”
“如果说烧杀抢掠是武士的本性,我们在这里等你们抢完,再抢劫你们,也没什么不合适吧?”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弟兄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伤才弄来的东西,怎会轻易让给你们?”
“你这么一说,事情就不好办了。这里已是我多罗尾城的地盘了。虽说如此,把你们拼尽老命才得来的东西都搜出来,也未免太过无情。这样,黄金、衣服、货 物、马匹之类全给你们了,把刀留下,换条道回去。我们就当没看见你们,否则,闻风而来、不讲情面的多罗尾的弟兄可决不会饶过你们。”
“只把刀交出来就行,是吗?等一下,让我们商量商量。”
人与人的关系有时不能以常理来衡量,而会受到某种气氛的支配。对方若知道自己是旅人,一定会露出利牙,豁出命来袭击。可是,当成为有了共同目的的同伙后,就会生出一种奇妙的义气,气氛为之一变。
“好吧,那就把刀交给我们,换条道去。可是,刀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只交出四五把就行了。”
首领模样的两三个人碰一下头,不久,就把抢来的刀扔在湿漉漉的山路上,退回去了。
家康心悦诚服地听着秀一的交涉,等他们离去后,捧腹大笑。“哈哈…………策略这东西可真是管用,没有向他们讲道理,却成了他们的同伙…………啊呀,真是兵法的 极致啊。”说着,家康看了一眼长谷州苦笑着捡回来的刀,急令:“万千代,拿火来。”只见其中一把刀的刀柄上刻着武田家菱形的金纹。莫非是穴山梅雪的东西?
侍卫领井伊万千代直政从火堆里拿来一根燃烧着的木头照着,家康突然低低地呻吟了一声。没错,正是穴山梅雪的刀!
“万千代,再把火把拿近点。”家康一下子拔出刀来,在炭火的映照下,在这把相州刀的刀身上,散落着点点梅花一样的血迹。相互厮杀,刀被夺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甲斐源氏灭亡之时,唯一生存下来的幸运之人就是穴山人道梅雪。没想到,他竟然也跟随胜赖去了,被土匪们杀死在了荒郊野岭。
“火把灭掉。”家康把刀还回刀鞘,嘴里念叨着梅雪的名字。人的命运真是变幻莫测。讨伐武田胜赖、看着武田氏破灭也会心痛的信长去了,武田氏唯一幸存的穴山梅雪也去了。下次丢掉性命的人,将是谁,是光秀还是自己?
天终于变白了。右面阴暗的悬崖上传来了小鸟的啁啾。
“好吧,就把这把武刀当成是穴山梅雪人道的遗骸来纪念吧。万千代,你拿着。”家康把刀交给井伊直政,“走,看不见的千辛万苦还在前边等着呢。”
一行人再次向东急行。
四周渐渐地明亮,天空的云层染上了淡淡的颜色。小雨终于停了,视野变得宽阔。大家的草鞋几乎都只剩下鞋绳了。他们已经越过了山城和河内。
“往前走我们就要到达天王,过多多罗、草内后,木津川就在对面了。渡过木津川,希望京城的吴服师龟屋荣任在那边活动,给我们弄点吃的。”茶屋四郎次郎不时走到家康身边来,和他说话。
每一次,家康都笑着点点头。“关于吃的话,我看你就别说了吧,我都听得肚子咕咕直叫了。”
前几天大家都吃腻了美食,因此每个人的精神都比平时在战场上萎靡得多。再走不到半个时辰,就看见了木津川。天已大亮,云缝里漏下缕缕灿烂的阳光。
这时,一股更强烈的睡意袭来。但是,除了两三个年轻的侍卫之外,其余人全都有千锤百炼过的钢筋铁骨。
“喂,这里有打斗的痕迹,草都被踩烂了。”
大家来到木津川前,先喝饱了水,然后草草洗了把脸。在茶屋和长谷川秀一的精心安排下,大家平安地渡过了木津川。
从乡口来到田原,在这一带找点吃食…………正这样想,对面有一片数不清的旌旗正向这边杀过来,是起义的农民军。
一进入田原,茶屋四郎次郎就从队伍中消失了,大概是去和先行一步的吴服师龟屋荣任联络,给家康找个歇息的场所和弄吃食去了。
“再坚持一下,进了田原就好了。一定要挺住。”
“说什么啊,不是才两天吗?我听说,一个人如果扎起裤腰带,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能战斗。”
虽然好多人在私下里唧唧喳喳,但明显可以看出,大家的脸都瘦削了不少。神原小平太迷迷糊糊地走在家康的后面,有时猛然一怔,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光天化日 下做着白日梦。默默地走在他前面的家康,看去仿佛是抹着盐粉的香喷喷的牡丹饼,他一把抓过来撕碎了,塞迸嘴里,可是,怎么也填不饱肚子。我怎么这么能 吃…………
神原小平太正在边走边做白日梦,茶屋四郎次郎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脸色大变。“大事不好,大人。”
小平太一下子睁开眼睛。
“从濑田、稻津那边杀过来一队起义军,在田原烧杀抢劫之后,正向咱们这边退过来。”
人们顿时大惊失色,赶忙停下脚步。家康那硕大的脑袋上,汗珠晶莹剔透。
“如果不赶紧掉头,就会和他们撞到一起。看,旌旗招展…………”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全都静了下来。号角低沉的声音,从山那边压了过来,震撼着每一个人。
“如果是起义军…………使些黄金的话…………”家康说道。
“这很难奏效。”茶屋使劲地摇着急得发红的脸,“都是些发了疯的家伙,连里衣都不会给你留下。这些人和劫匪们不同,不好对付。”
小平太舔着已经干裂的嘴唇,等待家康的指示。如果改道,在这样的山中,不是原路返回,就是进入两边无路可走的山谷潜伏起来。而且,如同茶屋所言,起义 者和盗贼完全不一样。盗贼有盗贼的现实利益,而起义的暴民却不知进退。盗贼已经职业化,时时能感受到自身的危险;起义者则是爆发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恨和愤 怒,为不断膨胀的对暴力的渴望所支配,所以,他们全然不会冷静地算计。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