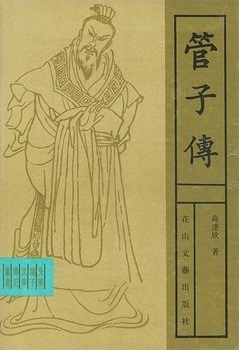丰臣秀吉自未想到利休会有这般准备,这是何等巧妙的反击!连三成、玄以都在侧耳倾听。秀吉发现其人不可轻视,遂道:“利休,你何时放弃了茶道,而成占卜师了?是用秀长之死来嘲笑我的悲哀吗?”
利休立即答道:“大人误会了,正因为别人不知,利休必须对大人说。可大人竟认在下为占卜之流。在下这是根据五行严格推算而出。大人若不信,就大错了。人的生辰八字决定其盛衰,人无论多幸运,十二年间,定有两年不顺。此人生黑夜就叫空亡。此时若轻举妄动,定招致破灭。因此须备加小心。从前太公望就是知道这个道理,才默默垂钓三年,等候即将来临的光明。信长公正好与此相反,于越前的金崎城惨败后,接下来有十年隆运。而当他前往本能寺时,忘了那是空亡之年再临。利休后悔当时为何未请信长公多注意些。因此,这次一定要提醒大人。此后的两年,便是您的空亡之期,请大人千万小心。”
秀吉听了,恨得牙痒痒----对我太阳之子胡言人生之夜将临,这是何等恶毒的胁迫!还举出太公望、信长、胜家的例子,甚至还提到秀长之死…………不能再退让了。对方既然气势汹汹,自己也要全力应对,否则颜面何在?
“哈哈,利休,我知。”秀吉假作让步,“你好像以为我不知空亡?我明白,而且非常清楚。即使不知空亡,我也有休养生息的常识,不必特意拿五行来说事。”
“这么说,大人明白了?”
“当然,我就是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此后的两年,我想过自在日子,享受风花雪月,多多思量人生真意。利休,我选阿吟为伴如何?阿吟何时来?如今春光正好,我们可在花前月下共享人生乐趣。怎样,利休?”
秀吉重新提到阿吟,微微笑了。他认为如此一来,利休应也会退一步。
可是利休半步也没退,也微微笑了。秀吉的攻击,他早有预料,低叹道:“大人,您又想说阿吟的事?”
“对,我想问令爱的事,才特意叫你来的。”
“我就是不希望大人提此事,才故意说到空亡。阿吟果然如我担心的那样,斥责了我一顿。”
“令爱斥责你?”
“是。她斥责我说,过去蒙大人恩典,才获得天下第一茶道师之名,如今却忘恩负又,胡说八道。”
“哦?”
“的确如此。把小女送到大人身边,会使她误解大人对茶道的诚心是假的,亦会使人误解我图谋出人头地,有损茶道。阿吟乃松永弹正之女,由我抚养长大,却会因此事成为不知感恩图报之人。况且这还有负北政所夫人的恩典,也会扰乱淀夫人和少公子的心。这样进退两难,动辄得咎,实乃大空亡。”
白刃相击,火花散落后,二人换了架势。秀吉眼里灼灼燃烧的火焰突然消失了,道:“听你这么一说,我不能轻易要阿吟啊!”
“大人能领会,不胜感激。”
“那么,我必须放弃令爱?”
“希望如此。”
“原来,这件事会玷污茶道。茶道对你我,甚而对天下,都是大事啊!”秀吉压下怒气,突然道,“利休!若你玷污了神圣的茶道,我不会原谅你!”
“是,在下知道彻底领悟此道,便是回报大人厚恩的唯一道路,在下必铭记于心。”
“闭嘴!你可知有人利用长次郎和濑户的茶碗牟取暴利,玷污茶道吗?”
利休微微一笑,这一次他没有掩饰鄙薄之色。他已料到秀吉会这样说,但装作毫不知情:“大人是说有人把长次郎丢弃的茶碗和濑户的废物,高价卖出?这可不行,那人究竟是谁?”
利休一反问,秀吉顿时忍无可忍:“就是利休你这个浑蛋!”
“大人?”
“就是你!”
“大人!长次郎虽被当今天子褒为天下第一,他们的茶具,也并不完全是最上品,濑户的陶工也如此。因此,不好的茶具统统打碎埋了。确是我告诉他们要如此做。那我又怎会把那些废物拿去卖人呢?是谁从我利休手中买到那样的废品,请不必顾虑,告诉在下。若有人假冒我,利休定将他拿到大人面前。”
秀吉吃惊地住了口,但他马上又圆场道:“我也相信你不是存心叛离、贪图钱财之人。长次郎和濑户所做名器,会胜过来自大明国和朝鲜的?”
“是,不能说最佳,但只要活用陶土的特性,稍加用心,便会做出毫不逊色于海外之物的名器。这些都是拜大人慷慨所赐,因此,他们会全力以赴。”利休说到这里,终于笑了,“而且,其价钱一定超过大明国和朝鲜的名器,不能太廉。要让买方确信其物,然后堂而皇之卖出高价。若非如此,世间那些盲目之人,只会认定便宜的东西便不好,这样就与大人的本意相违背,因此一定要注意陶器的品质。可是,竟有人不顾这些,把废弃之物掘出来,高价卖出,更假借利休之名,实令在下忍无可忍!”
秀吉压住怒气----这是我的疏忽,利休定是有备而来,须改变战法才是。他便突然笑着压低声音:“所以你把好东西高价卖出。好吧。可是…………利休啊!”
秀吉不记得自己曾输给任何人。他总是刚柔相济,左右逢源,自信能任意操纵天下人事。可他这一回却被利休难住了。若只是被利休攻击,尚可一笑置之,使对方感到莫测高深,也是胜利。可是今日的利休,却始终不动声色,不惊不乍。利休恐是暗喑自诩,能将我丰臣秀吉玩弄于股掌之上?若真如此,实不可容忍----秀吉终于变成了狮子,不过他仍装成柔顺的羊,道:“利休啊,你大概也察觉了吧,出事了。”
“出事?”
“嗯,所以我想问问你,搞个清楚。”
“在下惶恐得很。”
“不不,你甚有见识,不愧是利休居士,可是,这不过是你我的看法,世人不见得会认同。”
“不无可能。”
“为慎重起见,我想亲口问你:你可知大德寺金毛阁山门上安置有你的木像?”
利休心中一紧:终于来了!他怀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情道:“在下已知。”
“那谁安置的?”
“古溪和尚被流放至九州时,在下曾请求大人赦免他。”
“对,有这事。”
“那时古溪和尚和春屋、玉甫等长老,认为在下积了阴德,就刻了在下的木像。”
“此事,长老们先征得你的同意了?”
“这…………提过。”
“你可有明确拒绝?”
利休不敢再说下去。他已看穿秀吉的心思,若出言不慎,便会把大德寺的长老们也牵连进来。
“是拒绝还是答应?”
“这…………在下认为没有大碍,便答应了。”
“那么,是你答应让他们建的了?”秀吉的声音逐渐肃冷得令人惊心,“治部和官内法印也听到了吧?大德寺的长老们为感谢利休而刻了木像,并把它装饰于山门楼上,此事得到了居士的允许…………明白了!”秀吉说着,又转向利休:“此事在公卿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利休默默看着秀吉,若秀吉说他不逊或者傲慢,则可全力反驳,可秀吉并未提到这些。寺院的木雕不过是些装饰,因此,可随意雕刻花鸟虫鱼于其上,给利休弄个木像装饰在那里,有何不妥?若引起谣言,只要马上把它取下来即可。可是,秀吉却似蓄意已久。
“众人说,你想让敕使自你穿鞋的木像下经过。”
“这…………”
“哼!我完全明白你的心思,可是世人并不把这当成你的罪过,而是当成我的过错,说关白太宠利休了,竟允他行此无礼之事,以后大慨会让你像清盛人道和北条氏那样忤逆犯上。这些说法,我岂能置之不理?你说呢,宫内法印?”
“是!”前田玄以回答。
“利休你可懂?好,我有命令,你们仔细听着!”
“是!”石田三成回答。
“利休!”秀吉一改声气,挺起胸膛,“在大德寺山门楼上,放着一个无职无分、着雪鞋、拄拐杖的木像,这便是大不敬,因此,我要没收先前给你的茶室,令你明日离开京城,到堺港去待命。”
利休笑了。
“三成!你马上去金毛阁拆下木像,拖到聚乐第大门前,处以钉刑。”
“遵命!”
“官内法印!你去大德寺,严命与此事有关的长老们闭门思过,等我命令。我会将此事禀报天子。否则,丰臣秀吉的勤皇生涯会留下大污点。”
利休默默凝视着秀吉。正如先前所料,二人的互相憎恶终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此短兵相接之时,连三成和前田玄以也都面面相觑,没有插嘴的余地。
“明白吗,利休?”秀吉严厉地盯着他,“你马上去堺港,闭门思过。”
“遵命!”利休沉着地施了一礼,“请大人见谅。”言罢起身离去,自然而傲岸,一副行云流水之态。
“大人!”等利休离开,玄以先道,“居士没有辩解,也没有道歉,就此离开了…………”
“哈哈,别担心!”秀吉脸色苍白,“如果他老老实实闭门思过,我自会饶他一命。”
“可是,在下觉得他无一丝悔意。”
“哈哈。和我争的结局如何,他不会不明。你们就遵我的命令,把木像处以钉刑!”
“可是,”三成道,“偏袒居士的大名也很多,万一出乱子…………”
“好生处理即可,不用担心。”秀吉低声道,“你们以为我真恼了?”
“大人是说…………”
“不!丰臣秀吉不会真正生利休的气,只是挫挫那厮的傲气罢了。我要假装恼火,等他害怕得要切腹了,再饶他一命再好不过。”
“哦…………”
“怎可杀他?这有损我对茶道的挚爱。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
三成似乎松了一口气。他虽然想让利休失势,却并不想眼见其被处以更严重的惩罚。如果一怒之下生起杀戮,受到伤害的还是秀吉。“听大人这么说,在下就安心了。那么,我速把木像处以钉刑。”
“哈哈。木像如果受了钉刑,恐怕京城的人也会大吃一惊,大德寺的长老会更吃惊,堺港的商人们也不敢再说三道四。此为一举多得啊!”秀吉说完,扶着屁股,起身如厕去了。
利休表情阴郁地回到葭屋町,把道安、少庵、阿吟三人叫到房里,道:“先叫人整理好大厅。”
随后,利休马上动手煮茶,给他们三人一人一碗,自己也喝了一碗。直到喝完了茶,也无人开口说一句话。儿女们了解利休,知道轻易开口会乱他心神。
“有人来了。阿吟,你去问问是谁命令他们来的,客气些。”
利休一说,三人才发觉宅子被人马团团围住。阿吟点头出去了。不久,她回来对利休复命道:“是上杉景胜大人手下的千坂兵部。”
“哦,有多少人?”
“约七八百人。”
利休听了,微微一笑,低声道:“我赢了!”
“赢了?”
“我赢了关白,好,去厅里!”
“父亲约了客人吗?”少庵害怕地问。
“少庵,莫要惊慌。”
“啊?”
“哈哈,马上就会明白了。上使会立刻到达,正式宣布放逐之令。”
“那么,父亲是在等那上使了?”
“对!茶人就是茶人。我们去等上使,他一到,你们就去玄关迎接。”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