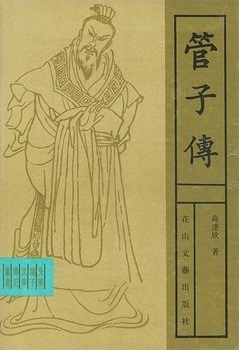阿幸的确被吓坏了,身上一滴汗也无,口干舌燥,她想起了关原合战前攻打伏见城那日的情形。
那日,阿幸去伏见城里一酒家访友。关西大军所到之处,包围的不只是城池。那酒家里不时有散兵游勇进进出出,调戏女人,喝酒撒疯。目力所及,下至十二三岁的女仆,上至六十多岁的嬷嬷,都遭了侮辱。阿幸和酒家女小萩一起藏身于酒窖一角。
把二人藏在那里的,乃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佣,后来她说出去看看风声,便一去不返。阿幸和小萩不安起来,小萩便也偷偷溜出去察看情况,没想到竟成永诀。终于,不知哪里起了火,浓烟从阿幸藏身的酒窖入口钻了进来。阿幸憋住气,拼命逃离了那里…………
直到如今,在疲劳时,阿幸还会梦到那时的场景。
阿幸所经历的“战事”,不是弓矢纷飞、剑拔弩张,而是满地翻滚的大圆桶中,堆弃无数女人尸首,惨状惊人。那些兵士喝足了酒,侮辱够了女人,还不满足。在肆意妄行一番之后,监军大概怕上头责骂,干脆大开杀戒,一把火将为害处烧了个精光。
阿幸逃跑时发现了小萩的尸体。小萩和在她之前跑出去的女佣依偎着倒在血泊中,下身插着一支长枪。阿幸大声尖叫着先前喝过的甜酒全吐了出来。她穿过重重烟雾,拼命奔跑。自那以后,一提到“打仗”,阿幸脑中便是那一日小萩的惨状。
“表兄,莫再说了…………”阿幸剧烈地颤抖着,“阿幸全明白。请明白告诉我,该怎么做。只要能够阻止战事,阿幸什么都愿意做!”
“呵,全明白了啊。”阿幸剧烈的反应,让光悦吃了一惊,“记住,若伊达和大久保谈到战事,要详细地告诉我。”
阿幸毫不犹豫地点头:“表兄,阿幸立刻就去寻大人。其实,阿幸也想知大人现在正干些什么。”
光悦未问阿幸从佐渡出发后,走哪条路来的京城,也未问她打算如何联络长安,他甚是放心,相信她自己能处理好一切,只把所忧之事反复叮嘱。
一旦关乎日莲宗和天下,光悦就忧心如焚。若非如此,他便不是本阿弥光悦了。光悦志存高远。为一事倾尽全力的人诚是伟杰,而一个男子,不管他是为了野心、技艺,还是兵法,那种竭尽全力、专心一致、心无旁骛之态,都让阿幸深深倾倒。阿幸嘴上虽轻描淡写,心中却称扬不已。她深深感叹,若光悦并非姐夫,她必会以身相许。除了光悦,她最喜欢的人便是大久保长安。长安与她不仅有男女之情,亦把她曾脱缰的心绪拉回尘世。然而,现在她喜欢的一个男子,让她去监视她喜欢的另一个男子,这是何等新鲜有趣的事啊!
阿幸从光悦宅中出来,朝一街之隔的娘家走去。她父母开着一家店铺。
“啊,阿幸啊,家里人都回来了,正等着你呢。”嫂子看到阿幸,嚷嚷道。嫂子乃是光悦的亲妹妹,两家其实便是一家。
“哦,多谢。”阿幸脑子里一片空白。随后要突然出现在大久保长安面前,吓唬他,然后照光悦教的探探他,阿幸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想着想着,她已穿过长长的走廊,到了内院。
“臼井?”
“是。臼井三郎兵卫在此恭候夫人。”臼井三郎兵卫乃是京城人,负责管埋长安的年赋,也是护送阿幸从大久保长安辖地来到大坂的人之一。
“怎的了,大人又换住处了?”
“是。大人在大和的公事已毕,现住在堺港奉行成濑正成大人别苑。”
“堺港?乳守宫附近的妓女早把他围住了吧?还有何人知我来了京城?”阿幸不忘身为侧室的体面,比面对光悦时显得威风了许多。
“这…………难得大人有兴致,夫人还是莫要放在心上…………”
“呵呵,这样啊。那好,不过今晚就要出发了,也不知船备好了没有。”
“今晚?”
臼井三郎兵卫吃了一惊,“但是,大人今晚已安排好了住处…………”
“呵呵呵,”阿幸像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大笑起来,“难道大人喜欢上了什么人?”
“夫人…………”
“到底怎回事?没有船?”
“船倒是有。但在下就这样把夫人带到堺港,大人万一怪罪下来…………”
“怕什么?”
“其他从能登跟来的人,对此也甚是担心。”
“呵呵。这个我心里有数。我在佐渡时,倒是想准备船来着。”
“呃…………”
“不过来不及了。不是有很多运送矿工的米船从能登开到佐渡吗?我就坐那种船去找大人。我想他会夸我,而不会责备。我想好了,不管大人是惊喜还是生气,都由我担着便是。”
“那…………能行吗?”
“哼,你以为我是因嫉妒才跑去责他?怎么说,我亦是在京城长大的女人啊。好了,立刻备船。”
臼井三郎兵卫凝视着阿幸,会心一笑,“遵命。”
“唉,为何我非得做出让你们为难之事呢?”
“在下立刻去办。”三郎兵卫以前曾和大久保长安一起演过手猿乐,年逾不惑,人情世故颇为练达。他恭敬地退下,走进暮色中泥泞的街道。
阿幸拍拍手召侍女,“阿杉!阿藏!”
此时,她嫂子慌慌张张跑了进来,“你不在的时候,姑娘们都出去买扇子了。”
“两个人都…………好吧?那她们就待在这儿吧,嫂子,我马上要去堺港走一趟。”阿幸乃是那种按捺不住之人。
大久保长安夹在一堆从乳守宫周围召来的妓女中间,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
位于宿屋町临海一面的堺港奉行的别苑,和旁边的旭莲社一祥,都用来招待高贵的客人。照例,奉行只负责警备,客人在内尽可自由自在。召妓召艺,洽谈生意,悉随尊便。长安充分利用了这种自在,每次从京城或大坂到奈良的属地时,定会来这里歇息歇息,放松筋骨。此处除了拥有四通八达的河道,海上交通亦甚是便利,无论去石见还是相模,都颇为方便,甚至还能及时掌握长崎的流行风尚。
“来来,今晚大家都得喝个痛快,玩个痛快!明日我就不在堺港了。”长安靠在一位叫千岁的妓女膝头,有些昏昏欲睡。
昨日长安刚到时,成濑正成过来聊了两句,之后就再未露面。在座的有堺港奉行的同心、长安的一个幕僚和从石见带来的半兵卫几人,还有演奏大鼓、小鼓、月琴和笛子的男艺人,外加十几个妓女。
“再热闹些!怎生和深更半夜一样安静?来来,喝,喝!”
此时入夜未久。从窗户看出去,暮色中若隐若现的渔火、泊船上的灯光,以及戎岛灯塔的光芒,随着海上夜色的加重,灯火愈发明亮起来。
女侍进来,不停地和正在同妓女喝酒的同心咬耳朵。同心点头不已,东倒西歪走到长安面前,半说笑道:“在下有事要和总代官大人说。”
“总代官大人?哈哈!今晚就叫我老爷吧,老爷我被石见和佐渡的金银之气弄得虚弱了许多啊。哈哈,要是不常把身上的铜臭洗一洗啊,气都喘不上来了!”
“是,老爷。”
“何事?”
“来了一位明石扫部大人先前的家臣,带着长崎奉行长谷川左兵卫藤广大人的书函。该怎生处理?”
“长崎奉行介绍?”
“正是。”
“既然得太郎冠者长崎奉行的照顾,恐与大御所爱妾阿奈津夫人之兄关系匪浅。”长安离开千岁的膝头,站起身来,完全如个狂言师,手舞足蹈,狂态毕露。
长安本就贪玩。加之最近的金银开采量远远超出预期,他的收入便也翻了几番竟常常大言不惭在妓女们面前说笑道:“方今天下最富有之人啊,除了将军大人和大坂城主,便是我!”他从白天喝到现在,马上就要醉倒,可一听说有客人来访,竟立刻兴奋起来。
“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可慢待,你且把这话给我好生传下去!”
“明白。”
看着同心摇摇晃晃走了出去,长安豪迈地大笑起来,“哈哈!一下子就清醒了!既然来人和大御所爱妾有些干系,就当再叫几个女人!咚一呛----次郎冠者听啊----令----”
“在!大人!”长安的幕僚哼着狂言唱腔走上前来。
“有劳你,去乳守官附近,找一个漂亮些的女人来!”
“明白!”幕僚恭恭敬敬施了一礼,正了正身姿,衣襟扫过榻榻米,退了出去。
“哈哈!愈发有趣了。千岁!”
“嗳,大人?”
“我的记性一直甚好,可现在竟突然把这客人的名字给忘了。客人叫什么来着?”
“呵呵!大人还没问过客人的名字呢。”
“怪不得我想不起来!你们说,不问怎能知道别人的名字呢?”
此时,隔扇被推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道:“是啊,我可想不起那个名字。”
长安愣了一下,看着来人,然而烛光摇曳,他的醉眼已看不清女人的长相。“嗬,还挺水灵的。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子阿幸。”
“阿幸?好似在哪儿听过啊。”长安嘟哝着,“不对啊,客人当是个男子,要不也不会特意差人去寻漂亮女子,是吧,千岁?”
“是,老爷。”
“客人确是说从长崎来的?”
“从长崎…………倒未说清楚。”
“到底是从何处来的?”
“这…………怕是从天上来的吧。”
“天上?那可不行!天上的客人有时会送来红头发、蓝眼睛的女人,那可怎生使得!”长安似想起了伊达政宗身边的碧眼侍妾,突然缩了缩脑袋,一副颇为害怕的样子。
这时,同心领着客人走了进来,“客人来了。”
同心禀报的时候,长安清醒了些。他有几分想起了伊达政宗和索德罗,人立时变得谨慎起来,严肃地上下打量了一番来客。只这一瞥,他又变回了那个吃过很多苦头才走到今日的大久保长安。
“听说乃是长谷川大人介绍你来的?”
“是,此处有一封书函。”来人年方二十五六,容貌俊美,谈吐文雅,像个生意人。
“你原来真是明石扫部手下?”
“这…………是。但小人职责实际与军务无涉,小人如今专门负责从堺港到长崎的船务。”
“哈哈!这么说来,你和我一样,太平时还有些用处,打起仗来就一无是处了。”
“呃…………是,是有那样的说法。”
长安从同心手中接过书函,边看边问:“你信洋教?”他似漫不经心,实则在认真观察对方的反应。
对方似是吃了一惊,道:“大人知道?”
“哪能不知!每次看到胸前挂着十字架的人,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这么说,总代官大人您也信奉…………”
“不,那倒不是。总的说来,洋教徒对自己很是严谨。”
“惭愧。小人名桑田与平,信函上也写着。”
“是写着。不过只有名字,未说何事。喝酒之前,先说说此行的目的吧。”
“多谢大人。”桑田身子有些僵硬,施了一礼道,“乃是关于生丝的生意…………小人想获生丝进口之权。”
“哦?那可找错人了。我只管金矿。”
“在下对此甚为清楚。”
“那还来找我谈生丝?”
“小人看出,获生丝进口之权的人,都非洋教徒。”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