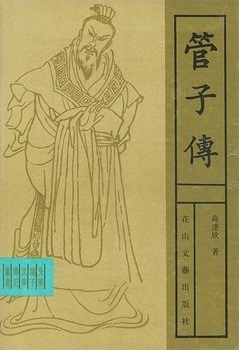波伏瓦:在昨天的谈话中,你谈到一件事,但没有充分展开,这就是你总是希望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萨特:是的。对许多人说来,社会主义体现了一种巨大的自由;首先是一种经济的自由,然后是一种文化上的自由,一种日常体验到的行动的自由,一种有大量选择权的自由。他们希望自己是自由的,不由社会决定,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形成他们自己。只是,例如马克思主义者显示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包含这种思想。马克思有这种思想,他展望共产主义遥远时代时,设想社会将由自由人组成。他设想的自由确切他说来不是我设想的自由,但这两者彼此是相似的,而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自由再没有任何地位了。对他们说来,要紧的事是他们将要建立的那种社会;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像许多机器那样被安放于其内。这种社会主义不承认某些价值,比如说正义,这是在一个人给予的和得到的东西间的一种平等。但一个自由人能超出社会主义存在的思想----我说超出我不是指在一个后来的时期,而是指每时每刻都超越社会主义的统治----是一种苏联人决不会具有的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如果它还可以称为一种仕会主义的话----并不表现为允许个体在他选择的方式中发展。这就是我在给那个我们1940年、1941年形成的思想贫乏的小团体起“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名称时我想说的东西。虽然这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是很难认清的,但它是那种结合的力量,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关系,代表了我的政治倾向。它是我的政治倾向,我从没有改变过它。甚至现在,我在同加维和维克多的谈话中努力维护的,还是社会主义和自由。
波伏瓦:对,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还是回到昨天谈的问题上,希望把社会主义和自由连结在一起,使你摇摆在***、组成***民主联盟、孤独、同***恢复关系等等之间。我们不必逐一回顾直到1962年你的全部政治生活的历史,因为我写过它,部分地是在你的口述下,在《境况的力量》中,但我希望知道你是怎样看待你走过的道路的,我们就说到阿尔及利亚战争为止。
萨特:嗯,我认为我是沿着自己的路线前进,道路是崎岖的,困难重重,我常常发现自己是少数派,常常是孤独的,但这确实是我永远希望的东西----社会主义和自由。长时间来我相信自由,我已经在《存在与虚无》中写了它。我觉得自己是自由地生活,从童年直到现在,虽然我也追随过大流。但我自由地生活过,我现在仍然有同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仍是结合在一起。
波伏瓦:你总是梦想着这两者的一致;但你从没有找到它。你有时有一种找到它的错觉吧?比如说,在古巴?
萨特:在古巴,是的。那儿有多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当时,我在那儿时,卡斯特罗没有真正的文化原则。他不想强加一种确定的文化。后来他变了。
波伏瓦:那是在1960年,不久他夺取了政权。
萨特:那时他甚至不希望被说成是社会主义。他请我在法国写关于他的文章时不要提及社会主义。
波伏瓦:事实上这是一种可以说是卡斯特罗主义的东西。
萨特:说真的,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我记得我总在问他们,“如果你们面临恐怖统治,你们怎么办?”
波伏瓦:后来他们确有一种恐怖统治。
萨特:他们已经有它将要来临的暗示。他们弄不清他们该做什么,他们没有回答我,没有说不会有一种恐怖统治。
波伏瓦:回到我的问题上来,你还记得你感受过和想过的东西吗?你走过的这段路程现在对你有什么影响?你认为自己犯了很多错误吗?你认为自己做了一些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吗?你是不是总是行动得很好?总之,你怎样看待这一切?
萨特:毫无疑问我犯有许多错误。但不是原则上的错误----而是方法上的错误,在表达某个确定事实时看法上的错误,但总的说来我同自己的过去是一致的----总的说来是一致的。我认为这必定会使我达到我已达到的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带着一种宽慰的眼光回顾自己的过去。
波伏瓦:你认为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
萨特:当我的年龄正好合适时,我没有热切地全心全意地同某些人结合在一起。
波伏瓦:你的意思是指战前?
萨特:战前和战后。
波伏瓦:你可以与谁结合成一体呢?
萨特:那儿毕竟有一个不是***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
波伏瓦:你已经尽可能地去接近他们了。
萨特:大概不全是这样。有些***人左派团体对正统的共产主义提出挑战,有时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我没有打算去了解他们。直到1966年,我对有关这个***人左派的一切事情都没有注意。
我认为政治就是对待社会党人和***人的问题,此外没有了。跟我周围的人一样我仍然被1939年战争前旧人民阵线深刻影响着。后来我发现我本来应该同年轻的左翼分子结合在一起。
波伏瓦:但有一些时刻你作出了决定。回顾起来,有哪些选择是你感到十分庆幸的?比如说我想你不会因为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态度而不高兴吧?
萨特:对,我想这种态度是必然采取的。
波伏瓦:你为阿尔及利亚独立而斗争的热望挫败了***人,你比他们走得远多了。
萨特:是的。他们只希望独立的可能性,而我同阿尔及利亚人一起,希望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我可以补充说一句,我不理解***人的谨慎。
波伏瓦:***人有时做事是很古怪的。他们投了授予全权票。
萨特:对的,我不理解***人的态度。这清楚地表明,像我常说的那样,他们不希望***。
波伏瓦:显然是这样。当时我们认为他们是想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大党,因此是一个取悦于法国人的党,他们必须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愿意人们说他们把殖民地贱价出卖掉。
萨特:但做民族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做殖民主义者。
波伏瓦:在当时…………
萨特:做一个民族主义者意味着同你诞生和生活的国家有着很强的结合力。这不意味着你要接受这个国家的一项确定的政策----例如,一种殖民主义政策。
波伏瓦:但你不认为他们的态度是有煽动性的吗?他们不愿任何人有可能说他们是反法国的人。
萨特:是的,他们确实如此。
波伏瓦: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有时同他们合作。我记得一起举行过一些示威活动。最后,在同秘密军队组织作斗争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同盟,其中有***人,你当时说,“一个人不可能同他们一起做任何事;但没有他们也不可能做任何事。”关于这种联合的努力你还记得些什么吗?
萨特:有段时间进行得还不坏…………
波伏瓦:但你同他们从没有过友谊关系,对不对?
萨特:对的。
波伏瓦:《死无葬身之地》上演后,爱伦堡对你说,你这样谈抵抗战士是可耻的。在《肮脏的手》上演后,他是那些说你为一份浓汤而出卖自己灵魂的人中的一个。而后来你忽然同他在一起,微笑着。1955年在赫尔辛基,我看到你同爱伦堡在一起,你们都在微笑。我们同他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他死。这是怎么回事?这不使你认为他…………
萨特:这不使我烦恼;他是表示友好的人。在莫斯科我再次表达了我的很大的热诚,他接待了我,在他同他妻子和姊妹住的别墅。我去看他时----我们在一个会议上见了面,但仅仅握了一下手----我主动去拜访他时,我是很乐于见到他的。有时我们之间是很轻松的,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总是很好的。而且我是真正喜欢爱伦堡。
波伏瓦:但总的说来,***对待你的方式----例如,对于有关亨利马丁的那本书----是没有真正人的、个人的深信不疑的友谊关系可言的;你对此感到不愉快吧?
萨特:对,这很令人不快。这种关系实在令人讨厌,这是我同他们完全断绝关系的原因;我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另一方面,我认识的毛主义者使人感动的地方是,他们把人当人看。
波伏瓦:你在《现代》上谴责劳动营的存在,你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你说,苏联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虽然充满了错误,但仍然是社会主义,你为什么说这话?
萨特:这话是我弄错了。它再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消失不见了:当时它本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但由于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后一些年的列宁,它逐渐改变了。
波伏瓦:你不再认为***是***的,但你认为***人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我相信这是你认为的东西。
萨特:对,确实如此。因为当时我看到同这个党联系在一起充满错误----这些错误往往被显露出来----的罢工、工会政策、法国总工会和工人政策。我想解释一下对那些同我相识的***人的看法。他们掩饰着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微笑着,回答着我的问题,但实际上作答的不是他们。“他们”消失不见了,变成了知道他们的原则并根据《人道报》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给予的东西来进行回答的人。
波伏瓦:像一种有程序的计算机。
萨特:我和他们之间,除了一起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直接的一致外,从没有过团结一致。
波伏瓦:但你仍同他们呆在一起?
萨特:因为再没有别的我可以与之发生政治关系的人。实际上他们有一种个人生活;那是在他们多少去掉自己的假面时;但那仅仅是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他们同外来者的关系中是没有兄弟之情的。
波伏瓦:有一个时期你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比较接近,他们采取的立场多少有点类似你在布达佩斯事件后的立场,他们是不是因此而被开除出党或退党?
萨特:大约是1957年,有维格尔、维克多勒迪克和其他人试图实现一种跟党没有根本区别、略作调整的政策。他们努力的方向跟我在“Fac”相仿佛;他们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态度跟我是相同的。
波伏瓦:韦科尔以一种多少有点开玩笑的口气说,他觉得自己对于***说来有如一个起很大装饰作用的瓷瓶;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萨特:完全没有。这跟韦科尔的时期完全不同。
波伏瓦:这么说来,韦科尔比你更驯服一些。他更像一个瓷花瓶。
萨特:我常常在会议上看到他,他讲话,表述一种往往是党的意见的观点。然后坐下一言不发。但***人让我主动地活动。我们共同决定某种活动,一个组织公开集会的活动,每个人在这个活动中都有比较确定的作用,我也讲一些我必须讲的话。这一切都很自然,我谴责***人的不是这个。我谴责他们的是,他们否弃一切主观性,缺乏任何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波伏瓦:你认为自己试图同***人一起工作是不是浪费时间?
萨特:不,不是浪费时间。我使我知道一个***员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同毛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他们也无法同***人友好相处,而我发现自己同他们倒合得来,因为他们在同***打交道中有跟我相同的感受。
波伏瓦:如果你没有打算同***人一起工作,如果你保有较多的时间去写作和搞哲学,如果你离政治背景较远一些,那么,你同毛主义者现在的关系会有不同吧?
萨特:是的。因为我是通过政治接近毛主义者。这是通过对1968年的反思,自己介入而站在毛主义者一边;而这必然隐含着在占领期和解放时期我所干的事情----我不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同人们结合在一起,而他们理解我。不,如果我在这以前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在我这个年纪我不会同毛主义者在一起。我可能会继续不关心政治。当你活动于一个运动之中时,必然有着开始和继续干下去;可以说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什么叫浪费时间?可以说这是浪费时间,但也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你得到了关于人们的知识,学会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或者正相反,你发现你和他们之间可能工作得很好。
波伏瓦:现在你的政治前景是怎样的?
萨特:我老了。我六十九岁了,我认为我现在无法从事任何可以看到结果的事情。
波伏瓦:你是什么意思?
萨特:哦,我参加的任何运动,在它取得明确的形式和达到一定的目标之前,我已经不在了。虽然我不能最后取胜,但我总可以有一个开头,这也不错。目前我正在开头,而我看不到什么更明朗、更强有力的东西----有许多、许多人不愿意参加***,但仍然希望进行活动。
波伏瓦:***有没有希望更新或改变?或者你认为这完全不可能?
萨特:总之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所有的成年党员,或几乎所有的成年党员,都已经有一种假面具,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一台计算机。如果年轻人有所不同,事情大概要好一些,但我不可能看到它了。
波伏瓦:问题就在于,年轻的一代将给***提供新鲜血液,还是正相反,使之僵化。
萨特:正是这样。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