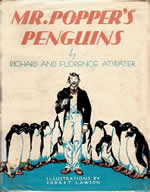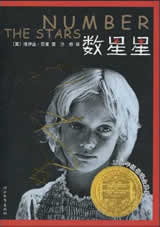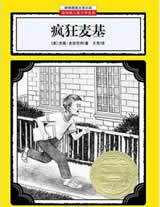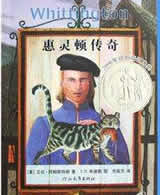羊群紧紧挤在一起,薄薄的鼻孔喷着气,纤细的前蹄不停地跺着地面,仰着脑袋朝羊栏奔去。羊群里腾起一股蒸气,冉冉上升到寒冷的空气里。河鼠和鼹鼠边说边笑,兴冲冲地匆匆走过羊群。一整天。他们和水獭一道在广阔的高地上打猎探奇,那儿是注入他们那条大河的几条山洞的源头。现在他们正穿越田野往家走。冬天短短的白昼将尽,暮色向他们逼来,可他们离家还有相当的路程。他们正踉踉跄跄在耕地里乱走时,听到绵羊的哗哗声,就寻声走来。现在,他们看到从羊栏那边伸过来一条踩平的小道,路好走多了。而且,他们凭着所有的动物天生具有的那种嗅觉,准确地知道,“没错,这条路是通向家的!”
“看来,前面像是一个村庄,”鼹鼠放慢了脚步,疑疑惑惑地说。因为,那条被脚踩出来的小道,先是变成了一条小径,然后又扩大成一条树夹道,最后引他们走上了一条碎石子路。村庄不大合两只动物的口味,他们平时常常过往的公路,是另一股道,避开了教堂、邮局或酒店。
“噢,没关系,”河鼠说。“在这个季节,这个时辰,男人呀,女人呀,小孩呀,狗呀,猫呀,全都安安静静呆在家里烤火。咱们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过去,不会惹事生非的。如果你愿意,咱们还可以从窗外偷瞧几眼,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
当他们迈着轻柔的脚步,踏着薄薄一层粉状的雪走进村庄时,十二月中旬迅速降临的黑夜已经笼罩了小小的村庄。除了街道两边昏暗的橘红色方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透过那些窗子,每间农舍里的炉火光和灯光,涌流到外面黑洞洞的世界。这些低矮的格子窗,多半都不挂窗帘,屋里的人也不避讳窗外的看客。他们围坐在茶桌旁,一心一意在干手工活,或者挥动手臂大声说笑,人人都显得优雅自如,那正是技艺高超的演员所渴求达到的境界——丝毫没有意识到面对观众的一种自然境界。这两位远离自己家园的观众,随意从一家剧院看到另一家剧院。当他们看到一只猫被人抚摸,一个瞌睡的小孩被抱到床上,或者一个倦乏的男人伸懒腰,并在一段冒烟的木柴尾端磕打烟斗时,他们的眼睛里不由得露出某种渴望的神情。
然而,有一扇拉上窗帘的小窗,在黑暗里,只显出半透明的一方空白。只有在这里,家的感觉,斗室内帷帘低垂的小天地的感觉,把外面的自然界那个紧张的大世界关在门外并且遗忘掉的感觉,才最为强烈、紧靠白色的窗帘,挂着一只鸟笼,映出一个清晰的剪影。每根铁丝,每副栖架,每件附属物,甚至昨天的一块舐圆了角的方糖,都清晰可辨、栖在笼子中央一根栖架上的那个毛茸茸的鸟儿,把头深深地埋在羽翼里,显得离他们很近,仿佛伸手就能摸到似的。他那圆滚滚的羽毛身子,甚至那些细细的羽尖,都像在那块发光的屏上描出来的铅笔画。正当他俩看着,那只睡意沉沉的小东西不安地动了动,醒了,他抖抖羽毛,昂起头。在他懒洋洋地打呵欠时,他们能看到他细小的喙张得大大的,他向四周看了看,又把头埋进翅下,蓬松的羽毛渐渐收拢,静止不动了。这时,一阵凛冽的风刮进他俩的后脖子,冰冷的雨雪刺痛了他们的皮肤,他们仿佛从梦中惊醒,感到脚趾发冷,两腿酸累,这才意识到,他们离自己的家还有一段长长的跋涉。
一出村庄,茅屋立时就没有了。在道路两旁,他们又闻到友好的田地的气息,穿过黑暗向他们扑来。于是他们打起精神,走上最后一段征途。这是回家的路,这段路,他们知道早晚是有尽头的。那时,门闩咔嚓一响,眼前突然出现炉火,熟悉的事物像迎接久别归来的海外游子一样欢迎他们。他们坚定地走着,默默不语,各想各的心事。鼹鼠一心想着晚饭。天已经全黑了,四周都是陌生的田野,所以他只管乖乖地跟在河鼠后面,由着河鼠给他带路。河鼠呢,他照常走在前面,微微佝偻着双肩,两眼紧盯着前面那条笔直的灰色道路。因此,他没怎么顾到可怜的鼹鼠。就在这当儿,一声召唤,如同电击一般,突然触到了鼹鼠。
我们人类,久已失去了较细微的生理感觉,甚至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形容一只动物与他的环境——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之间那种息息相通的交流关系。比如说,动物的鼻孔内日夜不停地发出嗡嗡作响的一整套细微的颤动,如呼唤、警告、挑逗、排拒等等,我们只会用一个“嗅”字来概括。此刻,正是这样一种来自虚空的神秘的仙气般的呼声,透过黑暗,传到了鼹鼠身上。它那十分熟悉的呼吁,刺激得鼹鼠浑身震颤,尽管他一时还记不起那究竟是什么。走着走着。他忽然定在那儿,用鼻子到处嗅,使劲去捕捉那根细丝,那束强烈地触动了他的电流。只一会,他就捉住它了,随之而来的是狂潮般涌上心头的回忆。
家!这就是它们向他传递的信息!一连串亲切的吁求,一连串从空中飘来的轻柔的触摸。一只只无形的小手又拉又拽,全都朝着一个方向!啊,此刻,它一定就近在眼前,他的老家,自打他第一次发现大河,就匆匆离去,再也不曾返顾的家!现在,它派出了探子和信使,来寻访他,带他回来。自打那个明媚的早晨离家出走后,他就沉浸在新的生活里,享受这生活带给他的一切欢乐、异趣、引人入胜的新鲜体验;至于老家,他连想也不曾想过。现在,历历往事,一涌而上,老家便在黑暗中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的家尽管矮小简陋,陈设贫乏,却是属于他的,是他为自己建造的家园,是他在劳碌一天之后愉快地回归的家园。这个家,显然也喜欢他,思念他,盼他回来。家正在通过他的鼻子,悲切地、哀怨地向他诉说,并不愤控,并不恼怒,只是凄楚地提醒他:家就在这儿,它需要他。
这呼声是清晰的,这召唤是明确的。他必须立即服从,回去。“鼠儿!”他满腔喜悦,兴奋地喊道,“停一下!回来!我需要你,快!”
“噢,走吧,鼹鼠,快来呀!”河鼠兴冲冲地喊,仍旧不停脚地奋力朝前走。
“停一停吧,求求你啦,鼠儿!”可怜的鼹鼠苦苦哀求,他的心在作痛。“你不明白!这是我的家,我的老家!我刚刚闻到了它的气味,它就近在眼前,近极了。我一定得回去,一定,一定!回来吧,鼠儿,求求你,求求你啦!”
这时河鼠已走在前面很远了,没听清鼹鼠在喊什么,也没听出鼹鼠的声音里那种苦苦哀求的尖厉的腔调。而且,他担心要变天,因为他也闻到了某种气味——他怀疑可能要下雪了。
“鼹鼠,咱们现在停不得,真的停不得!”他回头喊道。“不管你找到了什么,咱们明天再来瞧。可现在我不敢停下来——天已经晚了,马上又要下雪,这条路线我不太熟悉。鼹鼠,我需要依靠你的鼻子,所以,快来吧,好小伙!”河鼠不等鼹鼠回答,只顾闷头向前赶路。
可怜的鼹鼠独自站在路上,他的心都撕裂了。他感到,胸中有一大股伤心泪,正在聚积,胀满,马上就要涌上喉头,迸发出来。不过即便面临这样严峻的考验,他对朋友的忠诚仍毫不动摇,一刻儿也没想过要抛弃朋友。但同时,从他的老家发出的信息在乞求,在低声哺哺,在对他施放魔力,最后竟专横地勒令他绝对服从。他不敢在它的魔力圈内多耽留,猛地挣断了自己的心弦,下狠心把脸朝向前面的路,顺从地追随河鼠的足迹走去。虽然,那若隐若现的气味,仍旧附着在他那逐渐远去的鼻端,责怪他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
他费了好大劲才撵上河鼠。河鼠对他的隐情毫无觉察,只顾高高兴兴地跟他唠叨,讲他们回家后要干些啥。客厅里升起一炉柴火是多么惬意。晚饭要吃些什么。他一点没留心同伴的沉默和忧郁的神情。不过后来,当他们已经走了相当一段路,经过路旁矮树丛边的一些树桩时,他停下脚步,关切地说:“喂,鼹鼠,老伙计,你像是累坏了、一句话不说,你的腿像绑上了铅似的。咱们在这儿坐下歇会儿吧。好在雪到现在还没下,大半路程咱们已经走过了。”
鼹鼠凄凄惨惨地在一个树桩上坐下,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自己就要哭出来了。他一直苦苦挣扎,强压哭泣,可哭泣偏不听话,硬是一点一点往上冒,一声,又一声,跟着是紧锣密鼓的一连串,最后他只得不再挣扎,绝望地放声痛哭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他几乎找到的东西,一切都完了。
河鼠被鼹鼠那突如其来的大悲恸惊呆了,一时竟不敢开口。末了,他非常安详而同情地说:“到底怎么回事,老伙计?把你的苦恼说给咱听听,看我能不能帮点忙。”
可怜的鼹鼠简直说不出话来,他胸膛剧烈起伏,话到口中又给噎了回去。后来,他终于断断续续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的家是个——又穷又脏的小屋,比不上——你的住所那么舒适——比不上蟾宫那么美丽——也比不上獾的屋子那么宽大——可它毕竟是我自己的小家——我喜欢它——我离家以后,就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可我忽然又闻到了它的气味——就在路上,在我喊你的时候,可你不理会——过去的一切像潮水似的涌上我心头——我需要它!——天哪!天哪!——你硬是不肯回头,河鼠——我只好丢下它,尽管我一直闻到它的气味——我的心都要碎了——其实咱们本可以回去瞅它一眼的,鼠儿——只瞅一眼就行——它就在附近——可你偏不肯回头,鼠儿,你不肯回头嘛!天哪!天哪!”
回忆掀起了他新的悲伤狂涛,一阵猛烈的啜泣,噎得他说不下去了。
河鼠直楞楞地盯着前面,一声不吭,只是轻轻地拍着鼹鼠的肩。过了一会,他沮丧地喃喃说:“现在我全明白了!我真是只猪!——一只猪——就是我!——不折不扣一只猪——地地道道一只猪!”
河鼠等着,等到鼹鼠的哭泣逐渐缓和下来,不再是狂风暴雨,而变得多少有节奏了,等到鼹鼠只管抽鼻子,间或夹杂几声啜泣。这时,河鼠从树桩上站起来,若无其事地说:“好啦,老伙计,咱们现在动手干起来吧!”说着,他就朝他们辛辛苦苦走过来的原路走去。
“你上(嗝)哪去(嗝),鼠儿?”泪流满面的鼹鼠抬头望着他,惊叫道。
“老伙计,咱们去找你的那个家呀,”河鼠高兴地说,“你最好也一起来,找起来或许要费点劲,需要借助你的鼻子呀。”
“噢,回来,鼠儿,回来!”鼹鼠站起来追赶河鼠。“我跟你说,这没有用!太晚了,也太黑了,那地方太远,而且马上又要下雪!再说——我并不是有意让你知道我对它的那份感情——这纯粹是偶然的,是个错误!还是想想河岸,想想你的晚饭吧!”
“什么河岸,什么晚饭,见鬼去吧!”河鼠诚心诚意地说。“我跟你说,我非去找你的家不可,哪怕在外面呆一整夜也在所不惜。老朋友,打起精神,挽着我的臂,咱们很快就会回到原地的。”
鼹鼠仍在抽鼻子,恳求,勉勉强强由着朋友把他强拽着往回走。河鼠一路滔滔不绝地给他讲故事,好提起他的情绪,使这段乏味的路程显得短些。后来,河鼠觉得他们似乎已经来到鼹鼠当初给“绊住”的地方,就说,“现在,别说话了,干正事!用你的鼻子,用你的心来找。”
他们默默地往前走了一小段路,突然,河鼠感到有一股微弱的电颤,通过鼹鼠的全身,从他挽着的胳臂传来。他立即抽出胳臂,往后退一步,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有一刻,鼹鼠僵直地站定不动,翘鼻子微微颤动,嗅着空气。
然后,他向前急跑了几步——错了——止步——又试一次;然后,他慢慢地、坚定地、信心十足地向前走去。
河鼠特兴奋,亦步亦趋地紧跟在鼹鼠身后。鼹鼠像梦游者似的,在昏暗的星光下,跨过一条干涸的水沟,钻过一道树篱,用鼻子嗅着,横穿一片宽阔的、光秃秃没有路径的田野。
猛地,没有作出任何警告,他一头钻到了地下。幸亏河鼠高度警觉,他立刻也跟着钻了下去,进到他那灵敏的鼻子嗅出的地道。
地道很狭窄,憋闷,有股刺鼻的土腥味。河鼠觉得他们走了很久很久,才走到尽头,他才能直起腰来,伸展四肢,抖抖身子。鼹鼠划着一根火柴,借着火光,河鼠看到他们站在一块空地上。地面扫得于干净净,铺了一层沙子,正对他们的是鼹鼠家的小小前门,门旁挂着铃索,门的上方,漆着三个黑体字:“鼹鼠居”。
鼹鼠从墙上摘下一盏灯笼,点亮了,河鼠环顾四周,看到他们是在一个前庭里。门的一侧,摆着一张花园坐椅,另一侧,有个石磙子。这是因为,鼹鼠在家时爱好整洁,不喜欢别的动物把他的地面蹴出一道道足痕,踢成一个个小土堆。墙上,挂着几只金属丝篮子,插着些羊齿植物,花篮之间隔着些托架,上面摆着泥塑像——有加里波的,有年幼的萨缪尔,有维多利亚女王,还有其他意大利英雄们。在前庭的下首,有个九柱戏场,周围摆着条凳和小木桌,桌上印着一些圆圈,是摆啤酒杯的标志。庭院中央有个圆圆的小池塘,养着金鱼,四周镶着海扇贝壳砌的边。池塘中央,矗立着一座用海扇贝壳贴面的造型奇特的塔,塔顶是一只很大的银白色玻璃球,反照出来的东西全都走了样,怪滑稽的。
看到这些亲切的物件,鼹鼠的脸上绽开了愉快的笑意。他把河鼠推进大门,点着了厅里的一盏灯,匆匆扫了一眼他的旧居。他看到,所有的东西都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看到长久被他遗忘的屋子的凄凉景象,看到它的开间是那么狭小,室内陈设又是那么简陋陈旧,禁不住又沮丧起来,颓然瘫倒在椅子上,双爪捂住鼻子。“鼠儿啊!”他悲悲戚戚地哭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在这样寒冷的深夜,把你拉到这个穷酸冰冷的小屋里来!要不然,你这时已经回到河岸,对着熊熊的炉火烤脚,周边都是你的那些好东西!”
河鼠没有理会他悲哀的自责,只顾跑来跑去奔忙着,把各扇门打开,察看各个房间和食品柜,点着许多盏灯和蜡烛,摆得满屋子都是。“真是一所顶呱呱的小屋!”他开心地大声说。“多紧凑啊!设计得多巧妙啊!什么都不缺,一切都井然有序!今晚咱俩会过得很愉快的。头一件事,是升起一炉好火,这我来办——找东西,我最拿手。看来,这就是客厅啰?太好了!安装在墙上的这些小卧榻,是你自己设计的吗?真棒!我这就去取木柴和煤,你呢,鼹鼠,去拿一把掸子——厨桌抽屉里就有一把——把灰尘掸掸干净。动手干起来吧,老伙计!”
同伴热情的激励,使鼹鼠大受鼓舞,他振作起来,认真努力地打扫擦拭。河鼠一趟又一趟抱来柴禾,不多会就升起一炉欢腾的火,火苗呼呼地直窜上烟囱。他招呼鼹鼠过来烤火取暖。可是鼹鼠忽然又忧愁起来,沮丧地跌坐在一张躺椅上,用掸子捂着脸。
“鼠儿呀,”他呜咽道,“你的晚饭可怎么办?你这个又冷又饿又累的可怜的动物,我没有一点吃的招待你——连点面包屑都没有!”
“你这个人哪,怎么这样灰溜溜!”河鼠责备他说。“你瞧。刚才我还清清楚楚看见橱柜上有把开沙丁鱼罐头的起子,既然有起子,还愁没有罐头?打起精神来,跟我一道去找。”
他们于是翻橱倒柜,满屋子搜寻。结果虽不太令人满意,倒也不太叫人失望,果然找到一听沙丁鱼,差不多满满一盒饼干,一段包在银纸里的德国香肠。
“够你开宴席的了!”河鼠一面摆饭桌,一面说。“我敢说,有些动物今晚要是能和我们一道吃晚饭,简直求之不得啦!”
“没有面包!”鼹鼠哭丧着脸呻吟道;“没有黄油,没有——”
“没有鹅肝酱,没有香摈酒!”河鼠撇着嘴嘲笑说。“我倒想起来了——过道尽头那扇小门里面是什么?当然是你的储藏室啰!你家的好东西全都在那儿藏着哪!你等着。”
他走进储藏室,不多会儿又走出来,身上沾了点灰,两只爪子各握着一瓶啤酒,两腋下也各夹着瓶啤酒。“鼹鼠,看来你还是个挺会享受的美食家哩,”他评论说。“凡是好吃的,一样不少哇。这小屋比哪儿都叫人高兴。喂,这些画片,你打哪儿弄来的?挂上这些画,这小屋更显得像个家了。给咱说说,你是怎么把它布置成这个样儿?”
在河鼠忙着拿盘碟刀叉,往蛋杯里调芥末时,鼹鼠还因为刚才的感情激动而胸膛起伏,他开始给河鼠讲起来,起先还有几分不好意思,后来越讲越带劲,无拘无束了。他告诉他,这个是怎样设计的,那个是怎样琢磨出来的,这个是从一位姑妈那儿意外得来的,那个是一项重大发现,买的便宜货,而这件东西是靠省吃俭用,辛苦攒钱买来的。说着说着,他的情绪好了起来,不由得用手去抚弄他的那些财物。他提着一盏灯,向客人详细介绍它们的特点,把他俩都急需的晚饭都给忘到脑后了。河鼠呢,尽管他饿极了,可还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于,认真地点着头,皱起眉头仔细端详,瞅空子就说“了不起”,“太棒了”。
末了,河鼠终于把他哄回到饭桌旁,正要认真打开沙丁鱼罐头时,庭院里传来一阵声响——像是小脚丫儿在沙地上乱跺,还有小嗓门儿七嘴八舌在说话。有些话断断续续传到他们耳中——“好,现在大家站成一排——托米,把灯笼举高点——先清清你们的嗓子——我喊一、二、三以后,就不许再咳嗽——小比尔在哪?快过来,我们都等着呐——”
“出什么事啦?”河鼠停下手里的活,问道。
“准是田鼠们来了,“鼹鼠回答说,露出颇为得意的神色。“每年这个时节,他们照例要上各家串门唱圣诞歌,成了这一带的一种风尚。他们从不漏过我家——总是最后来到鼹鼠居。我总要请他们喝点热饮料,要是供得起,还请他们吃顿晚饭。听到他们唱圣诞歌,就像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咱们瞧瞧去!”河鼠喊道,他跳起来,向门口跑去。
他们一下子把门打开,眼前呈现出一幅美丽动人的节日景象。前庭里,在一盏牛角灯笼的幽光照耀下,八只或十只小田鼠排成半圆形站着,每人脖子上围着红色羊毛长围巾,前爪深深插进衣袋,脚丫子轻轻跺着地面保暖。珠子般的亮眼睛,腼腆地互视了一眼,窃笑了一声,抽了抽鼻子,又把衣袖拽了好一阵子。大门打开时,那个提灯笼的年纪大些的田鼠喊了声“预备——一、二、三!”跟着尖细的小嗓就一齐唱了起来,唱的是一首古老的圣诞歌。这首歌,是他们的祖辈们在冰霜覆盖的休耕地里,或者在大雪封门的炉边创作的,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每逢圣诞节,田鼠们就站在泥泞的街道上,对着灯光明亮的窗子,唱这些圣诗。
《圣诞颂歌》
全村父老乡亲们,在这严寒时节,
大开你们的家门,
让我们在你炉边稍歇,
尽管风雪会趁虚而入,
明朝你们将得欢乐!
我们站在冰霜雨雪里,
呵着手指,跺着脚跟,
远道而来为你们祝福——
你们坐在火旁,我们站在街心——
祝愿你们明晨快乐!
因为午夜前的时光,
一颗星星指引我们前行,
天降福祉与好运——
明朝赐福,常年得福,
朝朝欢乐无穷尽!
善人约瑟在雪中跋涉——
遥见马厩上空星一颗;
玛丽亚无须再前行——
欢迎啊,茅屋,屋顶下的产床!
明晨她将得欢乐!
于是他们听到天使说:
“首先欢呼圣诞的谁?
是所有的动物,
因为他们栖身在马厩,
明晨欢乐将属于他们!”
歌声停止了,歌手们忸怩地微笑着,相互斜睨一眼,然后是一片寂静——但只一会儿。接着,由远远的地面上,通过他们来时经过的隧道,隐隐传来嗡嗡的钟声,丁丁当当,奏起了一首欢快的乐曲。
“唱得太好了,孩子们!”河鼠热情地喊道。“都进屋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吃点热东西!”
“对,田鼠们,快进来,”鼹鼠忙喊道。“跟过去一个样!关上大门。把那条长凳挪到火边。现在,请稍候一下,等我们——唉,鼠儿!”他绝望地喊,颓然坐在椅子上,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咱们都干些什么呀?咱们没有东西请他们吃!”
“这个,就交给我吧,”主人气派十足的河鼠说。“喂,这位打灯笼的,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告诉我,这个时辰,还有店铺开门吗?”
“当然,先生,”那只田鼠恭恭敬敬地回答。“每年这个季节,我们的店铺昼夜都开门。”
“那好!”河鼠说。“你马上打着灯笼去,给我买——”
接着他俩又低声嘀咕了一阵,鼹鼠只零星听到几句,什么——“注意,要新鲜的!——不,一磅就够了——一定要伯金斯的出品,别家的我不要——不,只要最好的——那家要是没有,试试别家——对,当然是要家制的,不要罐头——好吧,尽力而为吧!”然后,只听得一串丁当声,一把硬币从一只爪子落进另一只爪子,又递给田鼠一只购物的大篮子,于是田鼠提着灯笼,飞快地出去了。
其余的田鼠,在条凳上坐成一排,小腿儿悬挂着,前后摆动,尽情享受炉火的温暖。他们在火上烤脚上的冻疮,直烤得刺痒痒的。鼹鼠想引着他们无拘无束地谈话,可没成功,就讲起家史来,要他们逐个儿报自己那许多弟弟的名字、看来,他们的弟弟因为年纪还小,今年还不让出门唱圣诞歌,不过也许不久就能获得父母的恩准。
这时,河鼠在忙着细看啤酒瓶上的商标。“看得出来,这是老伯顿牌的,”他赞许地评论说。“鼹鼠很识货呀!是地道货!现在我们可以用它来调热甜酒了!鼹鼠,准备好家什,我来拔瓶塞。”
甜酒很快就调好了,于是把盛酒的锡壶深深插进红红的火焰里;不一会,每只田鼠都在啜着,咳着,呛着(因为一点点热甜酒劲头就够大的),又擦眼泪,又笑,忘记了他们这辈子曾经挨冻来着。
“这些小家伙还会演戏哩,”鼹鼠向河鼠介绍说。“戏全是由他们自编自演的。演得还真棒!去年,他们给我们演了一出精彩的戏,讲的是一只田鼠,在海上被北非的海盗船俘虏了,被迫在船舱里划桨。后来他逃了出来,回到家乡时,他心爱的姑娘却进了修道院。喂,你!你参加过演出的,我记得。站起来,给咱们朗诵一段台词吧。”
那只被点名的田鼠站起来,害羞地格格笑着,朝四周扫了一眼,却张口结舌,一句也念不出。同伴们给他打气,鼹鼠哄他,鼓励他,河鼠甚至抓住他的肩膀一个劲摇晃,可什么都不管用,他硬是摆脱不了上场昏。他们围着他团团转,就像一帮子水手,按照皇家溺水者营救协会的规则,抢救一个长时间溺水的人那样。这时,门闩卡嗒一声,门开了,打灯笼的田鼠被沉甸甸的篮子压得趔趔趄趄,走了进来。
等到篮子里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股脑倾倒在餐桌上时,演戏的事就再也没人提了。在河鼠的调度下,每只动物都动手去干某件事或取某件东西。不消几分钟,晚饭就准备停当。鼹鼠仿佛做梦似的,在餐桌主位坐定,看到刚才还是空荡荡的桌面,现在堆满了美味佳肴,看到他的小朋友们个个喜形于色,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他自己也放开肚皮大嚼那些魔术般变出来的食物。他心想,这次回家,想不到结果竟如此圆满。他们边吃边谈,说些往事。田鼠们告诉他最近的当地新闻,还尽力回答他提出的上百个问题。河鼠很少说话,只关照客人们各得所需,多多享用,好让鼹鼠一切不必操心。
最后,田鼠们卿卿喳喳,一迭连声地道谢,又祝贺主人节日愉快,告辞离去了,他们的衣兜里都塞满了纪念品,那是带给家里的小弟妹们的。等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大门关上,灯笼的叮咚声渐渐远去时,鼹鼠和河鼠把炉火拨旺,拉过椅子来,给自己热好睡前的最后一杯甜酒,就议论起这长长的一天里发生的事情。末了,河鼠打了个大大的呵欠,说,“鼹鼠,老朋友,我实在累得要死啦。‘瞌睡’这个词儿远远不够了。你自己的床在那边是吧?那我就睡这张床了。这小屋真是妙极了!什么都特方便顺手!”
河鼠爬进他的床铺,用毯子把自己紧紧裹住,立刻沉入了梦乡的怀抱,就像一行大麦落进了收割机的怀抱一样。
倦乏的鼹鼠也巴不得快点睡觉,马上就把脑袋倒在枕头上,觉得非常舒心快意。不过在合眼之前,他还要环视一下自己的房间。在炉火的照耀下,这房间显得十分柔和温煦。火光闪烁,照亮了他所熟悉的友好的物件。这些东西早就不知不觉成了他的一部分,现在都在笑眯眯毫无怨言地欢迎他回来。他现在的心境,正是机敏的河鼠不声不响引他进入的那种状态。他清楚地看到,他的家是多么平凡简陋,多么狭小,可同时也清楚,它们对他有多么重要,在他的一生中,这样的一种避风港具有多么特殊的意义。他并不打算抛开新的生活和明朗的广阔天地,不打算离开阳光空气和它们赐予他的一切欢乐,爬到地下,呆在家里。地面世界的吸引力太强大了,就是在地下,也仍不断地召唤着他。他知道,他必须回到那个更大的舞台上去。不过,有这么个地方可以回归,总是件好事。这地方完全是属于他的,这些物件见到他总是欢天喜地,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总会受到同样亲切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