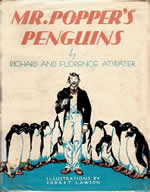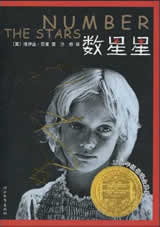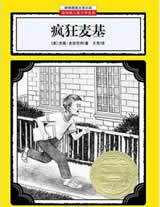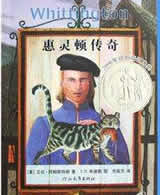接下来的事我可不记得了。我隐隐约约记得自己心力交瘁,贝特里奇把我带到他那间起居室。看到贝特里奇老头那张亲切的脸,我感到说不出的舒服。我说:“我就跟你一样,根本一点也不知道我自己偷了那颗钻石。可是有个对我不利的证据!睡衣上的漆,睡衣上的名字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呀!”
“您伸手摸进箱子里的时候,难道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我这才想起口袋里那封信。我取出信,信上签着字:罗珊挪-史柏尔曼。我开始念了。
“少爷:
我坦白这件事是非常痛苦的,我的坦白只有三个字:我爱您。”
那封信从手里掉了下去,这是怎么回事?
“请再念下去,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少爷。”
我就重新念信。这是封长信,写的是她那段伤心史,对我竟在一见倾心,后来就出了丢失钻石的事。门上发现一块漆斑,她跟总管女儿谈过一番以后,知道这漆斑只有晚上来过的人才会擦掉。那天早晨,到我房里去收拾,她看见我的睡衣扔在床上,想折好――就看见从雷茜儿小姐房门上沾来的漆!她看了大吃一惊,跑到自己房里,反锁了门。她拿住了一个把柄,证明我晚上到过雷茜儿小姐的房里!开头她一醋劲儿,后来她终于相信是我偷了那颗钻石。她认为我已经自甘下流,跟她成了一路。她还认为手头有我那件睡衣,就掌握了我唯一的罪证,有个机会可以赢得我的欢心。
克夫探长一踏进屋子,屋里所有人的麻布衣服就逃不了受检的难关。藏暗它上弗利辛霍去,做了件新睡衣,再把新睡衣代替丢掉的那件,跟我的衣物放在一起。罗珊娜几次想找我谈话,都没谈成。她拿定个主意,打算把睡衣藏在激沙滩里,她虽是可怜虫,不愿把她唯一能够证明她救了我的证据毁掉。她从没死过心,可是,她心里又暗自说着,要是她再错过接近我的机会,要是我再那么狠心,她就要与世永别了。这封信署名是:“您永远忠实的爱人和卑贱的仆人,罗珊娜顿首。”
信念完了,我们默不作声的坐着。到后来,贝特里奇终于打破了沉默。“弗兰克林先生,您能不能干脆一句话告诉我,这一团乱麻中,您看出什么头绪吗?”我说:“我看只有回伦敦一条路,去跟布罗夫先生和克夫探长商量商量……”
我刚说了这句话,门外有人在敲门。
“不管哪位,进来吧,”贝特里奇暴躁地说。
门开了,悄悄进来一个面目非常特别,前所未见的人。看他的身材和举止,他还年轻。但看他的脸孔,他比贝特里奇还显得老。肤色黝黑。两颊凹陷,鼻梁端正,古代的东方人通常总是长着这种鼻子。他脸上的皱纹多得数不清。在这张怪脸上,一对眼睛比脸还要怪,深深凹了进去。“对不起,”他说,“我没料到贝特里奇先生有客。”他把一张纸条递给贝特里奇,就跟时来时那样悄悄的走出了房。
“那是谁?”我问道。
“坎迪先生的助手,”贝特里奇说,“说起来,那个小个子医生从那天吃了寿酒回家,得了病以后,就没复元过,他也没法子,只好将就的找这个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人。”
“看来你不喜欢他,贝特里奇?”
“谁也不喜欢他,少爷。”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这名字不能再难听了,”贝特里奇气呼呼地说。“叫埃兹拉-吉宁士。”
我记下了这个名字,感到这里气氛是那样压抑,决定走了。
我到火车站去,由贝特里奇陪着。我口袋里放着那封信,手提包里放着那件睡衣,这两件东西都要交给布罗夫先生去研究。我们默不作声的离开那屋子。我倒底耐不住沉闷,开腔说,“贝特里奇,雷茜儿生日那天晚上,我喝醉了没有?”
“您喝醉啦!”他大声叫道。我又问:“贝特里奇,在没出国以前,你看见我有梦游症吗?”
“梦游,少爷?您一生从没梦游过!”
听了这句话又觉得贝特里奇一定不错,要是我有梦游症,准有有不少人见过我梦游,他们就会警告我。
我虽承认这一切,但还是固执的抱着当时我仅能看到的那套看法,贝特里奇看透了这一点,马上把我这两种论调驳得体无完肤,站不住脚。
“很好,少爷。我们就说您偷宝石那时是喝醉了酒,或者是在梦游。嘿,那您把宝石带到伦敦去那时,是不是喝醉了酒呢?难道梦游到鲁克先生那儿去的?因此您自己还不配下结论。您越早见着布罗夫先生越好。”
我们走到车站,只剩下一两分钟了。我正在跟贝特里奇话别,我又看见坎迪先生那个面目特别的助手了,我们的眼光碰上了。埃兹拉-吉宁士对我脱帽为礼。火车刚开,我心里纳闷,一天之内怎么会两次看见这个头发花白的人!
那天傍晚,我到了布罗夫先生的寓所。他马上领我到书房,打发听差通知他太太小姐别来打扰我们,随后就全神贯注看罗珊娜的信,看完信,布罗夫先生说:“弗兰克林,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你跟雷茜儿都关系重大。她那古怪的举动,如今可不是个谜了。她以为你偷了那颗钻石。”我只好承认他下的那个可怕的结论完全正确。
“头一步该去恳求雷茜儿,”布罗夫先生接下去说。“这段日子里,她为了你一直保持沉默,一定得求她说出来,她凭什么认为是你偷了宝石。如果她说了出来,这件案子就迎刃而解了。”
“你这番话真叫我心里舒服,”我说。“不过我想知道,怎么样……”
“两分钟之内我就能告诉你,”布罗夫先生插嘴说。“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钻石丢失那天晚上,穿这件睡衣的人就是你?”
他驳得我开不了口啦。
“至于这个,”律师拿起罗珊娜的自白书说道,“我能了解这对你是件痛苦的事。但我跟你的地位不同。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份文件。因此我可以疑心她没把实话全都说出来。如果雷茜儿光凭着这件睡衣作为证据来怀疑你,那么这件睡衣九成倒是罗珊娜给雷茜儿看的。这女人的信上证明她嫉妒雷茜儿。我不想追究是谁偷了那颗钻石――罗珊娜为了要达到目的,就是五十颗月亮宝百她也会拿――就此趁机害得你跟雷茜儿一辈子不和。”
“我看那封信时,心里也有过这种猜疑。不过要是事后证明真是我穿这件睡衣的,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不谈这问题。日后我们看看雷茜儿是不是光凭着那件睡衣作为证据来怀疑你的。你好好想一想,再回答我的这句话:你住在她公馆里时有没有出什么事,叫雷茜儿看了不信你是个正人君子。
贝特里奇写的故事第八章中,提到有个外国人为了我欠巴黎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一笔债,上我姨她家来找我。这个外国人脾气暴躁,我们双方就此唇枪舌剑的争了起来。范林太夫人得知是怎么回事以后,就立刻把钱还给他。雷茜儿后来也知道这回事,她说我“卑鄙无耻”、“没有骨气”:“不知我下步会做出什么事来”,以及诸如类的话。我们吵了嘴。雷茜儿记得那回不幸的事吗”布罗夫先生马上对这问题作了正面的答复。
他站起来,开始在房里若有所思的走来走去。我打定主意亲自找雷茜儿谈一谈。布罗夫先生听到这话,大为惊讶。不过他承认我有个有利的机会――换句话说,雷茜儿还有点喜欢我呢。
这一来事情也许会就此水落石出。问题是――我怎么去见她?
“她在你府上作过客,”我说。“我冒昧的建议在这儿见她,成吗?”“我同意。我要请雷茜儿上这儿来玩一天;后天我就通知你。”
我千恩万谢的回到伦敦寓所。第三天早晨,布罗夫先生来了,他交给我一把大钥匙,他说,“她要来陪我妻子和女儿玩一个下午。“这是我后墙上大门的钥匙。今天下午三点到那儿去。你开门走进,会在音乐室里碰到雷茜儿――一个人。”
我还要牵肠挂肚的等上好几个钟头呢,为了打发时间,我看看信。有一封是贝特里奇写来的。
我心急如焚的拆开信,信上没什么重要消息,看到第二句,就又出现了那个出现多次的埃兹拉-吉宁士!那天贝特里奇刚走出车站,半路上就给他拦住,打听我是谁。事后他告诉他的上手坎迪先生,说他看见了我。坎迪先生马上乘了车去找贝特里奇,说他有事想找我谈谈,等我下回再到请求我通知他,这就是信里的大概内容。
我把信揉成一团放在袋里,过一会儿就忘了,一心一意的想着去见雷营儿。
汉普斯特德教堂的大钟打了三下,我就把布罗犬先生那把钥匙插进墙上大门的锁眼里,打开了门。
我在门口刚一露脸,雷茜儿就一骨碌从钢琴边站起身。我向她迎上几步,柔声说:“雷茜儿!”她听了我这一声喊,身上重新现出了活力,脸上也恢复了血色。她照旧一言不发的走上前来,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将她搂在怀里,在她的脸上吻个遍。
我一时以为她也在吻我。谁知她吓得大叫一声,把我推开。“你这个胆小鬼!”她说。“你这个卑鄙下流,无情无义的胆小鬼!”这就是她劈头一句话。
这种侮辱实在受不了。但我心平气和地说:“如果你认为我卑鄙无耻,我立刻就走。刚才说我干了这等好事,我干了什么来着?”
“你干了什么来着!你竟问我?我一直没把你干的那种丑事说出来,我替你遮丑,自己反受罪。难道你竟不知感恩吗?从前我喜欢你,我更喜欢你……”
她声音哽住了,倒在一张椅子上,双手蒙住了脸。我等了一会才跟她说话,“要是你不肯先说,”我说,“那我就得先说了。我到这儿来是要跟你谈件正经事。”
她不动弹,也不答理。我把自己在激沙滩发现的事讲给她听。
“我有句话问你,”我说。“我不得不重新提到一个痛心的问题,罗珊娜把睡衣给你看过吗?”
她霍的跳起身,向我迎面走来,“你疯了?”她问。”
我还是沉住气,镇静地说:“雷茜儿,请你回答我呀”:据说你一死,你就成了个财主。你上这儿来是赔我钻石的?”
我再也忍不住了,“你完全把我看错了!你疑心我偷了你的钻石。我有权利想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疑心你!”她大声叫道,她也跟我一样冒火了。“你这坏蛋,我亲眼看见你偷那颗钻石的!”
我突然听到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禁吓得不知所措。我虽然是平白受冤,也只好默默无言的站在她面前。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羞着无地自容的人。我突然默不作声,倒叫她吓了一跳,“你干吗到这儿来自讨没趣?”
我向她迎上前去,简直不知自己在做些什么。我一听见她说到亲眼目睹的铁证,心里就糊涂了。我握住她的手。我想斩钉截铁的说几句,但说得出口的只是,“雷茜儿,你从前爱过我的呀。”
她打了个寒噤,手在我掌心里无力地发着抖。“放手,”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在手这么一握,我初进房时她听见我声音的反应又来了,我还可以左右她,我说,“我要你把我们当时彼此说了晚安,一直到你看见我偷那颗钻石这段时间里的一切事情告诉我。”
“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呢?”她大声问道。
“我回头告诉你为什么,把你生日那天晚上的事情回想一下,我们也许彼此取得谅解。”
她听了这话,心头仿佛又有了点希望,心甘心情愿的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先从那夭我们彼此说了晚安以后的事谈起吧。”我说。“当时你上床汉有?你睡着了吗?”
“没。那夜我睡不着。我在想你。”
她这回答几乎弄得我失魂落魄。我歇了一会儿,才能接着往下说。“你房里掌灯没有?”
“没――等到一点钟光景,我又起床,才点了蜡烛。”
“你离开卧室没有?”
“我正想出房。刚开门我就站住了脚,不能上起居室去了。”
“你为什么又不去了呢?”
“我看见房门下面有光;我还听到了脚步声,我吹掉蜡烛来不及回床,起居室那扇门就打开了,我看见了――你。”
“跟平时一样打扮?”
“不,穿着睡衣――手里拿着一支蜡烛。”
“你看得见我的脸吗?”
“看得见。清清楚楚的。你手里那支蜡烛把你脸照亮了。”
“我的眼睛开着吗?你看见我眼睛里有什么奇怪的神色吗?有没有一种茫茫然的发愣样子?”
“你的眼睛雪亮,比往常还要亮。你朝房里四下看看,仿佛怕被人看见似的。”
“你看见我走路的样子吗?”
“你象平时一样走法。你走到房间当中,站住脚,四下看看。”
“你看见了我,你怎么样呢?”
“我动不了。我吓呆了。我开不了口。我连动也动不了,没法去关门。”
“你站在那儿,我看得见吗?”
“照说你应该看得见。但你压根就没向我看,你一直走到墙角印度古玩橱那儿。你把蜡烛搁在橱顶上,把抽屉一格格打开,又一格格关上。等到找着那格放钻石的抽屉,你就伸手进去,拿出钻石。我看见那颗宝石在你大拇指和另外几个手指头中间闪闪发亮。”
“接下来怎么样?我有没有马上离开房间。”
“没。你一动不动站着,模样好象在想心思,后来你突然清醒过来,一直走出了房。”
“我关上门没有?”
“没,你匆匆走了出去,没把门关上,等到看不见你蜡烛的光,听不见脚步声,我就一个人留在暗里。”
“从那时候一直到全家都知道钻石丢失那段时间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出什么事。我压根就没回床。到早上,管家女儿照老时间进来以前,没出什么事。”
我放下她的手,站起身。梦游这种想法和喝醉这种念头,都证明一无是处,明摆着的是偷窃这个可怕的事实。如今我万念俱灰了。
“怎么样?”她说,“你问过了,我也答过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听她这种口气,我处境难堪,一筹莫展,竟失去自制。“如果你从前好好的亲口说破――”我开腔说。
她气冲冲的大叫一声,“噢!天底下还有这种人吗?我不顾心碎饶了你,你现在反咬一口说我应该亲口说破。我情愿丢掉五十颗钻石,也不愿看你象现在这样欺骗我!”
见她这样待我,真心痛如绞。她等了一会儿,才镇定下来。
“我应该好好的亲口说破,”她学着我的话说。“回头你就明白我对你是否公道。我没惊动全家人,也没把这事告诉大家,我想了又想――结果就写了封信给你。”
“我根本没收到过信。”
“我知道你根本没收到过信。等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原因了。信上说――我知道你欠着债,我母亲和我都知道你要用钱,我向你提议――借一大笔钱给你,要是需要的话,我亲自把那颗钻石抵押出去,”她大声叫着说,脸上又泛了红。“我写给你的就是这几句话。我打算让起居室的房门开一个早上,房里空着,我还一心指望你会趁这机会,把钻石偷偷放回抽屉里呢。”
我正想开口。
“我知道你要说你根本没收到过我的信。”她马上又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原因。我把信撕了。”
“什么缘故?”我问。
“这缘故再讲得通也没有了。这个主意刚打定,我竟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你――要请警察来,你最起劲;你带着头;你找宝石那份劲儿比谁都足!眼看你这副可怕的假惺惺面目,我就把信撕了。我逼不得已同你说话,难道你忘了我说的话吗?”
她的话我句句记得。当时我看见她这么激动,心里又惊讶又苦恼。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在阳台上跟我说知那话时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打算。
“我知道我说过什么话。我一次次的给你机会坦白,你竟然假装吃惊,脸上装作毫不知情――你是天底下最下流的混蛋!”
要是再待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话。我就走过她身边打开了门,“让我走吧,雷茜儿!”我说。
她拖我回来的时候,发狂似地越来越火。“你干吗到这儿来?你怕我揭穿你的秘密,我不会揭穿!我比你坏得多。我心里没法忘了你,就连事也忘不了!”她突然放了我,疯也似的使劲扭着双手。”啊,天呐!我瞧不起他,但我更瞧不起自己!
我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我再也忍不住了,“你总会知道你冤枉了我,”我说。“要不然你就永远也看不见我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她。她霍的站起身――我的好人儿呀!――跟在我后面,说了临别最后一句好心话。
“弗兰克林!”她说,“我原谅你!哦,弗兰克林!我们再也见不了面啦,说你原谅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