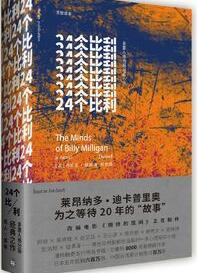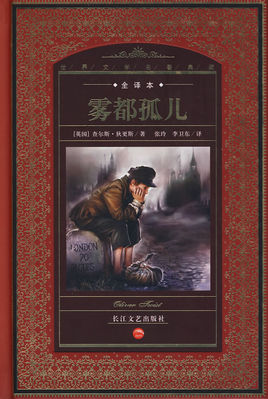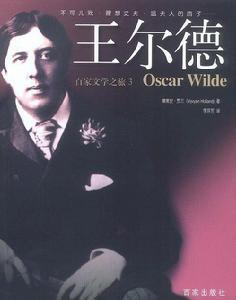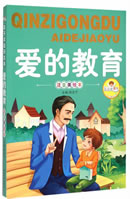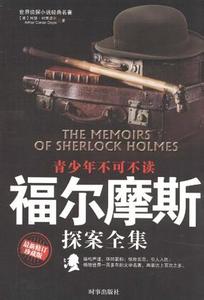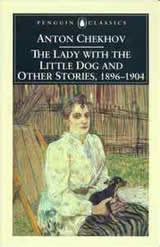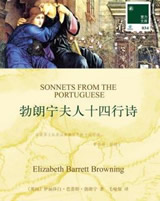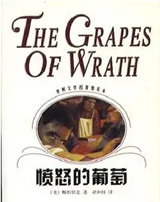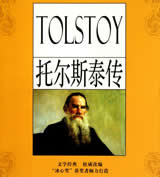第二十七章 为了每天的面包
暴风雪一直持续到第三天夜里,阿曼乐在一片寂静中醒来。原来暴风雪已经停止了。他在严寒中伸出手拿起挂在椅子上的背心,再取出表和一根火柴,看清楚时间快到凌晨三点了。
在这个漆黑的的凌晨,他仍然十分怀念当年把他从一床一上赶起来的情景。现在,他必须自己强迫自己从一温一暖的一毛一毡里爬起来,走进严寒的空气中。他必须自己去点灯、生火、打碎水桶里结的冰,他可以选择自己做早饭吃,当然,他也可以选择饿肚子。凌晨三点钟,是他唯一不喜欢自一由与独立的时候。
不过,一旦硬着头皮爬下一床一穿上衣服,他对清晨的喜一爱一就远远胜过一天中的其他时候。这时候的空气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新。东方的天空中还 挂着寥寥几颗晨星。气一温一是摄氏零下十度,风平稳地吹着。看来今天天气不错。
当他驾着拖着干草的雪橇驶过大街的时候,太一陽一还 没升起来,但晨星已经融入一道飞扬的光芒中。英格斯 家的房子黑黢黢地耸立在白雪覆盖的东边大草原边缘上。再过去就是第二街,远处有两座马厩,旁边堆着干草,看上去十分渺小。从马厩过去就是凯普·格兰的小房子,厨房里亮着豆大的灯光。凯普驾着他那匹鹿皮斑纹的Yan马拖着雪橇迎了上来。
他向阿曼乐招了招手,阿曼乐也举起手臂用力挥了挥,套在厚重的羊一毛一衣袖里的双臂显得十分僵硬。他们的脸都裹在了围巾里,两人都用不着再说什么。三天前,也就是在这场暴风雪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周密地计划好了这一切。阿曼乐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凯普让花斑马掉过头走上大街,紧紧地跟在阿曼乐后面。
到了这条短短的街道的尽头,阿曼乐转向了东南方,准备穿越大沼泽最狭窄的部分。太一陽一冉冉升起,天空中泛起一片淡淡的清冷的蓝色,整个大地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在一陽一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粉一红色的光芒,还 隐隐约约呈现出蓝色的一陰一影。马呼出的热气瞬间就在头顶上化成一一团一团一白雾。
四周安静极了,唯一能听到的是王子的四蹄踏在硬雪上的嘎吱嘎吱声和雪橇滑行杆摩一擦雪地的沙沙声。在波一浪一起伏般的雪地上既看不见的足迹,也看不见乌儿的爪痕。雪地上看不见道路的痕迹,也没有生物存在的任何迹象。冰冻的每个转弯处景致都各不相同,给人的感觉极其陌生。一阵风吹来,把地面上的积雪吹皱了,形成了微微起伏的雪一浪一,每一道雪一浪一都染上一道淡淡的蓝晕。在光滑而坚一硬的雪堆表面,风刮起了一一团一团一雪雾。
在这片雪海里毫无道路可寻,每一道一陰一影都在随风微微移动。风刮起来的雪烟使得眼前一一团一模糊,根本无法寻找地面的标记。阿曼乐极力想在变幻莫测的雪地里判断方向和推测距离,他想:“我们只好凭猜测或是碰碰运气去确定方向了!”
他猜想他们已经到达埋在雪堆下的大沼泽狭窄地带,也就是他运干草要经过的那个地方。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雪橇下面的雪层应该被压得十分紧密,那么在五分钟或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他就可以安全地登上高地。他向身后瞟了一眼,只见凯普已经放慢了花斑马的脚步,小心地保持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王子突然陷进雪堆里了。
“吁——,稳住!”阿曼乐的喊叫一声穿过围巾响起来,他的声音十分镇定,很具有安一抚的意味。在雪橇前方,只看见这匹喷着鼻息的马头,从草丛的空洞里伸出来。雪橇还 在不停地往前滑,雪橇上无法安装刹车器,不过幸好它及时停了下来。
“吁——王子,现在稳住,”阿曼乐说,“稳住,一定要稳住。”他紧紧地收住了马缰。王子深深地陷在深雪堆里,一温一驯地站着一动不动。
阿曼乐跳橇,取下了雪橇前面系在滑行杆链条上的横木。凯普驾着雪橇绕到他的身边停下来。阿曼乐走到王子头部的地方,步履艰难地走进那个雪洞的乱草丛里,然后抓住马勒下的缰绳。“稳住,老伙计,稳住,一定要稳住。”他一温一柔地安慰着它。因为他踉踉跄跄的走路姿势又让王子害怕起来。
接着,他使劲把脚底下的雪踩紧,让王子相信雪已经紧得可以踩上去了。他拉住王子的马勒,叫它往前走,直到它用力一跃跳出雪洞,然后阿曼乐拉着它很快爬了出来,重新走到坚一硬的雪地上。他牵着它走到凯普的雪橇边,把缰绳一交一给了凯普。
凯普的眼睛闪闪发光,蒙在围巾里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他惊喜地说道:“原来你是这么做的啊!”
“这没什么。”阿曼乐说。
“真是个出门的好日子!”凯普说。
“没错,是一个美妙的清晨。”阿曼乐赞同道。
阿曼乐走过去,把他的空雪橇往旁边拉,拉到他和王子弄出来的大雪洞后面。他很喜欢凯普。凯普总是乐呵呵的,无忧无虑,不过当他受到欺负和人家打起架来,他却十分凶猛。他一旦发起脾气来,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缝,看上去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谁也不敢去招惹他。阿曼乐曾亲眼看见他把最粗野的铁路工人吓得屁滚尿流的场景。
阿曼乐从他的雪橇上取下一卷绳索,把一端绑在雪橇的链条上,另一端系到王子身上的横木上。在王子的帮助下,他把雪橇从洞一口拖开,然后再把雪橇套到王子身上,卷起绳索,继续往前行驶。
阿曼乐领头朝太一陽一升起的地方走去,直到他确信他已经越过了了大沼泽区。然后他转向南方,朝双子湖——亨利湖和汤普生湖驶去。
现在,无边无际的雪地上只映射一出一片淡蓝色,处处都闪烁着小小的亮光。扎眼的亮光刺痛了阿曼乐的眼睛,他只好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每呼吸一次,他的围巾就鼓一胀起来,接着又被他的鼻子和嘴巴吸了回去。
他的手已经冻得麻木了,根本感觉不到马缰,他只好双手轮换着紧一握着缰绳,空出一只手来捶打胸脯,让浑身的血液流动,以保持身一体一温一暖。
他的双脚变得麻木的时候,他就走下雪橇,在雪橇旁边飞跑。在急速跳动的心脏的压力作用下,热气传送到脚底,直到双脚像火烧一般感到又痛又麻时,他才跳上雪橇。
“靠运动来暖身一子是最好不过的啦!”他回过头朝凯普大叫。
“我也来跟你一起暖一暖!”凯普回应道,也跳下雪橇,跟在阿曼乐旁边跑起来。
他们就这样跑上一会儿,然后再跳上雪橇,击打着胸膛,然后又跑,这时候马儿也轻快地奔跑起来。“喂,我们这样要跑多久啊?”有一次凯普开玩笑地大叫起来。“一直跑到我们找到小麦,或者跑到地狱里去溜冰!”阿曼乐回答。
“你现在就在地狱上溜冰啊!”凯普幽默地说。
他们继续往前跑。太一陽一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倾泻下来的一陽一光似乎比风还 要冷。天空中没有一丝云,不过寒气却越来越重。
走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沼泽地,王子又陷进了雪堆里。凯普急忙赶上来,停下雪橇。阿曼乐把王子从雪橇上卸下来,牵着它来到坚一硬的雪地上,然后把雪橇绕开雪洞拖开,重新把马套一上。
“你看前面有没有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他问凯普。
“没有!不过,我的眼睛靠不住。”凯普回答说。强烈的一陽一光使他们无论看哪儿都是一些黑点。
他们重新把围巾围好,把结了冰的地方从磨伤的脸上挪开。他们朝四周望去,一直看到遥远的地平线,可是除了闪亮的白雪和强劲的冷风,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到目前为止还 算幸运,”阿曼乐说,“只陷进去了两次。”
他站在雪橇上,开始向前跑,突然他听到凯普叫了一声。回头一看,花斑马跟在王子后面,在转弯的地方陷进去了。
凯普把马牵出来,拖着雪橇绕开那个洞,再重新套一上马。
“用运动取暖最好了!”他提醒阿曼乐。
在下一个低矮的高地上,他们看见了那棵孤零零的白杨树,它光秃秃的,看上去十分憔悴。两个湖之间的矮树丛都被积雪覆盖了,唯有这一棵光秃秃的白杨树傲一然一挺一立在苍茫大地上。
阿曼乐一看见这棵树就赶紧转向西方,远离双子湖周围的沼泽区。在高地的草丛上,积雪挺坚实的。
那棵孤零零的白杨树是最后一个路标。它很快就消失在无迹可循的雪一浪一中。没有路,没有任何标记,没有人知道那个种小麦的拓荒者在哪儿,甚至没有人敢确定他是不是还 在那个地区,他有可能已经搬迁到其他地方过冬了,有可能那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也许只是一个谣传,由一个人无意间信口开河告诉另一个人,说这个地区的某个地方某个人种了小麦。仅此而已。
在漫无边际的冰雪世界里,每一处雪一浪一看上去都没什么两样。风刮起雪堆顶上的积雪,掀起阵阵雪雾,草原低矮的隆一起处一个接一个,看上去也是一模一样,太一陽一缓缓地爬上高空,寒气越来越重。
除了马蹄声和雪橇滑板不着痕迹地滑过雪面发出的沙沙声,还 有风吹过雪橇发出的轻微声响,再也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啦。
阿曼乐时不时地回过头看看,凯普总是对他摇摇头。他们谁也没有在这寒冷的天空中看见一缕轻烟。小小的冰冷的太一陽一似乎一动不动地悬挂在空中,不过实际上它正在缓慢地往上升。地面上的影子越来越短,雪一浪一和草原上凸起的地带似乎也变平了。白色的荒野看上去平坦开阔,一陰一森森的,空荡荡的。
“我们还 要走多远啊?”凯普叫道。
“直到我们找到小麦为止!”阿曼乐回头大声说。不过他也拿不准在这一望无垠的雪原上是不是真有小麦。太一陽一已经升到了最高处,这一天已经过去了一半时间。西北方的天空还 看不出有暴风雪到来的迹象,两场暴风雪之间居然有超过一天的晴天,这真是罕见了。
阿曼乐明白他们该掉头返回镇上去了。他已经浑身冻僵了,踉踉跄跄地跳下雪橇,在旁边奔跑起来。他并不情愿回到那个正在饱受饥饿折磨的小镇,告诉大家他双手空空地回来了。
“你估计我们走了多远啦?”凯普问道。
“大约有三十公里吧,”阿曼乐推测道,“你是不是想回去了?”
“除非倒下,否则绝不放弃!”凯普神情坚定地说。
他们朝四周看了看,发现他们正处在一块高地上。要不是因为白雪的反射光使得靠近地面的空气雾蒙蒙的,他们也许可以看到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可是,在太一陽一的直射下,一些看似平坦的草原隆一起处,却把西北方的一些小镇给挡住了。西北方的天空依然晴朗无云。
他们使劲跺了跺脚,用手拍打着胸脯,从西到东仔细搜索着这一片白茫茫的草原,极力向南方眺望。可是四处仍然不见一缕轻烟。
“我们朝哪个方向走?”凯普问。
“哪个方向都一样。”阿曼乐回答说。他们呼出来的气已经使围巾结满了冰,冰把他们的脸都磨伤了,他们在羊一毛一围巾上几乎找不出一块干爽的地方,用来捂住疼痛的皮肤。“你的脚怎么了?”他问凯普。
“没事,”凯普回答说,“我想应该没什么。我要继续往前跑。”
“我也要跑跑。”阿曼乐说,“如果脚不能很快暖和起来,我们最好停下来用雪擦一擦。我们先沿着这块高地往西跑上一段看看,如果没有找到什么,我们就绕回来往南跑。”
“我也这么想。”凯普极力赞成。两匹优秀的小马十分乐意地小跑起来,他们也跟在雪橇旁边跑着。
高地比他们预料的要狭小一些。雪坡向下倾斜,延伸成了一片平坦的洼地。这片洼地被高地遮住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沼泽。阿曼乐收紧缰绳让王子放慢脚步,他站在雪橇上仔细观察地形。洼地一直向西延伸,他知道如果不转身沿着高地走回去的话,就没办法绕过这片洼地。突然,在越过沼泽的地方,他看见被风卷起来的积雪中有个黄色的东西。他让王子停下来,同时叫道:“嗨,凯普!前面好像有一股烟啊?”
凯普也正朝那个方向望去。“看来好像是从雪堤里冒出来的!”他叫道。
阿曼乐驾着雪橇从斜坡上滑一下去。几分钟后,他回来嚷道:“是烟!没错,那儿有幢房子!”
他们必须穿过这片沼泽才能到达那幢房子。凯普想赶上来跟在阿曼乐旁边一道向前行驶。在匆忙中,花斑马一下子陷进雪洞了。这是他们所遇到的最深的一个雪洞,雪洞四周的雪层都松碎了,下面空空的,好像深不见底。等到他们把花斑马弄到坚固的雪地上,再小心翼翼地朝前行驶,远方的天际已经爬上了一陰一影。
这股轻烟的确是从一道长雪堤中升起来的。雪地上连一个标记也没有,等他们从南边绕了一个圈子走到雪堤时,这才发现雪堤里有一道门,门前的积雪已经被清除了。他们把雪橇停下来,大声叫喊起来。
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男子,他站在那儿,显得十分惊讶。他的头发长长的,没有修刮的一胡一髭几乎遮住了半张脸。
“嗨!嗨!”他叫道,“快进来!快进来!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啊?准备到哪儿去?进来吧!你们会待多久呢?赶快进屋来吧!”他兴奋极了,只顾着自己说话,也不等人家回答。
“我们必须先把马安顿下来!”阿曼乐说。
男子进屋抓起一件大衣穿上,走出来说道:“请过来吧,走这边,跟我来?你们两个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刚从镇上赶来。”凯普回答说。这个人带着他们走到另一道雪堤里的一扇门前。他们一边卸马一边把名字告诉了他,那个人说他的名字叫安德森。他们把马牵进一温一暖的草泥马厩里。马厩建在雪堤下面,十分舒适。
马厩的尽头用柱子和一道粗糙的门隔出了一个夹墙,从一道裂缝里漏出些小麦粒。阿曼乐和凯普看了看那儿,两人不由得相视一笑。
他们在门边的水井里打了些水让王子和花斑马喝好水,给它们喂了些燕麦,然后把它们拴在安德森那对黑马旁边装满干草的马槽上。接着,他们跟随安德森走到雪堤下面的屋子里。
这间屋子的天花板是用木条搭盖的,上面铺着厚厚的干草,在雪的重压下,天花板已经凹垂下来。墙是草泥皮涂抹的。安德森将门打开一条缝,让光线透进来。
“自从上回那场暴风雪过后,我还 没来得及把堆在窗户上的雪清除掉呢。”他说,“雪堆积在西北方那个隆一起的高地上,挡住了我的房子,所以我这儿很暖和,也不需要多少燃料。总之,草泥屋是最暖和的。”
屋子里的确十分暖和,火炉上烧着开水,氤氲的水蒸气在房屋里缭绕。安德森的晚餐已经摆放在靠墙边的粗木桌上。他叫他们把椅子拉过来,坐下来和他一起吃饭。自从十月到镇上买回冬天的生活物资后,他就再也没见过一个人。
阿曼乐和凯普陪他坐下来,津津有味地吃着烤豆、酸面饼干和干苹果酱。热气腾腾的食物和咖啡让化们浑身都暖和起来,他们脚上的冰雪也渐渐融化,感觉像火烫一般刺痛,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脚还 没冻伤。阿曼乐向安德森先生提到他和凯普赶来是想买一些小麦。
“我不卖!”安德森直截了当地说,“我种出来的小麦都是留下来做种子用的。你们在这时候来买小麦做什么呢?”他好奇地问道。
他们只好如实告诉他,火车停开了,镇上的人都在挨饿。
“从前开始,镇上的妇女和孩子们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阿曼乐告诉他,“他们必须吃些东西,否则等不到就要饿死了。”
“这与我无关!”安德森先生说,“谁也没有责任去管那些毫无先见之明、不能照顾自己的人。”
“没有人认为你该对此负责,”阿曼乐反驳道,“也没有人要求你送给他们任何东西。我们愿意付你一袋八角钱的高价,也省了你运去镇上卖的麻烦。”
“我没有小麦可卖!”安德森说。阿曼乐知道他态度坚决,确实不愿意卖。
这时凯普插话了,他被雪风刮得开裂的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们就开门见山照实说吧,安德森先生,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镇上的人不得不从你这儿弄一些小麦回去,不然就会被活活饿死。当然!我们必须付钱给你。你要多少钱才卖昵?”
“我不想占你们的便宜!”安德森说,“我不想卖。那是我的小麦种子,我明年的收成全靠它。如果要卖的话,我去年早就卖了!”
阿曼乐迅速作出决定。“我们一袋给你一元钱,”他说,“比市场价高出了一角八分。别忘了,还 是我们亲自过来搬运的。”
“我不卖我的种子,”安德森依然不依不饶,“明年我得有收成才行。”
阿曼乐沉思着说:“种子还 可以再买啊。这儿有很多人都要买种子。你把高过市场价一角八分的净利白白扔掉啦,安德森先生。”
“我怎么知道他们能及时把种子运来给我们播种?”安德森质问。
凯普十分机智地问他:“唔,这么说,你又怎么知道你会有收成呢?说不定你这次拒绝了现金一交一易,把小麦播种下去,到时候遇到一场冰雹或者蝗虫灾害,也可能颗粒无收啊。”
“这倒是实话。”安德森说。
“你现在能够把握住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放在你口袋里的现金。”阿曼乐说。
安德森慢慢摇了摇头。“不,我不卖!去年夏天我拼命翻了四十亩土地,我得留够种子好播种啊。”
阿曼乐和凯普互相看了看,阿曼乐拿出他的钱包。“我们给你一袋一元两角五分的高价,咱们一手一交一钱一手一交一货!”他取出一沓钞票放在桌上。
安德森开始犹豫起来,接着他的视线从钱上移开了。
“一鸟在手,胜过二乌在林啊。”凯普说。
安德森忍不住又看了看钞票,接着他身一子往后一靠,认真考虑起来。他搔了搔头。“嗯,”他最后说,“我还 可以另外种些燕麦。”
阿曼乐和凯普都没吭声。他们明白他正在作艰难的选择。如果他现在决定不卖了,他就再也不会改变主意了。最后,他终于作出决定:“我想就让你们以那个价钱买六十袋小麦吧。”
阿曼乐和凯普迅速从桌边站了起来。
“来吧,我们把它装上雪橇!”凯普说,“我们还 要赶很远的路才能回到家呢。”
安德森先生劝他们留下来过了夜再走,可是阿曼乐同意凯普的决定。“谢谢啦,不过我们得立马动身。”他匆匆说,“最近暴风雪过后往往只能晴上一天,下一场暴风雪就会接踵而至。眼下已经过了中午了!我们马上动身回去已经有些晚了。”
“小麦是没有装袋的。”安德森解释说。阿曼乐说,“我们带了袋子来。”
他们急忙赶往马厩。安德森帮着他们把小麦从谷箱桶里铲出来,倒进一只能装六十公斤的大袋子里,再把袋子搬上雪橇。趁套马的工夫,他们向安德森先生打听怎么穿过沼泽才最快捷最安全,可是安德森这一年冬天还 从未穿过沼泽出去,况且雪地上没有任何标记,他实在是无法说清楚去年夏天他是从哪儿驾车通过沼泽的。
“你们最好还 是留在这儿过夜吧。”他再一次劝留他们。可是他们跟他匆匆告别后就动身赶往回家的路了。
他们驾着雪橇从雪堤下的屋子里走进凛冽的寒风中,还 没有越过那片平坦的洼地,王子就一个跟头栽进雪洞里。凯普的花斑马拐了个弯,绕过了这个危险的地方。突然花斑马脚下的雪“哗”的一声塌了下去,它惊叫一声,一头栽了下去。
马撕心裂肺地叫着。有好一阵子,阿曼乐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王子要稳住别动。接着他看见凯普紧一抓着吓得发一抖的花斑马的马勒,跟马一起掉进了雪洞里。花斑马使劲挣扎着,差点儿把凯普的雪橇拖进了雪洞。雪橇在洞一口的一侧倾斜着,一些小麦袋子已经滚落在了雪地上。
“没事吧?”阿曼乐问道。这时候花斑马的情绪似乎平静下来了。
“没事!”凯普爽一快地回答说。接着他们忙了一阵子,各自在被踏破了的雪洞里和像铁丝网般纠缠在一起的草丛中把马卸下来,然后在雪洞里使出浑身的劲又跺又踩,好给马弄出一块结实的地方来。他们从雪洞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沾满了雪,连骨子里都冷透了。
他们把两匹马都拴到阿曼乐的雪橇上,然后把凯普雪橇上的小麦卸下来,把雪橇从洞里拖出来,再将六十公斤重的小麦袋子一袋一袋放在雪橇上,最后再套一上马。他们冻僵的手艰难地扣紧硬一邦一邦的冰冷的皮带。阿曼乐再次小心翼翼地驾着雪橇穿越这片危险的沼泽区。
王子不小心又掉进雪洞里了,不过幸运的是花斑马没有掉下去。在凯普的帮助下,没过多久就把王子从雪洞里弄出来了。从这以后他们没有再遇到麻烦,顺利地爬上了高地。
阿曼乐在高地上停下来,对凯普大声说:“你认为我们最好是不是按原路返回?”
“不行!”凯普回答说,“最好是直接朝镇上跑,我们不能再耽误了。”马蹄和雪橇在坚一硬的雪层表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唯一的标记就是他们曾掉进去的雪洞,这些雪洞都在回程路东边的沼泽里。
阿曼乐朝西北方前进,越过白雪覆盖的广袤草原。他唯一的向导就是自己的影子。草原上的隆一起处看上去都一模一样,积雪覆盖的沼泽也只有大小之分。如果从低地驶过,就要冒着陷进雪洞和耽误时间的危险;如果沿着高地隆一起的地方走,就要多走几公里路。马匹已经有些疲倦了。它们总是害怕陷进隐藏在雪地里的空洞,这种恐惧更加重了它们的疲惫。
它们还 是常常陷进薄薄的硬雪层下面。凯普和阿曼乐不得不把雪橇从它们身上卸下来,然后把它们弄出雪洞,再重新套一上雪橇。
他们一刻也不停歇地在刺骨的寒风中艰难地跋涉。马匹拖着沉重的小麦,已经累得跑不动了。因为马跑得不够快,阿曼乐和凯普也就不能跟在雪橇旁跑,他们只有一边走一边使劲跺着脚,这样才能避免脚被冻僵。他们还 得用手臂拍打胸脯。
他们越来越冷。阿曼乐跺脚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知觉,手僵硬得根本无法把手指伸开。他把马缰套在肩头,让两只手自一由活动,他每跑一步,就双手一交一叉捶打着胸部好让血液流动起来。
“嗨,阿曼乐!”凯普大声嚷道,“我们是不是在往偏北的方向走?”
“我怎么知道啊?”阿曼乐大声地说。
他们继续步履艰难地跋涉着。王子又掉进雪洞里去了,无一精一打采地站在那儿。阿曼乐把它从雪橇上卸下来,踩紧下面的雪,然后把它牵出来,再把它套一上雪橇。他们爬到一处高地上,绕过了一处沼泽地,再往下走,穿过另一片沼泽地。王子再次陷进雪洞里。
“让我来带一会儿路吧!”凯普说,“这样你和王子都可以少吃一点儿苦头。”
“好吧,”阿曼乐说,“我们轮流带路。”
就这样,这匹马掉下去了,另一匹马就领头跑,另一匹马掉进去了,再换这匹马来领头。太一陽一已经落得很低了,西北方雾气也越来越浓。
“到了前面那个高地,我们就可以看见那棵孤零零的白杨树了。”阿曼乐对凯普说。
“是的,我也这么想。”过了一会儿,凯普才回答说。
可是等他们上了高地,却什么也看不到,眼前依然是一望无边的雪一浪一和西北方低垂的浓雾。阿曼乐和凯普望着前方,然后对他们的马说了几句贴心话,又继续前行,他们的雪橇靠得很近。
等到他们看见东北方那棵白杨树光秃秃的树梢时,落日已经在地平线留下一抹残红。在西北方,暴风雪的云层已经清晰可见,正低低地聚集在地平线上。
“它似乎已经在准备发动进攻了,”阿曼乐说,“我早就注意到了。”
“我也是,”凯普说,“不过我们最好暂时把寒冷抛到一边,驾着雪橇走一会儿吧!”
“好的,”阿曼乐说,“我也正好想休息几分钟。”
他们除了催促疲惫的马跑快一点儿外,不再说什么话。凯普带头笔直地跨过高地,穿越过低洼地,迎面遇上了呼啸的狂风。他们低着头顶着风继续前行,直到花斑马再次陷进雪洞里。
阿曼乐紧跟其后,眼看着也要冲向那个隐藏的雪洞。他急忙往旁边一闪,可是王子已经紧一贴着花斑马掉下去了。两匹马中间的雪层全都塌陷下去,阿曼乐的雪橇一倾斜,小麦连雪橇一同掉进碎雪和枯草丛中。
凯普帮阿曼乐把雪橇拖出来,再把小麦从雪堆里挖出来搬上雪橇,这时候黑夜已经悄悄来临。雪地发出了苍白的淡淡的光晕,风已经停歇了,在黑沉沉的寂静中,空气仿佛也凝固了。他们仰望着天空,发现南方和西方的天空中群星闪耀,而北方和西方的天空却低垂着,漆黑一片。不久,黑夜笼罩了大地,把天上的全都吞没了。
“我们也许被困住了。”凯普说。
“应该快到家了。”阿曼乐回答道。他一边跟王子说着话,一边领头朝前跑着。凯普跟在后面,他和雪橇形成一个巨大的一陰一影,在昏暗的白雪上缓慢地向前移动。
他们前方的天空中涌来一片黑云,星星转眼间全都消失了。
阿曼乐和凯普用镇定自若的语气和疲惫不堪的马儿说着话,催促着它们快点儿往前跑,前方还 要穿越沼泽的狭窄地带。现在他们已经看不清地上哪儿是隆一起的哪儿是低凹处,只能凭着灰白的积雪和微弱的星光,依稀分辨出眼前的一小段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