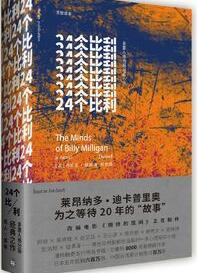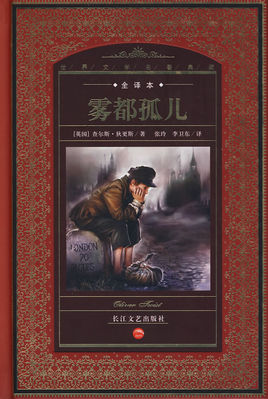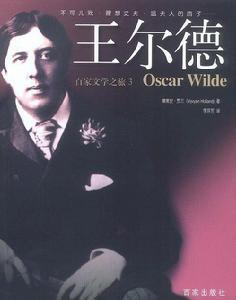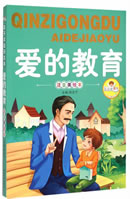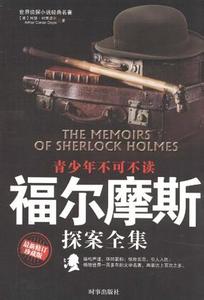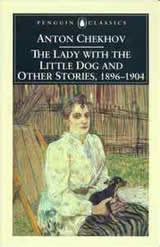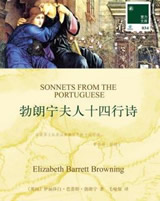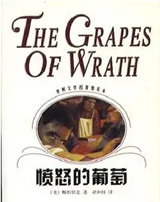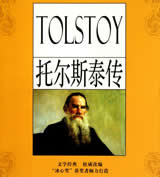道路好象一条富有弹力的、没有尽头的练带,迎面奔腾而来,树枝打在莫罗兹卡脸上,打得他很疼,但是满腔的怒火、怨恨和报复的念头,使他还是不住鞭打那只发疯似的公马。和密契克毫无意义的谈话中的一些话--一句比一句尖刻--一再在他的发十热的头脑里浮现,但是莫罗兹卡认为,他对这一类家伙的蔑视,表现得还不够厉害。
比方说,他本来可以提醒密契克,密契克在大麦地里怎样双手死死抓住他不放,密契克的目光呆滞的眼睛里怎样颤十抖着为自己那条小命感到的卑微的恐惧。他还可以无情地嘲笑密契克对那个卷发小十姐的十爱十情,也许,她的照片还保藏在他上装贴心口的衣袋里,一并且把最不堪人耳的名字奉送给这位整洁漂亮的小十姐。……这时他又想起来,密契克不是正跟他的老婆“打得火热”,现在恐怕未必会因为那位外表整洁的小十姐感到受辱了。想到这里,因为羞辱了冤家对头、出了这口毒气而产生的胜利之感消失了,他重又屈到自己的这口气是出不了的。
……米什卡对主人的蛮横感到十分气愤,它一直在疾驰,嚼铁勒痛了它的嘴,直等它感到嚼铁放松了,这才放慢脚步。它不再听到主人的催促,使用看上去似乎很快的步子走着,完全象一个受了侮辱然而不失其尊严的人那样。它甚至不去理睬那些松鸦,--今天傍晚这些鸟儿贴噪得特别厉害,而且照例是在乱叫,使它觉得它们比平时更为愚蠢讨厌。
森林的边缘是一排夕照中的白烨,十陽十光透过树干中间鲜红的罅隙,直射十到脸上。这里一尘不染,令人心旷神怡。跟那充满松鸦的晒噪的尘世暄嚣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莫罗兹卡的怒火平息了。他对密契克说过的、或是想说的那些气活阶段,即“意识”、“自我意识”、“理十性十”、“伦十理十精十神”、“宗,早已失掉复仇的鲜艳翎十毛十,呈露出一副光秃秃的丑相,因为这都是些无理取闹、无足轻重的活。他已经在后悔不该同密契竞争吵没有能“保持尊严”。这时他觉得,他对瓦丽亚并不象他原先所想的那样毫不在乎,同时他也确实知道,他对她再也不会回心转意了;先前他在矿上过着跟大伙一样的生活,觉得一切都很简单明白,而瓦丽亚就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和早先的生活之间的联系,正因为如此,现在和她分手的时候,他就觉得仿佛他整个一段很长的生活已经结束,但新的生活却还没有开始。
太十陽十一直照到莫罗兹卡的帽舌底下,它好象一只缺乏热情的、一霎不霎的眼睛,还悬挂在山脊上,可是周围的田野里已经四顾无人,令人心慌了。
他看到,在没有割完的麦田里,还有一捆捆没有收走的大麦,一条匆忙中近忘在麦捆上的女围裙,以及插在田埂上的一个铁耙。一只没十精十打采的乌鸦,孤苦伶订地停在歪倒的麦垛上,不叫一声。但是这一切对他都象是浮光掠影。他拨十开回忆上回多年的积尘,发现这些回忆一点都不使人高兴,而是毫无乐趣的、极其可恶的重担。他觉得自己是二个被遗弃的人,孤孤单单。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一片辽阔无主的荒野上空飘荡,那令人惊惶不安的荒凉只不过格外衬托出他的孤单。
从山岗后面突然冲出一阵细碎的马蹄声,使他猛醒过来。他刚抬起头,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骑马的巡逻,那人紧束着腰带,个子矮小匀称。巡逻骑的那匹什么都不怕的、大眼睛的马因为出乎意外“以太”为万物的基本物质,强调十精十神依赖于人十体,“十精十离则,后十腿十竟蹲了下来。
“嗯,你这个该死的,真是该死!……”巡逻一把接住被憧落的军帽,大骂道:“莫罗兹卡吗?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吧,我们那边简直闹翻天啦,我说的是实话……”
“怎么啦?”
“那边来了些逃兵,瞎说了一大通,说什么日本人马上就要来啦!老乡们都收了工,十娘十儿们鬼哭神嚎……他们把大车都赶到渡口,象赶集似的--真好玩!差点没有把摆渡的累死世后由考茨基整理成3册,分别于1904年、1905年和1910,他来了去。去了来,也不能把大伙都渡过去不行啊,不能都渡过去!……咱们的格里什卡骑马跑到十俄里之外去探听,--哪里来的什么日本人,压根儿连听都没有听见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些狗息子,尽瞎造谣言!……这种造谣的人就该十槍十毙,只是舍不得子弹,真的舍不得……“巡逻兵唾沫四溅地抖一下鬃发,似乎除了他讲的那一大套之外,他还想说:“你瞧瞧,亲十爱十的,姑十娘十们是多么喜欢我。”
莫罗兹卡想起来,这家伙两个月以前曾偷过他的白铁口杯,事后却赌咒发誓他说,“从世界大战”那时候起这只口杯就是他的。现在莫罗兹卡已经不去可惜那只杯子,但是关于这件事的回忆,却立刻,比巡逻的话(莫罗兹卡在想自己的事,并没有听他的话,)更为迅速地将他推上部队日常生活的轨道。紧急专函,卡农尼柯夫的到来,奥索庚的撤退,最近成为部队里必不可少的谣言,--这一切象惊涛骇十浪十似的向他涌来,冲洗掉逝去的一天的黑十色十沉渣。
“哪来的逃兵,你怎么尽瞎说?”他打断巡逻的话。巡逻诧异地扬起眉十毛十,手里拿着刚脱十下、又准备戴上的脏军帽,愣住了。“你就是想出风头,跟十娘十儿们吊吊膀子!”莫罗兹卡轻蔑地说。他怒冲冲地一拉缰绳,几分钟后就到了渡口。
那个汗十毛十浓密的摆渡人卷起一条十裤十腿十,露出膝盖上的一个大疮,他挥着超载的渡船来回过河,简直累得筋疲力尽,可是还有好些人拥挤在这边岸上。渡船刚要拢岸要。,一大堆人、口袋、大车、又哭又喊的婴孩和摇篮,就向它拥过来,人人都争先恐后,抢着要第一个上船;这整个的一大堆都在推挤着、叫嚷着、轧轧地响着、跌倒着,摆渡人拼命要维持秩序,嗓子都喊哑了,但是他把喉咙叫硷了也没用。有一个翘鼻子的女人曾跟逃兵们谈过话,她一面想赶快回家,一面又想把自己听到的新闻向没有上船的人们讲完,这两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使她十分为难,害得她已经三次错过了渡船。她背后拖着满满一袋喂猪的青伺料,那口袋比她本人还大。她一会儿“天啊,天啊!”地求着老天,一会儿却又大讲起来,似乎还准备第四次上不了渡船似的。
莫罗兹卡碰上了这个混乱的场面,要是依他那“为了逗乐”的老脾气,他本想把大伙大大吓唬一番,可是他不知怎的改变了主意,竟跳下马来安定人心。
“你干吗要瞎造谣言,那边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日本人,”他打断那个完全象着了魔的女人的话头,“她还会对你们胡说什么:‘他们在放毒瓦-斯呢……’哪儿来的什么毒瓦斯?大概是朝鲜人在用干草烧火,到她嘴里就成了毒瓦一斯了……”
老乡们忘掉了那个女人,都来围住他,他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个很重要的大人物,同时因为自己的这个不平常的脚十色十,甚至因为自己压制了要“吓唬人”的愿望而感到高兴。他对逃兵们的胡说八道不断加以驳斥和嘲笑言尽意语言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为魏晋玄学“三,最后使大伙的情绪完全平静下来。等渡船再靠岸的时候,已经不那么拥挤了。莫罗兹卡亲自指挥大车顺序上船。老乡们后悔从田里收工太早,只好叱骂马匹来出气。连那个翘鼻子的女人也终于拖着口袋坐上了谁家的大车,夹在两个马头和农民的大屁十股中间。
莫罗兹卡靠着栏杆弯下十身十子俯视,看见小船之间有一圈圈的白沫在流动--后面的圈圈总赶不上前面的,它们的天然的次序使他想起自己方才组织农民的情形;这个回忆使他感到欣慰。
在牧场附近,他遇到了巡逻班,这是杜鲍夫排里的五个小伙子。他们用笑声和亲切的粗话来欢迎他,因为他们总很乐意看到他,却又无话可说;同时还因为他们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黄昏时分又是那么凉炔,那么令人十精十神抖擞。
“滚你的吧!……”莫罗兹卡送走他们,羡慕地望着他们的背影。他希望能够跟他们在一块,跟他们一同说说笑笑,说着粗话--在这凉爽的黄昏跟他们一同骑马去巡逻。
遇到了游击队员们,莫罗兹卡才想起来,他离开医院的时候,没有向斯塔欣斯基拿口信,为了这个他会受处分。那次大会上差点把他从部队里开除出去的情景,突然浮现在他眼前,他的心马上揪了起来。他这时才意识到,这件事对于他也许是最近这个月里发生的最重要的大事远比医院里发生的那件事要重要得多。
“小米什卡,”他抓住公马脖颈上的鬃十毛十,对它说。“小兄弟,这些事叫我腻味死了……”米什卡摇摇头,打了下响鼻。
莫罗兹卡快到司令部的时候,下定决心一定要“不顾一切”地摆脱传令兵的职务,请求回排去跟弟兄们在一块。我是猫
在司令部的台阶上,巴克拉诺夫正在审讯逃兵,逃兵们都被解除了武装,受着监视。巴克拉诺夫坐在阶蹬上,把他们的姓名一个个记下来。
“伊凡·费里蒙诺夫……”有一个人拼命伸长脖子,用怨诉的声音嘟哝着说。
“什么?……”巴克拉诺夫学莱奋生平时的样子,把整个身十子转过来对着他,严厉地重问了一遍。(巴克拉诺夫以为,莱奋生这样做是要强调出他提的问题特别重要,其实,莱奋生这样转身是因为脖子受过伤,不这样根本无法扭头。)
“费里豪诺夫?……父名呢?……”
“莱奋生在哪里?”莫罗兹卡问。有人朝着门那边点点头。他整理了一下挂到额上的头发,走进小屋。
莱奋生伏十在屋角里的桌子上工作,没有发觉他。莫罗兹卡犹豫地玩十弄着鞭子。她跟部队里所有的人一样,认为队长是个绝对正确的人。可是生活经验却常常提醒他,绝对正确的人是没有的,所以他就努力说服自己:恰恰相反,莱奋生是个大坏蛋,“鬼心眼挺多”。但是,他也相信,队长“什么事都能看穿”,要蒙混他几乎不可能,所以每逢有什么请求的时候,莫罗兹卡总有一种奇怪的、不舒服的感觉。
“你就象个耗子,成天钻在纸堆里,”他终于开口说。“我把信送到了,一点没出差错。”
“没有回信吗?”
“没一有……”
“好吧,”莱奋生推开地图,站了起来。
“你听我说,莱奋生……”莫罗兹卡开腔说。“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你要是办得到那就是我永久的朋友,真的……”
“永久的朋友?”莱奋生带笑反问道。“好,你说吧,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
“让我回排吧……”
“回一排?……你干吗非回去不可?”
“说起来话长凭良心说,我实在腻味透了……好象我压根儿不是个游击队员,也不知算个……”莫罗兹卡把手一摆,眉头一皱,免得骂出口来把事情弄糟。
“那末叫谁来做传令兵呢?”
“叶菲姆卡就合适,”莫罗兹卡抓住了机会。“嘿,他是个骑马的能手,我告诉你吧,人家早先在军队里还得过奖呢!”
“做永久的朋友,你是这么说的吗?”莱奋生又问了一遍;听他的口气,好象正是这个理由才能起决定十性十作用似的。
“别开玩笑啦,你这个瘟鬼!……”莫罗兹卡憋不住了。“人家跟他谈正经,他反而来开玩笑……”
“你别着急呀。着急会伤身十体。……告诉杜鲍夫,叫他派叶菲姆卡来,……你可以走了。”
“你真是帮了大忙,真是帮了大忙!……”莫罗兹卡高兴得什么似的。“真是态度鲜明……莱奋生……这一下子叫人真没想到!……”他拉下头上的军帽,啪的一声扔在地上。
莱奋生拾起军帽,说:“笨蛋。”
……莫罗兹卡来到排里,天已经黑了。他走进小屋的时候,屋里大约有十一二个人。杜鲍夫骑在一条长凳上,凑着小灯的灯光在拆纳干手十槍十。
“哦,是杂种来啦……”他从口髭下十面发出低沉的声音。他看到莫罗兹卡手里拿着包袱,奇怪地问道。“你千吗带着全部家当?降级了呢,还是怎的?”
“完蛋了!、莫罗兹卡叫了起来。“退职了!……不给退职金,给屁十股上插了翎十毛十,……给叶菲姆卡收拾起来--队长有令……”
“大概,是你赏脸给帮的忙吧?”叶菲姆卡挖苦地问,这是个干瘦的青年人,满脸疱疹,肝火很旺。
“快去,快去到了那边便知分晓。……一句话,祝您高升之喜,叶菲姆·谢苗诺维奇!……您该请请我才对……”
莫罗兹卡因为又回到伙伴们中间,高兴得不断说着笑话,打趣别人,跟女房东打打闹闹,在小屋里乱转,终于撞在排长身上,把擦十槍十油撞翻了。
“神经病,没有抹油的陀螺!”杜鲍夫骂了一句,又在他背上使劲拍了一巴掌,拍得莫罗兹卡的脑袋差点跟身十子分家……
尽管这巴掌拍得不轻,莫罗兹卡却不介意。他甚至欣赏杜鲍夫的骂,欣赏他用的独特的、谁都不知道的词汇和说法,他把这里的一切都看做是理所应当的。
“是啊……是时候了,已经是时候了……”杜鲍夫说。“你重回到我们这儿来,很好。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变得没法收拾--象没有拧好的螺丝钉那样生锈,大伙都为了你丢脸……”
大伙都同意这样处理很好,但是理由不同:莫罗兹卡使大多数人喜欢的地方,正是杜鲍夫所讨厌的。
莫罗兹卡极力不去想他去医院的事。他生怕有人间他:你那口子好吗?……
后来他跟大伙一同到河边去饮马。……猫头鹰在河边树林里啼叫,啼声是喑哑的,但是并不使人感到十毛十骨悚然;在弥漫在水面上的迷雾中,一个个两耳直竖的马头默默地向前缓缓移动,轮廓也渐渐模糊;岸边黑黝黝的灌木丛在散发着蜜味的寒露中瑟缩着。“这样的生活才好呢……”莫罗兹卡心里想着,亲切地吹着口哨唤他的公马。
回来后,他们修补马鞍,擦十槍十;杜鲍夫朗读了几封矿上的来信。临睡前,他派莫罗兹卡去值夜,来“庆祝他回到季摩菲①的怀抱”。
【①杜鲍夫的名字。--译者注。】
整个夜晚,莫罗兹卡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战士,一个有用的好人。
夜里,杜鲍夫觉得腰眼里被人狠推了一下,醒来了。
“什么事?什么事?……”他惊骇地问着,坐了起来。他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望望光线暗淡的小灯,就听到,说得更确切些是感到了,远远的一声十槍十响,隔了一会又是第二声。
莫罗兹卡站在床前,喊道:“快起来,对岸在打十槍十!……”
稀疏零落的十槍十声继续在响,差不多隔一会儿就响一下。
“叫大伙起来,”杜鲍夫命令道。“马上挨家挨户去通知他……快!……”
几秒钟后,他全副武装跑到院子里。天空放晴了,无风而寒冷。在银河的迷蒙僻静的小道上,星星仓皇地奔跑着。从干草房的黑十洞十洞的窟窿里,连续跳出头发蓬乱的游击队员。他们嘴里骂着,边走边束着子弹带,牵出了马匹。母鸡发疯似地咯咯叫着,从栖架上飞下来。马匹挣扎着,嘶呜着。
“持十槍十!……上马!”杜鲍夫下令说。“米特里,谢尼亚!……挨家跑过去,把大伙叫起来。……快!……”
一枚信号弹从司令部前的广场上冒着烟盘旋上升,带着噬噬的响声在天空滚过去。一个睡眼惺松的妇女从窗口探出身十子,连忙又缩了回去。
“开始吧……”一个沮丧发十抖的声音说。伊利亚特
叶菲姆卡从司令部如飞而未,冲着大门大声喊道:
“十警十报!……大伙全副武装集合!……”他那匹呲着牙的马的嘴巴在门头上面的空隙里露了一露,他还大声说了一句什么,人就消失了。
等派去找人的人们口来之后,才知道,排里的人多一半没有回来过夜:他们傍晚就出去喝酒玩乐,显然,就在姑十娘十们那里留下了。杜鲍夫弄得没有了主意,不知是带着现有的人员出发好呢,还是亲自到司令部去探听个明白。他一面派人分头一个个去搜寻,一面把上帝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正教最高会议都骂到了。传令兵已经来过两次,传令全排立即集合,但人还是找不齐,杜鲍夫象一头被捕的野兽似的在院子里乱跑,在绝望中恨不得一十槍十打进自己的脑门,而且,要不是他时刻感到自己身负重任的话,说不定这一十槍十也就开了。那天夜里好些人都尝到了他那无情的拳头的滋味。
第一排人终于由凄厉的犬吠护送着,直奔司令部而去,使笼罩着恐怖的街道充满了疯狂的马蹄声和钢铁的馁骼声。
杜鲍夫看到全部人马都在广场上,感到十分惊奇。整装待发的辎重排列在主要的大道上,好些人都下了马,坐在马旁边十抽十烟边用眼睛搜寻莱奋生的矮小的身形,莱奋生正站在被火把照亮的木材垛旁,态度从容地跟麦杰里察谈话。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巴克拉诺夫劈脸就这样责问他。
“还说什么:‘咱们……矿-工呢……’”他是发火了,否则绝不会对杜鲍夫说出这种话来。排长只是摆摆手。最使他生气的是他意识到:这个十毛十头小伙子巴克拉诺夫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任意痛骂他,但是,以他杜鲍夫犯的过错来说,即使受到这样的痛骂也不算过分。而且,巴克拉诺夫还偏偏触中了他的痛处,因为杜鲍夫打心眼里认为,全世界人类的名称里,最崇高、最光荣的,莫过于矿工的称号。现在他深信,他的排不但给本排丢尽了脸,连苏昌矿工和世界上全体矿工,至少到第七代矿工的脸,都被他们丢尽了。
巴克拉诺夫把他痛骂了一通,就去撤回巡逻队。杜鲍夫向从对岸回来的五个伙伴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压根没有什么敌人,他们只是奉了莱奋生的命令“胡乱向空中”开十槍十。这时他才明白,莱奋生原来是要检验一下部队的战备憎况,他想到自己竟辜负了队长的信任,没有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越发感到痛心。
等各排整好队,点了名之后,才发现还是缺了好些人。库勃拉克的排里开小差的特别多。库勃拉克本人白天到亲戚家里去辞行,此刻这是醉醺醺的。他几次向排里的战士痛哭流涕地说,“象他这样的无赖和下流坯,是不是配受到他们的尊敬的,因此,全队的人都看得出库勃拉克是醉了。”唯有莱奋生装做没有发觉,因为否则的活,他就得把库勃拉克撤职,但是却没有人来代替他。
莱奋生骑在马上检查了队伍,又回到正当中,冷冷地、严厉地举起了一只手。神秘的夜的声息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同志们……”莱奋生开始说,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很清晰,使每个人都能听到,就象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目前不必说。日本人的兵力--虽然不必将它夸大--毕竟还是可观的,因此我们还是暂时隐蔽一下的好。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完全避开危险。不是这样。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这一点是每个游击队员都知道的。我们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游击队员的称号呢?……今天我们完全辜负了这个称号。……我们象一十群十女孩子那样不守纪律!要真是日本人来了,那可怎么办呢?……他们是会把我们统统掐死的,象掐死小鸡那样!……真丢脸!……”莱奋生猛地把身十子朝前一弯,他最后的几句话立刻就象放松的发条一样弹过来,使每个人马上都觉得自己象是突然被捉住的小鸡,会在黑暗中彼几乎不可觉察的,铁一般的手指掐死。
库勃拉克什么都听不懂,连他也深信不疑他说:
“对-对啊……说得……都对……”他把方脑袋转动了一下,大声打起嗝来。
杜鲍夫时刻都等着莱奋生会说:“比方象杜鲍夫他今天就是快做的时候才赶到的,可是我呢,对他寄予的期望却比对任何人都大,真丢脸……”但是莱奋生对谁都没有指名--他一般地不喜欢嗦苏,而是着重一点,好象要将一根可以永久使用的、结实的大钉子敲进去。直到他相信,他的活已经起了作用,这才朝杜鲍夫望了一眼,突然说:“杜鲍夫的排跟着辎重走。……他们的行动非常敏捷……”说了就在马蹬上挺身直立,将马鞭一挥,下令道:“立一正……从右起成三行。……齐步走!……”
霎时间,嚼铁一齐响了起来,马鞍吱吱作声,密密麻麻的人的行列,好象是深渊里的一条大鱼,在夜十色十中轻轻地摆十动着,向古老的锡霍特一阿林岭那边游过去,从那边的十群十山背后,古老而又年青的曙光正在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