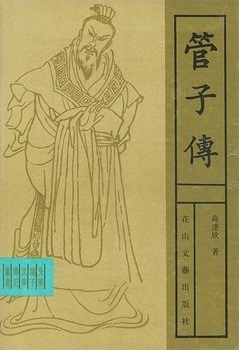第二章 成长
1
1895年,唐霍塞因小女儿之死被迫远走巴塞罗那,无意中为帕布洛打开了一扇新鲜的窗口。
帕布洛一到达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料,这竟然是满口反对教会和政府专制的现代运动的气息。一群颓废派诗人、泛神论者、 象征主义者、哲学家在街头集会游行,他们举着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喊着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口号,“印象派”的光波在他们迷乱的眼神 里激荡,“象征主义”的沉梦在他们蓬松的长发间出没。帕布洛一下就注意到了那个拖着脏污卷发、络腮胡子的卡塔鲁那人圣地亚哥鲁西诺,他是位画家,可他讲 演好像比画画更出色。这位巴塞罗那现代运动的领袖,是西班牙16世纪末绘画大师格列柯的崇拜者。1894年,现代派在海边小镇西特赫斯举行隆重集会,鲁西 诺自己出钱,买下了格列柯的两幅画,专门赠给这次集会。在诗人伊萨特朗诵了大作《肺病印象》之后,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宁愿做象征主义者,宁愿精神失常,不,甚至疯疯癫癫,萎靡堕落,也不愿降格以求,胆小怕事。陈规陋习令人窒息,在我国,谨小慎微实在太过分了!
唐霍塞在靠近码头的旧城区克里斯提那街租到了房屋。这里本身很安静,又能看到马车、火车、渔船等热闹场面;当然,不喜欢走路的唐霍塞更多的是想到住处离美术学校不过几百码远。
10月的一天,帕布洛跟着父亲爬上了一幢叫做交易大楼的高层建筑的最高几层,这就是巴塞罗那美术学校的校址。帕布洛很奇怪,这个学校怎么吊得这么高?幸而一些雕像和喷泉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不然他对学校的印象就真是一无是处了。
帕布洛的腋下夹了几幅人物画,它们将是他能否取得入学资格的准绳。校长安东尼奥恰巴,一位优秀的人物像画家,他看着这个才满14岁的孩子的作品,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帕布洛站在一旁,非常紧张,他悄悄地隐到了父亲的后面,搓着冒汗的手心。
恰巴好不容易看完了,他抬起头对唐霍塞说:
“对我们学校,你的儿子比你更重要。”
2
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吵吵闹闹。帕布洛坐在墙角的一个座位上,显得十分孤独,他除了知道这个教室里有个叫帕布洛的学生外,一无所知。这时,他感觉有一双温和的大眼睛望着他,并向他走来。
“我叫曼奴尔帕拉勒斯,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帕布洛鲁伊斯毕加索。”
他们就这样成了好朋友。帕拉勒斯是塔拉戈纳省荷尔达镇人,比帕布洛大5岁。帕拉勒斯谈起他们的友情,说:
“14岁的时候,他的活动和工作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其他同龄人。他非常早熟,我们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年龄差别。在观察事物、感染他人等方面,他还是我的老师。”
唐霍塞看到儿子心不在焉,有些着急。他知道以儿子的水平,在那个班上是受了点委屈。他亲自找到校长,于是,帕布洛获准跳过这个枯燥死板的初级阶段,参加了“古代美术、实物写生和绘描”的插班考试。
考试的结果吓了老师们一跳。恰巴校长见他年纪小,原定期限一个月。帕布洛可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用一天就交卷了。那些作为考试的素描,上面盖有校印, 至今还保存在该校。当看到少年毕加索的素描所表现出的无可否认的技能时,人们都感叹:这个天才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那些以朴实而夸张的手法描绘的人体精彩生动,真实准确。
唐霍塞见儿子长进不小,就在普拉塔街给他租了一个房间做画室。
帕布洛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专门画室,自然兴奋不已,随手就在画布上涂了一幅好玩的《刺刀冲锋》。他把它带回家里,妹妹洛拉见了,吵着要。帕布洛不给,正闹得很僵,唐霍塞用一个漂亮布娃娃哄住洛拉,才结束了这场兄妹之争。
3
帕布洛平生第一幅最重要的作品即将问世了。
1896年,为了参加一个大型展览会,16岁的帕布洛决定画一套具有“沙龙风格”的作品,他征求父亲的意见。父子俩商量了好久,最后选中了三个题材:《唱经班的男孩》、《第一次圣餐》、《科学与仁慈》----既有宗教的,又有科学的,反映了当时两代人的妥协。
4月,巴塞罗那全市美术展览会上,帕布洛的《第一次圣餐》陈列于第一展览室,标价1500比塞塔。5月15日的《巴塞罗那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次展览的综合评述,其中也提到了这幅画,称其“画中人物富于感情,线条明快”。
帕布洛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的情绪、心理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动笔画那幅著名的《科学与仁慈》。
唐霍塞对此也十分重视,他破天荒地亲自做模特儿,于是他就成了画面左边坐在病人床旁的医生。唐霍塞一生拘谨踏实,极少照相,后人也许只能通过这位 “医生”来想像他的模样了。帕布洛充分借鉴流行的印象派的技巧,在以赭色、棕色表现悲悯和忧郁的同时,映衬着紫红、黄绿诸色,从而一扫伤感颓靡之风,画面 成熟稳重,泰然自若,虽然尚没有摆脱学院派的影子,却也对未来有所预示。比如,病妇那只柔软细长的手,就好比一段安详优美的语言,在款款倾诉。
《科学与仁慈》在1897年的马德里全国美展上获得赞扬,接着又在马拉加市的全省美展上摘取了金像奖。
他在别人吹捧的光晕中,他在别人期待的眼神里,他上了报纸,上了展览,如果他按着别人为他指明的道路走下去,凭帕布洛的聪明,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画家,至少会超过他的父亲,名望于当地,传诵于当时。但是,我们就永远也见不到天才的毕加索了。
帕布洛决意离开巴塞罗那。
正好,放暑假了。帕布洛随父母返乡,他暂时把烦恼丢到了脑后。帕布洛受到了亲戚朋友的热烈欢迎,叔父萨尔瓦拥抱了侄儿,他一直对他抱着很深的期望。常在列塞奥俱乐部聚会的唐霍塞的一群朋友,也设宴为画家帕布洛鲁伊斯毕加索祝贺。
人们不难看出,这段时间帕布洛把绘画丢开了,他一到傍晚,就挽着表妹卡门布拉斯科的手在海滩、河边散步。他腋下夹着一根手杖,戴一顶黑帽子,也遮掩不住帽檐下乌黑眼珠闪出的亮光。洛拉常常跟踪在哥哥的后面,窥视他们的亲密举动,然后回来学给大人们看,逗得满堂笑声。
帕布洛与表妹的郎才女貌让人们认定了这是天生的一对。他还特意在一个铃鼓上画了一束花送给布拉斯科,因为这么名贵的花,他还买不起,他不好意思向叔 父要钱干这些事情。过了几天,布拉斯科说,她不能再和他一起出去了。原来,布拉斯科的妈妈嫌帕布洛家里穷,社会地位不高,配不上她的女儿。
帕布洛虽然冷静地和布拉斯科分手了,他的心中却烙上了不可磨灭的伤痕。那么短暂而圣洁的初恋呵!在以后毕加索一生的情海里,很少有过这种单纯和爱恋了,而更多的是成人化的感情的依托、寂寞的排遣与情欲的宣泄。
4
暑期刚过,毕加索就在萨尔瓦的帮助下,孤身去了首都马德里。执教于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的牟诺斯德格拉因先生是唐霍塞的朋友,他的引荐使帕布洛顺利 地就读于该校。但他很少去教室上课,不是呆在学校的画室,就是跑去普拉多美术馆,在那里,他又一次被委拉斯开兹、格列柯、鲁本斯吸引住了。“这才是真正的 学校。”帕布洛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
埃尔格列柯引起了帕布洛的特别注意。生活在16至17世纪的格列柯属威尼斯派,所作多宗教题材,人物瘦长变形,在一种神秘气质里宣扬苦行主义精神。他那通过手势和眼神揭示人物心理的哲人式画法感染了帕布洛。去普拉多复制委拉斯开兹和格列柯的名画,成了帕布洛的必修功课。
天气稍暖,帕布洛漫步在喧嚣的街头,手里拿着写生本,他很快就完成了5本街景的写生,其中2本只用了一个月。帕布洛几乎走遍了全城,尤其是饥饿与贫 困的波希米亚人出没的那些暗得可怕的小胡同。他敏锐的目光开始对实物的可塑性进行考察。他发觉,同样是人,富人总是那么大腹便便,目空一切;而穷人却枯肠 瘦肚,委琐难堪。物体这种可塑的品质,后来在他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绘画中就表达了出来。
萨尔瓦听说帕布洛在学校专门逃学,很不高兴。在这位一心只想侄子光宗耀祖的叔父看来,只有圣费尔纳多学院才能使帕布洛飞黄腾达,如此自由散漫的帕布洛太让他失望了。他一气之下,停止了对帕布洛的接济。
帕布洛本来十分拮据,这一来,更是雪上加霜。他穷得连绘画的材料也买不起,毕加索曾对诗人艾吕雅回忆这个时候说:
“饿肚皮是小事,几天不能创作,我就像停止了呼吸一样。”
无奈,他便把一张画纸做几张用,密密麻麻画,重重叠叠画,有一张后来被发现的画纸,上面涂满了小丑、狗、马和吉卜赛人。由于画得太密,辨认不清,只 数得出八个签名,前面都是同一日期:“12月14日”。帕布洛总是把日期放在签名之前,有人对此不解,他说,时间比名字更重要。
冬天,马德里特别地冷,帕布洛身无分文,每天喝西北风度日,他终于病倒了,猩红热使他成了格列柯画中一样的人物。为了捡回一条命,他被迫回到巴塞罗那父母的身边。
唐霍塞对儿子明显冷淡了,以前欢迎过帕布洛的人也怪怪的,惟有母亲洛佩斯相信儿子,她拍着帕布洛的肩膀说:“要是你当兵,就能做将军;要是你当僧侣,就能做教皇。”1946年后,毕加索当着情人弗朗索瓦吉洛的面,接上了母亲的话茬:
“可是我当了画家,就成了毕加索。”
母亲的话对帕布洛触动很大。从此,他的画面上不再用“鲁伊斯(Ruiz)”署名。“毕加索(Picasso)”,大家都这么叫他,一是这个姓很新鲜,二是他和母亲太相像了,他愿意这么改过来。
家里太闷,毕加索想起了好朋友曼奴尔帕拉勒斯。1898年6月,毕加索来到了曼奴尔的家----阿拉贡边区的荷尔达。他头一回沐浴农村的风光,与和气 热情而又沉默寡言的农民打成一片。曼奴尔家所在的村庄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桑雷恩花园。鲜花遍野,绿树成荫,山丘河谷长满了葡萄滕和橄榄树,石灰石峰峦有 如哥特式建筑,高耸云霄。毕加索在这里很少画画,他学习了各种农活,给骡子装载,给公牛套车,以及酿酒等等,他都极有兴趣。
他和曼奴尔在山上找到了一个山洞,那里幽静凉爽,好比天然画室。他们还筑起了一堵墙,用以避风。那年夏天,在西班牙历史上是百年不遇的炎热,他们在 山洞里一个劲地画牛、羊、驴、马,根本不管外面热浪滔天。他们3个月后才下山,而毕加索被好客的曼奴尔家人留到了第二年的1月份。他研究冬天的落叶从枯黄 到降落的全过程。他最喜欢的是山区的太陽,那么纯净而热烈,宛如山区姑娘湛然的明眸。他对曼奴尔说:“印象派怎么画得出这样的太陽呢?光线多么美呀。”
5
1899年2月,毕加索从荷尔达回到巴塞罗那。出去这么久,父母很担心,生怕他住不了几天又要跑,只好同意他不去学院的要求。毕加索的同学约瑟夫卡尔多那专攻雕塑,他十分钦羡毕加索的才华,邀请他来共用他的画室,解了毕加索的燃眉之急。
初春,巴塞罗那的天气转向和暖。毕加索整天都一头扎在画稿当中,他画了又改,改了又画,似乎没有满意的时候。可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美术活动已经纳入了“现代派”的观察范围。
一天,毕加索正在修改作品。忽然,门开了,信佛刮进来一阵旋风,一个长头发青年就站在了毕加索的面前,问他是不是安达卢西亚人毕加索。毕加索惊讶地睁大黑色的眼睛,没有做声。来人也不再问,视线转到画板上,那件被改得鬼画桃符般的作品使他弓着腰,足足看了十来分钟。
他就是诗人、画家沙巴泰,毕加索终生的朋友和知音。
多年后,毕加索与沙巴泰都回忆起这第一次会面。
毕加索说:
“当我走过他的面前,向他道别时,我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禁为他的整个形象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而折服。”
沙巴泰说:
“我一看见他就想,德梭那小子没说错,他果真是非凡的。他的眼睛亮得像一颗星,你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那双手虽小,但灵巧、好看,动起来的时候好像在说话。他的画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说不出,但深得我心。”
毕加索特别神往英国,他禀承了父亲对英国家具、服装和绘画的爱好,他尤其想见识一下英国的妇女,在他的心目中,英国妇女美丽、勇敢,富有魅力。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经巴黎到伦敦。
临走前,毕加索画了一幅自画像给自己壮行,他遥视浩茫的天空,大雁飞过,万里碧空,挑战的豪情和征服的欲望蓦然跃起。毕加索神定气足地在自画像的眉毛上连写三遍:“老子天下第一。”
更新至 · 附录:毕加索年表
2024-09-09网友评论
“毕加索”相关作品
-
罗斯福传记
《罗斯福传记》罗斯福,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残疾人总统,四次当选,任职长达13年。他是一个精明的统治者,在驾驭政府与时代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胆略和才能,由于他在内政方面的伟大建树和在与法西斯斗争中的不朽功绩,而被世人公认为同华盛顿、林肯相比肩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康拉德・布莱克 · 著 -
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在线阅读
阿道夫.希特勒 · 著 -
肯尼迪传
《肯尼迪传》《肯尼迪传》在线阅读,西奥多・索伦森
西奥多・索伦森 · 著 -
彼得大帝传略
《彼得大帝传略》彼得大帝传略 在线阅读,帕普连科
帕普连科 · 著 -
渴望生活梵高传
《渴望生活梵高传》《渴望生活梵高传》是(美)欧文・斯通编著的一本书籍。《渴望生活――梵高传》是其年仅二十六岁时的作品。欧文・斯通认为,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名人深厚的 成就和辉煌,而是他们追求和探索的过程。七十余年来,梵高悲惨而成就辉煌的人生震撼无数读者。这部作品也成为欧文・斯通的成名作,被译成八十余种文字,发 行数千万
(美)欧文・斯通 · 著 -
【忏悔录】卢梭自传
《【忏悔录】卢梭自传》【忏悔录】卢梭自传在线阅读
卢梭 · 著 -
司马懿大传
《司马懿大传》司马懿大传,在线阅读
马敏学 · 著 -
王安石传
《王安石传》王安石传在线阅读
梁启超 · 著 -
武则天正传
《武则天正传》林语堂《武则天正传》:武则天这个女人活了八十二岁,权倾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生活对她而言就如同游戏一样,她有比普通人更强烈的欲望,以至于秽闻不断。
林语堂 · 著 -
成吉思汗传
《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传,在线阅读
勒内・格鲁塞 · 著 -
汉武帝传
《汉武帝传》汉武帝传,在线阅读
石静 · 著 -
华盛顿传
《华盛顿传》华盛顿传记在线阅读
华盛顿・欧文 · 著 -
朱元璋传
《朱元璋传》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皇帝中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
吴晗 · 著 -
魏阉全传
《魏阉全传》魏阉全传,在线阅读
魏忠贤 · 著 -
富兰克林自传
《富兰克林自传》富兰克林自传在线阅读
本杰明・富兰克林 · 著 -
叶赛宁传
《叶赛宁传》叶赛宁传在线阅读
南平编著 · 著 -
谋圣张良
《谋圣张良》谋圣张良,在线阅读
张毅 · 著 -
狄青传
《狄青传》狄青传在线阅读
许慕羲 · 著 -
俾斯麦传记
《俾斯麦传记》俾斯麦传记在线阅读;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俾斯麦传记 。激励人心的奋斗传奇、惊心动魄的政坛谋略、波澜壮阔的统一历程 。10年统一德意志,政治强人一手缔造世界强国 。
艾伦・帕麦尔 · 著 -
刘邦大传
《刘邦大传》刘邦大传在线阅读
陈文德 · 著 -
胡雪岩全传
《胡雪岩全传》胡雪岩全传,在线阅读
林学武 · 著 -
张居正大传
《张居正大传》《张居正大传》介绍了张居正是明朝中期的重臣,他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本书讲述了传主如何从一个普通人直至位极人臣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纷繁芜杂的官场斗争。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对传主所置身的时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亦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
朱东润 · 著 -
毕加索传
《毕加索传》毕加索传在线阅读
毕加索 · 著 -
秦始皇大传
《秦始皇大传》秦始皇大传,在线阅读,人物传记
江柳人 · 著 -
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李鸿章传》在线阅读
梁启超 · 著 -
曼德拉传
《曼德拉传》《曼德拉传》,名人传,曼德拉传奇 《曼德拉传》在线阅读
[美]查伦•史密斯 · 著 -
甘地传
《甘地传》《甘地传》在线阅读;甘地,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
米歇尔.尼科尔森 · 著 -
巴顿传
《巴顿传》巴顿将军传,巴顿传,《巴顿传》在线阅读
巴顿 · 著 -
艾森豪威尔传
《艾森豪威尔传》艾森豪威尔传,艾森豪威尔简介,名著《艾森豪威尔传》
斯蒂芬・安布罗斯 · 著 -
林徽因传
《林徽因传》《林徽因传》不仅仅写出了林徽因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子,有着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积极的人生启示。
张清平 · 著 -
隆美尔传
《隆美尔传》《隆美尔传》在线阅读
隆美尔传 · 著 -
德川家康传
《德川家康传》《德川家康》洋洋五百五十万言,将日本战国中后期织田信长、武田信玄、德川家康、丰臣秀 吉等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德川家康最终脱颖而出,结束战国烽烟,开启三百年太平盛世。作品展现了德川家康作为乱世终 结者和盛世开创者丰满、曲折、传奇的一生,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与
一条瑜 · 著 -
慈禧后私生活实录
《慈禧后私生活实录》《慈禧后私生活实录》
德龄 · 著 -
西施艳史演义
《西施艳史演义》《西施艳史演义》在线阅读
佚名 · 著 -
李小龙传
《李小龙传》《李小龙传》
崧灵 · 著 -
心学大师王阳明大传
《心学大师王阳明大传》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王阳明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士大夫之一,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本书,以文学笔调真实叙述了王阳明的一生:其“德行”及“事功”,并以现代理论与方法,阐述了王阳明的“言”即其思想,再现了王阳明的人格魅力。
周月亮 · 著 -
我的另一面
《我的另一面》我的另一面在线阅读;作者:西德尼・谢尔顿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
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
《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在线阅读;作者:易水寒
易水寒 · 著 -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在线阅读;作者:朱可夫
朱可夫 · 著 -
诸葛亮传
《诸葛亮传》诸葛亮真有那么神奇吗?他真的算无遗策,用兵如神吗?诸葛亮的智慧又是从何处来的呢?答案尽在书中。
若虚 · 著 -
赵匡胤
《赵匡胤》《赵匡胤》传记书籍在线阅读;五代十国,神州血雨腥风,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望天悲问:大乱何时休?!国家何时大治?21岁的赵匡胤,辞别父母和妻子,离家闯荡,千里送京娘,受尽磨难。...
郭兆祥,李金水 · 著 -
居里夫人传
《居里夫人传》一书回顾了居里夫人这位影响过世界进程的伟大女性不平凡的一生,主要描述的是居里夫人的品质、她的工作精神、她的处事态度。作者艾芙·居里向读者详介了她 的母亲除了在科学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外,她还用自己一生为人处世的崇高行为给女儿树立榜样,对女儿的教育也有许多独特的做法。读完这部书,相信居里夫人对 困苦和灾
(法〕艾夫﹒居里 · 著 -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在线阅读
吕峥 · 著 -
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
《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在线阅读;作者:罗大伦
罗大伦 · 著 -
希特勒传
《希特勒传》《希特勒传》在线阅读
约翰・托兰 · 著 -
萨特传
《萨特传》萨特传在线阅读;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西蒙娜・德・波伏娃 · 著 -
李自成
《李自成》《李自成》, 姚雪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3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小说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 农民起义军由弱小变强大,转败为胜推翻明王朝统治、抗击清军南下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起义军
姚雪垠 · 著 -
杜甫传
《杜甫传》杜甫传在线阅读;作者:还珠楼主
还珠楼主 · 著 -
和珅·帝王心腹
《和珅·帝王心腹》和珅·帝王心腹在线阅读
李师江 · 著 -
帝王师・刘伯温
《帝王师・刘伯温》帝王师・刘伯温在线阅读;作者:度阴山
度阴山 · 著 -
李煜
《李煜》南唐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又最奢靡、最血腥又最文雅的时代,后主李煜在政治上偏安懦弱,历来被史家贬为奢靡误国的“亡国之君”,《中国历代文人长篇传记小说之李煜》从文人的角度来剖析后主的一生,推翻史家的论调,丝丝入扣地点评出后主仁爱、细腻、宽厚、唯美的文化品格。南唐之亡,非亡于奢靡,而是亡于文人与政治的对决
刘小川 · 著 -
左宗棠发迹史
《左宗棠发迹史》左宗棠发迹史在线阅读;作者:汪衍振
汪衍振 · 著 -
林肯传记
《林肯传记》林肯传记在线阅读,欢迎大家免费阅读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 著 -
屈原传
《屈原传》屈原传在线阅读
王健强 · 著 -
老子传
《老子传》老子传在线阅读
余世存 · 著 -
被埋没的天才
《被埋没的天才》被埋没的天才在线阅读,被埋没的天才txt电子书阅读
玛格丽特・切尼(美) · 著 -
荀子传
《荀子传》荀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本书写出思想家的思想深度、历史地位和人格精神,又能将史料与生活相融合,既要历史真实,又要活的灵魂;让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活脱脱的站立在读者面前。
刘志轩、刘如心 · 著 -
管子传
《管子传》管子传在线阅读;管子(公元前725-645),名仲,我国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
高连欣 · 著 -
庄子传
《庄子传》庄子传在线阅读
王新民 · 著 -
徐志摩传
《徐志摩传》本书采用别致的纪传体手法,围绕徐志摩短暂而丰富的一生,细加考究、多有新解。叙述真实而全面,史料考订颇有收获,既真切记录了徐志摩生命中的留学生涯、文学活动,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诗人,更对徐志摩一生中重要的情路历程秉笔直书,写尽了张幼仪的质朴而深沉的爱、陆小曼热烈而洒脱的情,亦不讳言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漠视与
韩石山 ·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