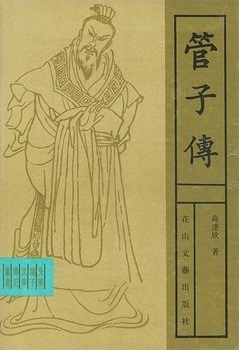1
1902年1月,毕加索出现在巴塞罗那梅尔赛德街自己的家里。虽然还很穷,但他名气不小,家里人见他回来都十分高兴。唐霍塞和萨尔瓦年纪一大把,也懒得对毕加索的艺术家派头发表评论了。
画家罗盖罗尔在伦巴拉斯中段附近的阿萨尔托街上有一间有陽台的画室,毕加索征得他的同意,借了一角之地,作为他的工作间。他也有西班牙人共同的生活 习惯,晚上睡得特别迟,早上则尽量往后拖延,直到上午11点左右,他才从家里出来,徒步走过旧城区那些狭小的巷道,一路上,他的眼光四处搜索,寻找可以入 画的人和事;看到哪里聚众或吵闹,他就好奇地跑过去,这倒不是想画什么,而是积蓄一些噱头和谈资。午后两三点,他赶到“四猫酒店”吃中饭,就不至于新鲜事 都被朋友们占了。傍晚,他呆在画室里,先在一张纸上胡乱画些东西,或者看几页书,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把一切与创作无关的事都置之度外,他仿佛在另一个 世界漫游,流连忘返。
毕加索不用调色板。他的右边有一张小桌子,上面铺着报纸和三四个插满了画笔的大罐头盒子,里边有松节油溶剂。他每次从盒子里选出一支笔,在报纸上蹭干。需要一种单色的时候,他就从油筒里往报纸上挤出一些。
在画架前,毕加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几乎从不改变姿势。他作画时通常不允许别人在场,然而凡是得到许可看过毕加索作画的人,都深切地体会到“全神贯注”是什么意思。沙巴泰说:
“他作画时思想如此集中,如此沉静,以至于任何人无论从远处或近处看到他,都懂得自行检点,保持肃静。”
同伴们总是调侃毕加索老是穿着那么一套衣服,毕加索也注意到了自己确实太寒酸了,他想讲究一点,可是没有钱。这时,他听说马纳奇在巴黎伯萨韦尔画 廊举办了他的画展,大约有30幅,如《卢森堡》、《静物》、《戴珠宝项圈的妓女》等。他神气地对同伴们夸口说,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旧貌换新颜了。
毕加索天天等着巴黎那边传来好消息。
不出所料,画展获得了好评,评论家阿德廉法奇在序文中称赞这些作品“使我们先睹为快,迷恋那种在调子上时而粗犷奔放,时而细腻老练的卓越技巧”。
出乎所料,还是没有卖出去一张画。
毕加索的“阔梦”破产了。他还是穿着那套旧衣服,只是改变了领带和背心。同伴们继续笑他换汤不换药。
毕加索硬着头皮走进一家缝纫店。他看了一眼铺面上挂着的高级时髦服装,摸摸瘪得不好意思的口袋,正待出去,被人喊住了:
“请问是不是毕加索先生?”
“您怎么认得我?”毕加索惊诧莫名。
“我在萨拉帕雷斯的画廊参观过您的画展,那里有您的照片。我十分喜欢您的画。”
毕加索转身又进了屋,他和裁缝索累谈得十分投入。索累答应为毕加索做一套挺拔合身的新装,不收费,条件是毕加索为他本人及全家各画一幅肖像。毕加索解释说,这是互相交换对方的长处。
毕加索画的画和索累做的衣都非常的棒。毕加索还迷住了索累剪裁衣服的熟练技巧,不久,他就将之运用到了绘画上。
毕加索依然孤独。同伴们的目光仅仅停留在他的衣着上,他们无法理解他的作品。这从他给马克斯耶科的信中可见一斑:“我给这里的画家、朋友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认为形似尚待商榷,神似有些过分,这太可笑了。”
蓝色的调子充斥着画面。凄楚与绝望,感伤与愤慨,一齐凝聚于毫端。毕加索所见所闻所思所画,都在一个字上----病。
天有病,人知否?
2
1902年夏末,毕加索第三次到巴黎。
塞纳路上一幢17世纪的老房,门楣上写着“马罗克旅馆”。它的顶层有一间小阁楼,就住着毕加索和另一位西班牙雕塑家西斯凯特。一张大铁床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因而两人总有一个必须大部分时间坐在床上。他们都穷得吃不饱饭,就望着床上堆积的作品发呆。
马克斯耶科要来看毕加索,毕加索不允,他宁愿自己去耶科那里。耶科明白,毕加索的自尊心很强,他只能不露声色地帮助他。不久,耶科在一家百货店找 到了工作,生活有了明显好转,他就在靠近巴黎工业中心的伏尔泰大街租了一间同样简陋但比较宽敞的房子,然后邀请毕加索来住。有意思的是,两个朋友共一顶礼 帽,谁出去谁戴,以至于邻居很长时间都认为这间房里只住了一个人。
床也只有一张。晚上,耶科睡觉,毕加索画画;白天,耶科到店里上班,毕加索则蒙头大睡。
贫穷与共的还有沙巴泰。有一次,毕加索和耶科兜底翻出各自的腰包,凑了几个硬币交给沙巴泰,叫他去买鸡蛋和别的食物。沙巴泰在商店里转来转去,最后 捧着鸡蛋,还有一块面包和两根香肠,兴冲冲地往回跑。也许是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去填饱肚子,又加上视力不好,沙巴泰上楼时不幸摔倒。鸡蛋破了,满楼板的印象 派画。沙巴泰把自己这幅无意中的“创作”丢在一边,手忙脚乱地抱着香肠、面包撞开门。毕加索听说等待已久的鸡蛋遇难,大发雷霆,对着沙巴泰吼道:
“我们把最后几个钱都交给你了,可你连个完整的鸡蛋也拿不回来。你这辈子算是白活。”
毕加索气愤地抄起一把叉子,插进一根香肠。“嘭!”香肠竟爆炸了。毕加索又试另一根香肠,也爆炸了。
沙巴泰的视力实在太差,他买了两根因时间太久而发酵的香肠,里边像气球似的充满气体,叉尖刚一戳破外皮就爆开了。
毕加索和耶科哭笑不得,只好把面包分吃了。而沙巴泰一副做错了事的样子,饿着肚子低头认罪。
10月份,贝尔特魏尔筹办新画展,毕加索在参展画家之列,其他的还有洛奈、皮乔特、吉鲁埃德等人。毕加索“虚无和绝望”的作品引起了高更的挚友查 尔斯莫里斯的关注,他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指出:“他像一个年轻的神,想要重新创造世界,但他只是一个忧郁的神…………他的世界并不比麻疯病人的病房更适 合居住,他的画本身也是病魔缠身。难道命运只让这个令人恐惧的早熟孩子创作反映生活消极面的杰作,只让他表现他比任何人都深受其害的病魔吗?”
这一篇写得一样异常有力的文章,震撼了毕加索。他要见一见莫里斯,这个准确诊断了他的思想的人一定也能治愈他的心病。
莫里斯一眼就看出了他面前这个腼腆小伙子是个天才,他意味深长地告诫毕加索:“仅有痛苦是不够的,还要有同情,同情能让人重新振作起来,并认识到自 己事业的价值,这不是用钱能衡量得了的。”他向毕加索推荐了高更的游记《诺阿》。高更那纯朴的、不懈追求的乐观主义对毕加索是一种激励,虽然,彻底摆脱悲 观和沮丧还要一个过程。
越怕发生的事越是来得快。神经质的个性使耶科失掉了饭碗,耶科不乏幽默地对毕加索说:
“我们又要搬家了。”
毕加索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一点儿也不好笑。
3
食不果腹,让毕加索倍加思家。
他把没有烧完的画捆成一大卷,寄放在塞纳街的画家朋友皮乔特处。他决定暂时回西班牙。
几个月后,当毕加索再来巴黎寻找皮乔特时,此人已搬往它处。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皮乔特的下落,皮乔特却把他的画忘在老房子的一只柜子上面了。
毕加索气急败坏地跑到皮乔特原先栖身的旅馆,在那只柜子顶上积得厚厚的一层灰尘下面,那捆画居然还在!
毕加索无法表达自己大起大落的感情,他只是紧紧地攥住一掌灰尘,谢谢它们保护了他的作品。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画出了蓝色时期的最优秀的作品。《生活》作于1903,规模相当大,构图煞费苦心。画面上一共有7个人物,左侧一对裸体的情侣,比 喻放纵的爱情,男人的手指向右边,女人循着手指望过去,显得惶惶不安。右边一个抱婴孩的母亲,象征着生活的重负,母亲一脸沧桑,看着前面的男女,神色冷 峻,目光严厉,好像有责备的意味。背景是两幅素描,女人的姿势都是缩成一团,只不过上面一幅的女人是窝在男人的怀里,无情地揭示出从相依为命到孤苦无依的 必然之路。
在画上增加人物形象,这种“拼贴”是不是含有裁缝索累的技法呢。当然,这只是表面的。绘画应当走出只能摹写自然的局限,它完全可以表达戏剧化的感情 体验。我们在《生活》这幅画中,能够感到人物与人物,与空间,与读者,甚至与作品背后的作者,有一种共鸣,就仿佛在读一首押韵的诗,这才是画的本质所在。 1946年,毕加索对弗朗索瓦说:
“绘画就是写诗,以造型艺术的韵律写成诗句,而绝不能写成无韵的散文。”他大胆地将韵律也纳入了绘画的基本质素之一。
他还说:
我从不认为,作画只是为了少数人的享受。我总是感觉到,一幅画必须在看画的人身上唤起点什么才达到了目的。比如在莫里哀的作品里,就存在一些东西, 使聪明的人发笑,也使看不懂的人发笑。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样有这种东西…………绘画也绝不是儿戏,而是极为严肃甚至神秘的艺事,别看是简单的一笔,它可以代表一 个活的生灵。不要局限于图像,要看到它真正的实质----那才叫妙不可言呢。
毕加索广泛涉猎各种美术风格,他在钻研西方大师的妙手丹青之余,还痴迷于东方和非洲的艺术特色,比如中国的水彩画和线条画,日本的“浮世绘”,西非 的丹族面具及其他黑人雕刻等。毕加索不断地在传统的绘画意义上加入诗和哲学的元素,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借助诗和哲学的力量来使绘画独立,而不是单纯的自然 风景与宗教故事的摹写。富于浓厚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的原始艺术,正中了毕加索的下怀。
1904年春,毕加索在沙巴泰家里的墙壁上,创作了一些具有亚述浮雕神采的壁画。在对着窗子的一堵墙上,画上一个半裸的摩尔人被绞死在树上,而他下面的一对年轻男女,却一丝不挂地正在“狂欢热恋”。
过了一会儿,他又把墙上高处的一扇圆窗用作他绘画的一部分,在窗上添几笔,它就变成一只俯视一切的眼睛。毕加索题词空白处:
“我的胡须虽已和我分开,但仍和我一样是天神。”
这种绘画和题词的方式是他新近从中国画那里学来的,只是此间透露出来的自负和疑问依然是毕加索式的。
东方艺术西渐古已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明治维新的成功,欧洲各国博物馆或多或少都藏有历代的中国书画,大英博物馆就收藏了中国最早的名画家顾 恺之的《女史箴图》。不过直到19世纪后期,当马奈、凡高、塞尚、高更等印象派大师,力图寻找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时,中国和日本的绘画才进入他们的视野。 特别是日本的“浮世绘”,成为许多画家直接研究的资料。
“浮世绘”,是汲取中国的线描和木板印刷而创造的艺术,在反映日本社会的世相百态中,形成的独特的风格。画面上常用大块的黑色,手工染成,因而更体 现出装饰意味。由于可以复制,故流传广泛,当时流向欧洲的各种日本商品的包装物上,总是印有“浮世绘”,西方画家很容易得到它。我们在马奈画的左拉肖像的 墙壁上,在凡高的自画像的背景上,都能看到“浮世绘”的影响。以后的毕加索、马蒂斯等,就更不用说了。
4
在巴塞罗那期间,毕加索画了一系列关于盲人的作品。一方面盲人最能表现人类的困境。盲目的,不仅是看不到光明,而且根本就没有光明的概念。沉于黑暗 的深渊,它的尽头依然是黑暗。爱情是盲目的,幸福是盲目的,只有苦难永远睁大着狞厉的眼睛。《盲人用膳》这幅画上,一个盲人坐在桌前,眼窝深陷,毫无生 气,枯瘦如柴的手摸索着桌上的水壶和面包。即将饱餐一顿,也看不出什么兴奋,面包没长眼睛,它下次还会不会飞到盲人的手中呢?
另一方面,看与知之间有很大的出入。不用眼睛,更能探究到艺术的真谛。眼睛看到的,都是表面的,肤浅的,戴着欺骗人的面具。要走进内心,走进人类的本质,必须睁开第三只眼睛,也就是毕加索所说的“内在的眼睛”。
介于感官知觉与更深一层的思维领域之间,有一种观察力,不妨比作一只内在的眼睛,它能够富有感情的观看和思考。通过这种想像的眼睛,即使丧失了生理上的视力,也能观看、理解和爱,而且在外在的眼睛失明之后,这种内在的视力可能变得愈加敏锐。
《年老的犹太人》坐在地上,他那双眼睛早已不起作用,旁边有一个目光明亮的小孩照料着他。小孩虽然看得见,但老人却是他的支柱,小孩是老人的“内在的眼睛”。他们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