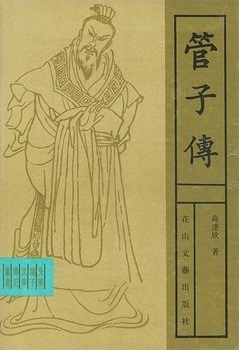第四章 居里夫人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 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 的。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 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 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 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 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陽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 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 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 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 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 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 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 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 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 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 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陰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1859年5月15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 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 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比埃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 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6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 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 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 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 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10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 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 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在这所陰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 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 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比埃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雅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雅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雅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还须再过十个月,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才肯答应和他结婚。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陽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 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 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1895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快到八月半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在商提宜附近一个别墅里住下了。这个别墅也是布罗妮雅发现的,她把这个幽静的住处租了几个月。同比埃尔和玛丽一起住在 这里的,还有老德卢卡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他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叫“禄”。 斯可罗多夫基教师和海拉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这所颇有诗意的房子,藏在树林中,与外面隔绝,树林里满是野鸡和野兔,地上盖满了铃兰花的 叶子,真是可爱极了;而住在里面的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的情谊,也真是好极了,比埃尔居里得到了他的妻族的永久爱慕。他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谈科学,同 小“禄”很严肃地交谈,小“禄”刚三岁,好看,滑稽,愉快,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居里大夫和夫人有时由梭镇到商提宜来看他们,大桌子上就又添了两份餐具,话 谈得很热烈,由化学说到医学,再说到儿童教育,由社会思想泛论到法兰西和波兰的一般观念。
更新至 · 第八章 晚年的辉煌
2024-09-25网友评论
“(法〕艾夫﹒居里”相关作品
-
罗斯福传记
《罗斯福传记》罗斯福,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残疾人总统,四次当选,任职长达13年。他是一个精明的统治者,在驾驭政府与时代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胆略和才能,由于他在内政方面的伟大建树和在与法西斯斗争中的不朽功绩,而被世人公认为同华盛顿、林肯相比肩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康拉德・布莱克 · 著 -
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在线阅读
阿道夫.希特勒 · 著 -
肯尼迪传
《肯尼迪传》《肯尼迪传》在线阅读,西奥多・索伦森
西奥多・索伦森 · 著 -
彼得大帝传略
《彼得大帝传略》彼得大帝传略 在线阅读,帕普连科
帕普连科 · 著 -
渴望生活梵高传
《渴望生活梵高传》《渴望生活梵高传》是(美)欧文・斯通编著的一本书籍。《渴望生活――梵高传》是其年仅二十六岁时的作品。欧文・斯通认为,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名人深厚的 成就和辉煌,而是他们追求和探索的过程。七十余年来,梵高悲惨而成就辉煌的人生震撼无数读者。这部作品也成为欧文・斯通的成名作,被译成八十余种文字,发 行数千万
(美)欧文・斯通 · 著 -
【忏悔录】卢梭自传
《【忏悔录】卢梭自传》【忏悔录】卢梭自传在线阅读
卢梭 · 著 -
司马懿大传
《司马懿大传》司马懿大传,在线阅读
马敏学 · 著 -
王安石传
《王安石传》王安石传在线阅读
梁启超 · 著 -
武则天正传
《武则天正传》林语堂《武则天正传》:武则天这个女人活了八十二岁,权倾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生活对她而言就如同游戏一样,她有比普通人更强烈的欲望,以至于秽闻不断。
林语堂 · 著 -
成吉思汗传
《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传,在线阅读
勒内・格鲁塞 · 著 -
汉武帝传
《汉武帝传》汉武帝传,在线阅读
石静 · 著 -
华盛顿传
《华盛顿传》华盛顿传记在线阅读
华盛顿・欧文 · 著 -
朱元璋传
《朱元璋传》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皇帝中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
吴晗 · 著 -
魏阉全传
《魏阉全传》魏阉全传,在线阅读
魏忠贤 · 著 -
富兰克林自传
《富兰克林自传》富兰克林自传在线阅读
本杰明・富兰克林 · 著 -
叶赛宁传
《叶赛宁传》叶赛宁传在线阅读
南平编著 · 著 -
谋圣张良
《谋圣张良》谋圣张良,在线阅读
张毅 · 著 -
狄青传
《狄青传》狄青传在线阅读
许慕羲 · 著 -
俾斯麦传记
《俾斯麦传记》俾斯麦传记在线阅读;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俾斯麦传记 。激励人心的奋斗传奇、惊心动魄的政坛谋略、波澜壮阔的统一历程 。10年统一德意志,政治强人一手缔造世界强国 。
艾伦・帕麦尔 · 著 -
刘邦大传
《刘邦大传》刘邦大传在线阅读
陈文德 · 著 -
胡雪岩全传
《胡雪岩全传》胡雪岩全传,在线阅读
林学武 · 著 -
张居正大传
《张居正大传》《张居正大传》介绍了张居正是明朝中期的重臣,他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本书讲述了传主如何从一个普通人直至位极人臣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纷繁芜杂的官场斗争。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对传主所置身的时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亦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
朱东润 · 著 -
毕加索传
《毕加索传》毕加索传在线阅读
毕加索 · 著 -
秦始皇大传
《秦始皇大传》秦始皇大传,在线阅读,人物传记
江柳人 · 著 -
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李鸿章传》在线阅读
梁启超 · 著 -
曼德拉传
《曼德拉传》《曼德拉传》,名人传,曼德拉传奇 《曼德拉传》在线阅读
[美]查伦•史密斯 · 著 -
甘地传
《甘地传》《甘地传》在线阅读;甘地,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
米歇尔.尼科尔森 · 著 -
巴顿传
《巴顿传》巴顿将军传,巴顿传,《巴顿传》在线阅读
巴顿 · 著 -
艾森豪威尔传
《艾森豪威尔传》艾森豪威尔传,艾森豪威尔简介,名著《艾森豪威尔传》
斯蒂芬・安布罗斯 · 著 -
林徽因传
《林徽因传》《林徽因传》不仅仅写出了林徽因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子,有着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积极的人生启示。
张清平 · 著 -
隆美尔传
《隆美尔传》《隆美尔传》在线阅读
隆美尔传 · 著 -
德川家康传
《德川家康传》《德川家康》洋洋五百五十万言,将日本战国中后期织田信长、武田信玄、德川家康、丰臣秀 吉等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德川家康最终脱颖而出,结束战国烽烟,开启三百年太平盛世。作品展现了德川家康作为乱世终 结者和盛世开创者丰满、曲折、传奇的一生,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与
一条瑜 · 著 -
慈禧后私生活实录
《慈禧后私生活实录》《慈禧后私生活实录》
德龄 · 著 -
西施艳史演义
《西施艳史演义》《西施艳史演义》在线阅读
佚名 · 著 -
李小龙传
《李小龙传》《李小龙传》
崧灵 · 著 -
心学大师王阳明大传
《心学大师王阳明大传》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王阳明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士大夫之一,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本书,以文学笔调真实叙述了王阳明的一生:其“德行”及“事功”,并以现代理论与方法,阐述了王阳明的“言”即其思想,再现了王阳明的人格魅力。
周月亮 · 著 -
我的另一面
《我的另一面》我的另一面在线阅读;作者:西德尼・谢尔顿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
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
《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在线阅读;作者:易水寒
易水寒 · 著 -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在线阅读;作者:朱可夫
朱可夫 · 著 -
诸葛亮传
《诸葛亮传》诸葛亮真有那么神奇吗?他真的算无遗策,用兵如神吗?诸葛亮的智慧又是从何处来的呢?答案尽在书中。
若虚 · 著 -
赵匡胤
《赵匡胤》《赵匡胤》传记书籍在线阅读;五代十国,神州血雨腥风,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望天悲问:大乱何时休?!国家何时大治?21岁的赵匡胤,辞别父母和妻子,离家闯荡,千里送京娘,受尽磨难。...
郭兆祥,李金水 · 著 -
居里夫人传
《居里夫人传》一书回顾了居里夫人这位影响过世界进程的伟大女性不平凡的一生,主要描述的是居里夫人的品质、她的工作精神、她的处事态度。作者艾芙·居里向读者详介了她 的母亲除了在科学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外,她还用自己一生为人处世的崇高行为给女儿树立榜样,对女儿的教育也有许多独特的做法。读完这部书,相信居里夫人对 困苦和灾
(法〕艾夫﹒居里 · 著 -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在线阅读
吕峥 · 著 -
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
《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在线阅读;作者:罗大伦
罗大伦 · 著 -
希特勒传
《希特勒传》《希特勒传》在线阅读
约翰・托兰 · 著 -
萨特传
《萨特传》萨特传在线阅读;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西蒙娜・德・波伏娃 · 著 -
李自成
《李自成》《李自成》, 姚雪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3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小说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 农民起义军由弱小变强大,转败为胜推翻明王朝统治、抗击清军南下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起义军
姚雪垠 · 著 -
杜甫传
《杜甫传》杜甫传在线阅读;作者:还珠楼主
还珠楼主 · 著 -
和珅·帝王心腹
《和珅·帝王心腹》和珅·帝王心腹在线阅读
李师江 · 著 -
帝王师・刘伯温
《帝王师・刘伯温》帝王师・刘伯温在线阅读;作者:度阴山
度阴山 · 著 -
李煜
《李煜》南唐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又最奢靡、最血腥又最文雅的时代,后主李煜在政治上偏安懦弱,历来被史家贬为奢靡误国的“亡国之君”,《中国历代文人长篇传记小说之李煜》从文人的角度来剖析后主的一生,推翻史家的论调,丝丝入扣地点评出后主仁爱、细腻、宽厚、唯美的文化品格。南唐之亡,非亡于奢靡,而是亡于文人与政治的对决
刘小川 · 著 -
左宗棠发迹史
《左宗棠发迹史》左宗棠发迹史在线阅读;作者:汪衍振
汪衍振 · 著 -
林肯传记
《林肯传记》林肯传记在线阅读,欢迎大家免费阅读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 著 -
屈原传
《屈原传》屈原传在线阅读
王健强 · 著 -
老子传
《老子传》老子传在线阅读
余世存 · 著 -
被埋没的天才
《被埋没的天才》被埋没的天才在线阅读,被埋没的天才txt电子书阅读
玛格丽特・切尼(美) · 著 -
荀子传
《荀子传》荀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本书写出思想家的思想深度、历史地位和人格精神,又能将史料与生活相融合,既要历史真实,又要活的灵魂;让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活脱脱的站立在读者面前。
刘志轩、刘如心 · 著 -
管子传
《管子传》管子传在线阅读;管子(公元前725-645),名仲,我国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
高连欣 · 著 -
庄子传
《庄子传》庄子传在线阅读
王新民 · 著 -
徐志摩传
《徐志摩传》本书采用别致的纪传体手法,围绕徐志摩短暂而丰富的一生,细加考究、多有新解。叙述真实而全面,史料考订颇有收获,既真切记录了徐志摩生命中的留学生涯、文学活动,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诗人,更对徐志摩一生中重要的情路历程秉笔直书,写尽了张幼仪的质朴而深沉的爱、陆小曼热烈而洒脱的情,亦不讳言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漠视与
韩石山 ·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