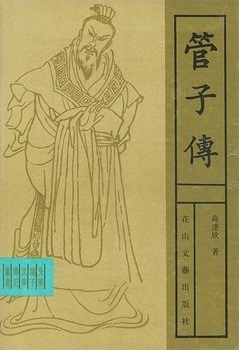第七章 孤军奋斗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 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 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 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 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 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 擦着。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 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 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 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 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 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 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这个孀妇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追述比埃尔的一生,很克制地悼惜他那不幸的死。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 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 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 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 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 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 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 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陰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有人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玷辱她近年来显扬了的辉煌名姓;虽然她的生活很严肃,很谨慎,而且近几年来特别可怜。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 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 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自从1905年***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 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 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这是她一生中觉得没有力气作任何事情的期间,而就在这个时候,两种不相符的使命在折磨着玛丽。
思归的心情使她犹疑许久,最后还是写了一封辞谢的信寄往华沙,她心里多么痛苦啊!她仍然答应在远处领导这个新实验室,并且把它交给两个最好的助手去实地管理:波兰人达尼什和卫丹斯坦因。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居里夫人的健康逐渐好转。到1913年夏天,玛丽背着背囊徒步游历昂加地纳,想借此试验自己的体力。她的女儿和她们的保姆陪着她,这一组旅行者中还 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天才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有时候讲法语, 有时候讲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理论。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作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稍后一点,那个爱说话的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是欧洲极少数能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伊雷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一些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上了一个极峰,而没有注 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夫人,你明白我须要知道的是,当一个升降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这样一个动人的忧虑,使那些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哄然大笑;他们一点没有猜想到这种想象升降梯坠落,含有“相对论”上一些高深的问题!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 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 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罗大夫同副校长李亚尔彼此达成谅解,解决了争论。大学和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各出40万金法郎创设一个镭研究院;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 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的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查教授领导,专研究癌瘤治疗方法。这两个孪生的研 究机构彼此合作,发展镭学。
玛丽现在常从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在那里拟定计划并且与工程师讨论。这个头发斑白的妇人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当然想着她个人的工 作,但是她尤其愿意建筑一个可以用30年、50年的实验室,愿意这个实验室在她化为灰尘之后可以用好多年。她要求宽大的屋子,要求能使研究室充满陽光的大窗户;她还要一个升降梯,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会使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如何气恼她要自己栽种蔷薇,挥动着铲子,用双手在没有盖成的墙脚下堆土,她每天浇水。当她立起身来站在风里的时候,她似乎是在看着那些无生气的石头和有生命的树木一起长高。
她继续在居维埃路工作,有一天早晨,她旧日的实验工友伯弟来找她。这个淳朴的人很难过,因为理化学校也在建筑工作室和梯形教室,而那个棚屋----比埃尔和玛丽的简陋潮湿的木板屋,将要在拆房人的鹤嘴锄下毁平了。
玛丽同这个地位很低的旧日朋友,一起到了娄蒙路,向那个棚屋最后道别。这个棚屋还在那里,一点没有动。黑板上还有比埃尔写的几行字,因为人们对这些字迹怀着虔敬的关切,所以没有人去碰它。似乎那个门就要打开,就要有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进来似的。
娄蒙路、居维埃路、比埃尔居里路三个地址,三个时期。玛丽自己没有觉得,她在这一天里已把她那美好而又艰辛的学者生活的道路又经历了一回。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N.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这个女英雄获得这个胜利的时候,已经既不年轻,也不康健,而且还已经失掉了家庭幸福。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她的周围有新设备,有热心的研究者准备同她一起奋斗!不,这不算太晚!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比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前途的庙宇”终于在那个不平常的七月里落成了。现在只等着它的镭、它的工作者和它的领导人。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这个波兰女子忘记了法国不过是她的第二祖国,这个作母亲的人不想去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这个虚弱有病的人轻视她的疾病,而这个学者准备把她自己的研究工作留到比较太平的时候再做。玛丽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在战争这可怕的变故中,她又表现了她的预感和主动精神。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 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德***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她这样不无虚伪地推论着,给指导她的本能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个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在本能上不喜欢逃避行动,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她决不让得胜的敌人走进无人照料的居里实验室而自鸣得意。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虽然玛丽能够从容地考虑住在被包围、被轰炸甚至于被占领的巴黎生活,然而有一件宝物----实验室所拥有的那一克镭却要她加以保护,不让侵略者侵占。
她不敢把这一点珍贵的东西交给任何使者,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去。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更新至 · 第八章 晚年的辉煌
2024-09-25网友评论
“(法〕艾夫﹒居里”相关作品
-
罗斯福传记
《罗斯福传记》罗斯福,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残疾人总统,四次当选,任职长达13年。他是一个精明的统治者,在驾驭政府与时代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胆略和才能,由于他在内政方面的伟大建树和在与法西斯斗争中的不朽功绩,而被世人公认为同华盛顿、林肯相比肩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康拉德・布莱克 · 著 -
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在线阅读
阿道夫.希特勒 · 著 -
肯尼迪传
《肯尼迪传》《肯尼迪传》在线阅读,西奥多・索伦森
西奥多・索伦森 · 著 -
彼得大帝传略
《彼得大帝传略》彼得大帝传略 在线阅读,帕普连科
帕普连科 · 著 -
渴望生活梵高传
《渴望生活梵高传》《渴望生活梵高传》是(美)欧文・斯通编著的一本书籍。《渴望生活――梵高传》是其年仅二十六岁时的作品。欧文・斯通认为,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名人深厚的 成就和辉煌,而是他们追求和探索的过程。七十余年来,梵高悲惨而成就辉煌的人生震撼无数读者。这部作品也成为欧文・斯通的成名作,被译成八十余种文字,发 行数千万
(美)欧文・斯通 · 著 -
【忏悔录】卢梭自传
《【忏悔录】卢梭自传》【忏悔录】卢梭自传在线阅读
卢梭 · 著 -
司马懿大传
《司马懿大传》司马懿大传,在线阅读
马敏学 · 著 -
王安石传
《王安石传》王安石传在线阅读
梁启超 · 著 -
武则天正传
《武则天正传》林语堂《武则天正传》:武则天这个女人活了八十二岁,权倾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生活对她而言就如同游戏一样,她有比普通人更强烈的欲望,以至于秽闻不断。
林语堂 · 著 -
成吉思汗传
《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传,在线阅读
勒内・格鲁塞 · 著 -
汉武帝传
《汉武帝传》汉武帝传,在线阅读
石静 · 著 -
华盛顿传
《华盛顿传》华盛顿传记在线阅读
华盛顿・欧文 · 著 -
朱元璋传
《朱元璋传》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皇帝中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
吴晗 · 著 -
魏阉全传
《魏阉全传》魏阉全传,在线阅读
魏忠贤 · 著 -
富兰克林自传
《富兰克林自传》富兰克林自传在线阅读
本杰明・富兰克林 · 著 -
叶赛宁传
《叶赛宁传》叶赛宁传在线阅读
南平编著 · 著 -
谋圣张良
《谋圣张良》谋圣张良,在线阅读
张毅 · 著 -
狄青传
《狄青传》狄青传在线阅读
许慕羲 · 著 -
俾斯麦传记
《俾斯麦传记》俾斯麦传记在线阅读;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俾斯麦传记 。激励人心的奋斗传奇、惊心动魄的政坛谋略、波澜壮阔的统一历程 。10年统一德意志,政治强人一手缔造世界强国 。
艾伦・帕麦尔 · 著 -
刘邦大传
《刘邦大传》刘邦大传在线阅读
陈文德 · 著 -
胡雪岩全传
《胡雪岩全传》胡雪岩全传,在线阅读
林学武 · 著 -
张居正大传
《张居正大传》《张居正大传》介绍了张居正是明朝中期的重臣,他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本书讲述了传主如何从一个普通人直至位极人臣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纷繁芜杂的官场斗争。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对传主所置身的时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亦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
朱东润 · 著 -
毕加索传
《毕加索传》毕加索传在线阅读
毕加索 · 著 -
秦始皇大传
《秦始皇大传》秦始皇大传,在线阅读,人物传记
江柳人 · 著 -
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李鸿章传》在线阅读
梁启超 · 著 -
曼德拉传
《曼德拉传》《曼德拉传》,名人传,曼德拉传奇 《曼德拉传》在线阅读
[美]查伦•史密斯 · 著 -
甘地传
《甘地传》《甘地传》在线阅读;甘地,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
米歇尔.尼科尔森 · 著 -
巴顿传
《巴顿传》巴顿将军传,巴顿传,《巴顿传》在线阅读
巴顿 · 著 -
艾森豪威尔传
《艾森豪威尔传》艾森豪威尔传,艾森豪威尔简介,名著《艾森豪威尔传》
斯蒂芬・安布罗斯 · 著 -
林徽因传
《林徽因传》《林徽因传》不仅仅写出了林徽因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子,有着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积极的人生启示。
张清平 · 著 -
隆美尔传
《隆美尔传》《隆美尔传》在线阅读
隆美尔传 · 著 -
德川家康传
《德川家康传》《德川家康》洋洋五百五十万言,将日本战国中后期织田信长、武田信玄、德川家康、丰臣秀 吉等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德川家康最终脱颖而出,结束战国烽烟,开启三百年太平盛世。作品展现了德川家康作为乱世终 结者和盛世开创者丰满、曲折、传奇的一生,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与
一条瑜 · 著 -
慈禧后私生活实录
《慈禧后私生活实录》《慈禧后私生活实录》
德龄 · 著 -
西施艳史演义
《西施艳史演义》《西施艳史演义》在线阅读
佚名 · 著 -
李小龙传
《李小龙传》《李小龙传》
崧灵 · 著 -
心学大师王阳明大传
《心学大师王阳明大传》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王阳明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士大夫之一,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本书,以文学笔调真实叙述了王阳明的一生:其“德行”及“事功”,并以现代理论与方法,阐述了王阳明的“言”即其思想,再现了王阳明的人格魅力。
周月亮 · 著 -
我的另一面
《我的另一面》我的另一面在线阅读;作者:西德尼・谢尔顿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
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
《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刘邦发迹史・神一样的无赖》在线阅读;作者:易水寒
易水寒 · 著 -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在线阅读;作者:朱可夫
朱可夫 · 著 -
诸葛亮传
《诸葛亮传》诸葛亮真有那么神奇吗?他真的算无遗策,用兵如神吗?诸葛亮的智慧又是从何处来的呢?答案尽在书中。
若虚 · 著 -
赵匡胤
《赵匡胤》《赵匡胤》传记书籍在线阅读;五代十国,神州血雨腥风,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望天悲问:大乱何时休?!国家何时大治?21岁的赵匡胤,辞别父母和妻子,离家闯荡,千里送京娘,受尽磨难。...
郭兆祥,李金水 · 著 -
居里夫人传
《居里夫人传》一书回顾了居里夫人这位影响过世界进程的伟大女性不平凡的一生,主要描述的是居里夫人的品质、她的工作精神、她的处事态度。作者艾芙·居里向读者详介了她 的母亲除了在科学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外,她还用自己一生为人处世的崇高行为给女儿树立榜样,对女儿的教育也有许多独特的做法。读完这部书,相信居里夫人对 困苦和灾
(法〕艾夫﹒居里 · 著 -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在线阅读
吕峥 · 著 -
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
《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在线阅读;作者:罗大伦
罗大伦 · 著 -
希特勒传
《希特勒传》《希特勒传》在线阅读
约翰・托兰 · 著 -
萨特传
《萨特传》萨特传在线阅读;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西蒙娜・德・波伏娃 · 著 -
李自成
《李自成》《李自成》, 姚雪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描写了距今300多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小说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 农民起义军由弱小变强大,转败为胜推翻明王朝统治、抗击清军南下为主要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再现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起义军
姚雪垠 · 著 -
杜甫传
《杜甫传》杜甫传在线阅读;作者:还珠楼主
还珠楼主 · 著 -
和珅·帝王心腹
《和珅·帝王心腹》和珅·帝王心腹在线阅读
李师江 · 著 -
帝王师・刘伯温
《帝王师・刘伯温》帝王师・刘伯温在线阅读;作者:度阴山
度阴山 · 著 -
李煜
《李煜》南唐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又最奢靡、最血腥又最文雅的时代,后主李煜在政治上偏安懦弱,历来被史家贬为奢靡误国的“亡国之君”,《中国历代文人长篇传记小说之李煜》从文人的角度来剖析后主的一生,推翻史家的论调,丝丝入扣地点评出后主仁爱、细腻、宽厚、唯美的文化品格。南唐之亡,非亡于奢靡,而是亡于文人与政治的对决
刘小川 · 著 -
左宗棠发迹史
《左宗棠发迹史》左宗棠发迹史在线阅读;作者:汪衍振
汪衍振 · 著 -
林肯传记
《林肯传记》林肯传记在线阅读,欢迎大家免费阅读
(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 著 -
屈原传
《屈原传》屈原传在线阅读
王健强 · 著 -
老子传
《老子传》老子传在线阅读
余世存 · 著 -
被埋没的天才
《被埋没的天才》被埋没的天才在线阅读,被埋没的天才txt电子书阅读
玛格丽特・切尼(美) · 著 -
荀子传
《荀子传》荀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本书写出思想家的思想深度、历史地位和人格精神,又能将史料与生活相融合,既要历史真实,又要活的灵魂;让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活脱脱的站立在读者面前。
刘志轩、刘如心 · 著 -
管子传
《管子传》管子传在线阅读;管子(公元前725-645),名仲,我国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
高连欣 · 著 -
庄子传
《庄子传》庄子传在线阅读
王新民 · 著 -
徐志摩传
《徐志摩传》本书采用别致的纪传体手法,围绕徐志摩短暂而丰富的一生,细加考究、多有新解。叙述真实而全面,史料考订颇有收获,既真切记录了徐志摩生命中的留学生涯、文学活动,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诗人,更对徐志摩一生中重要的情路历程秉笔直书,写尽了张幼仪的质朴而深沉的爱、陆小曼热烈而洒脱的情,亦不讳言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漠视与
韩石山 ·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