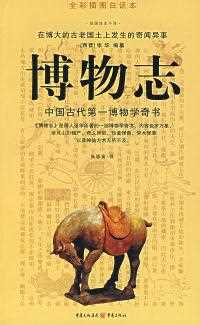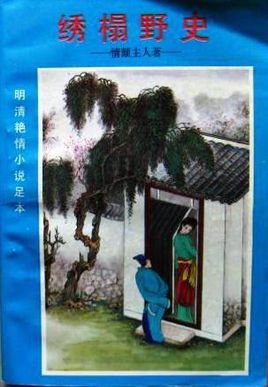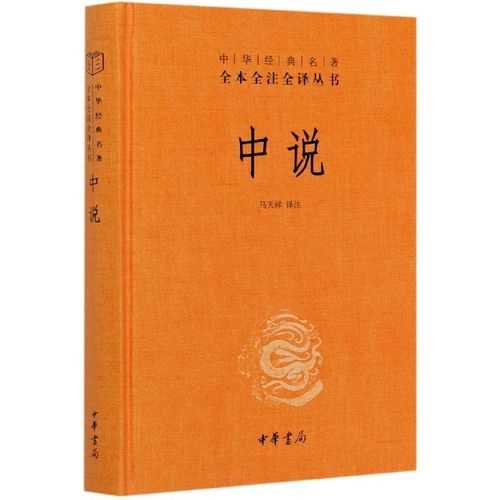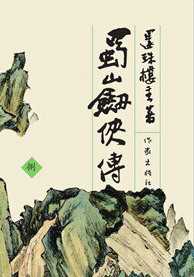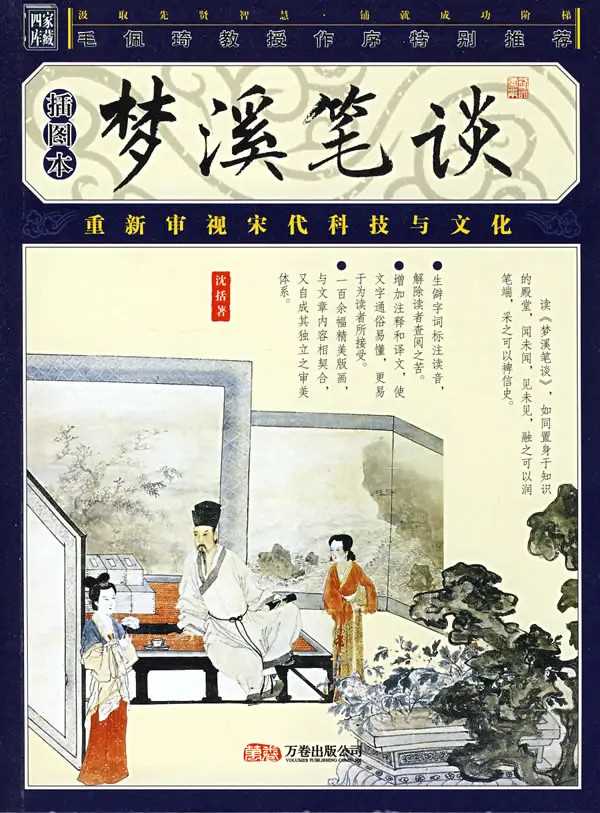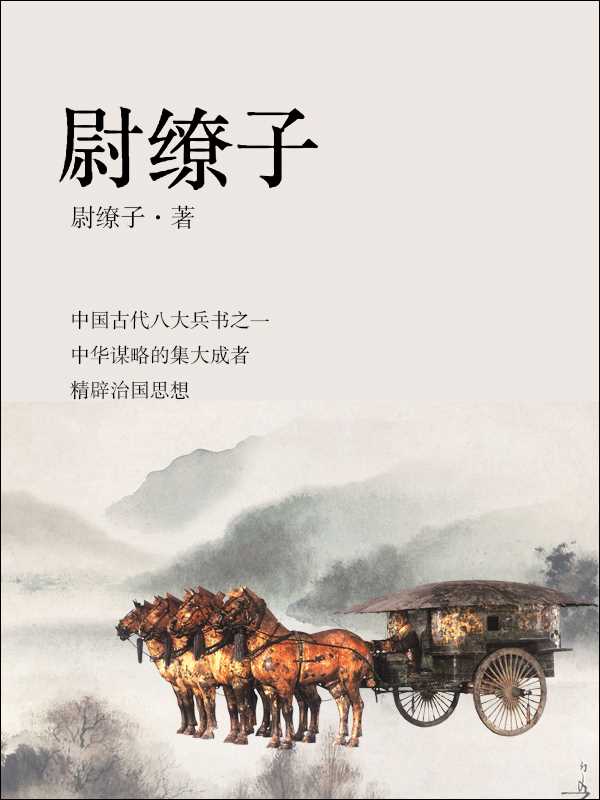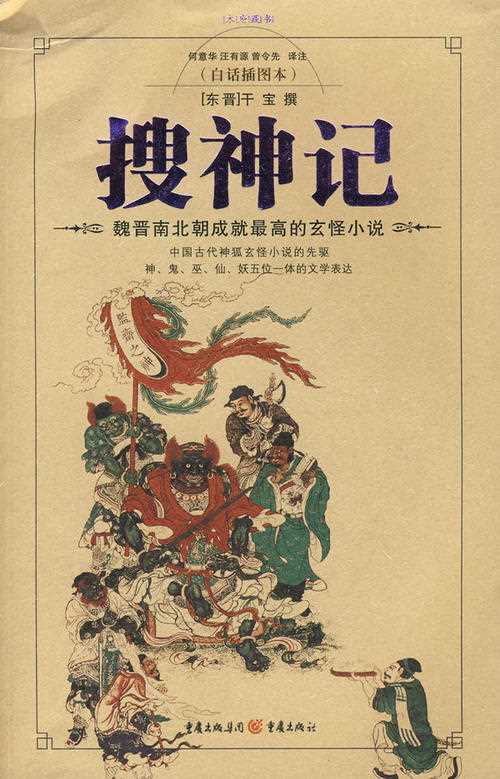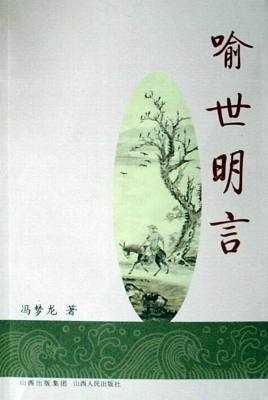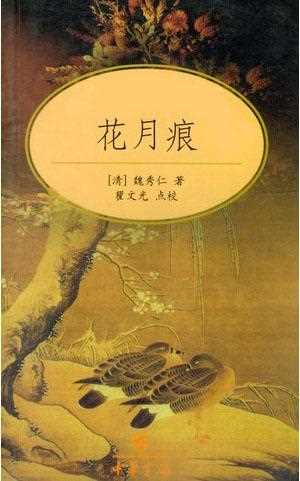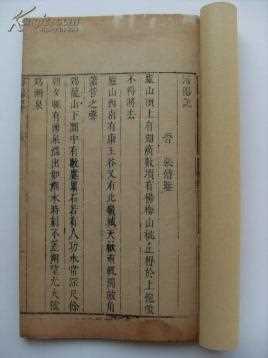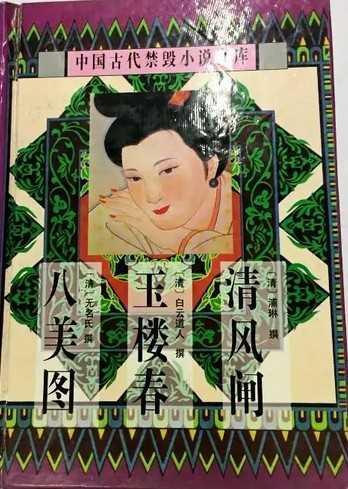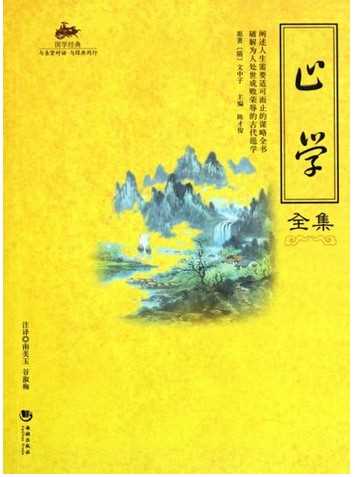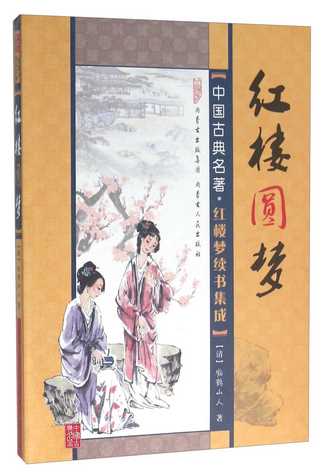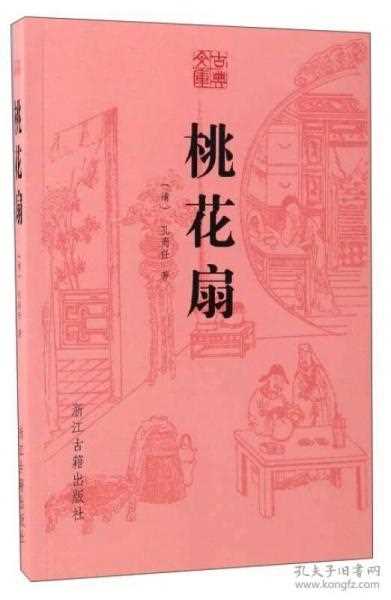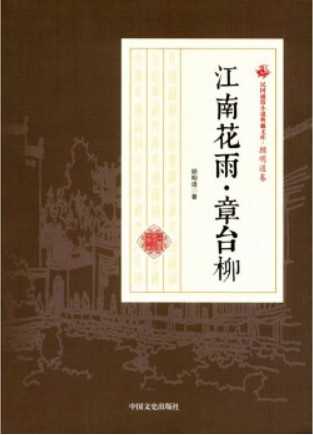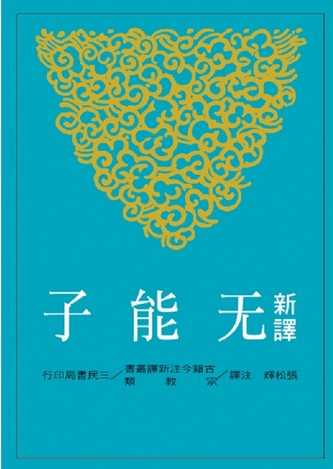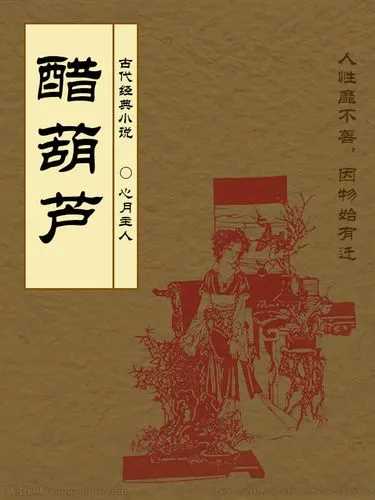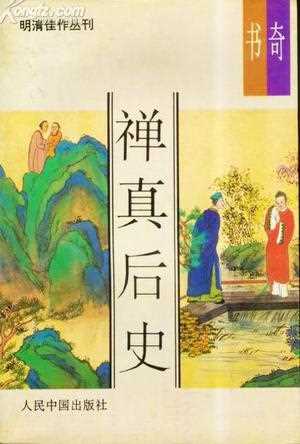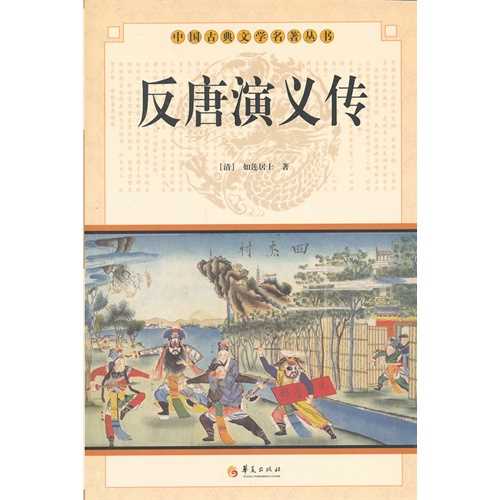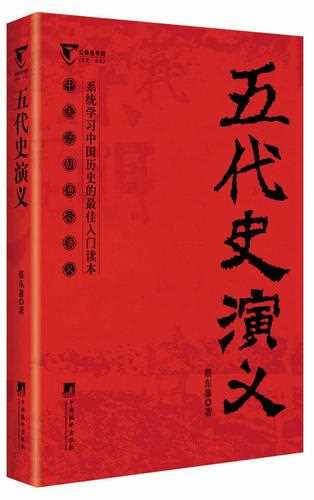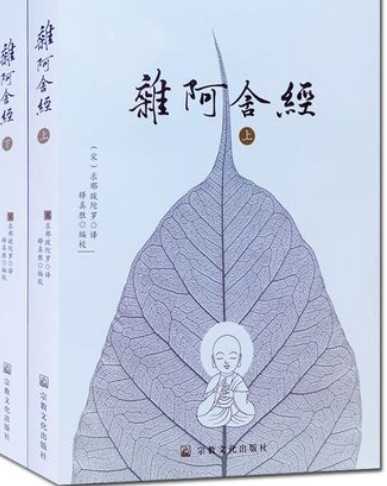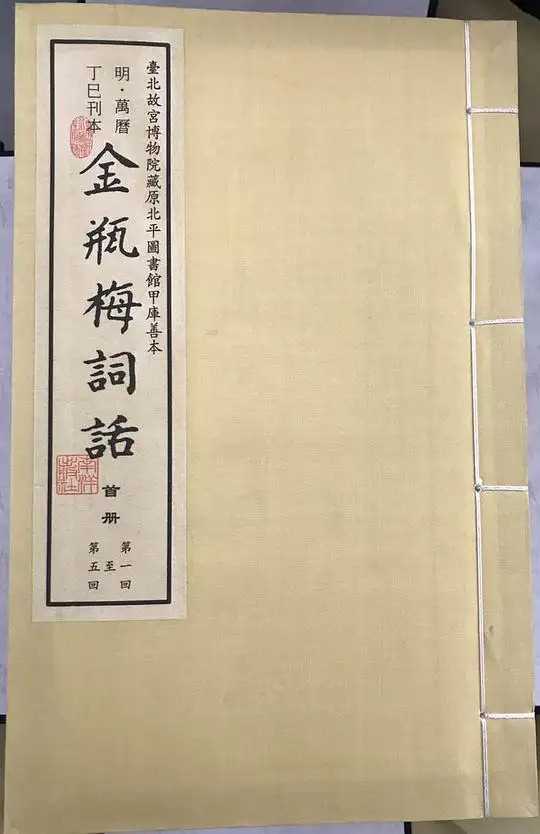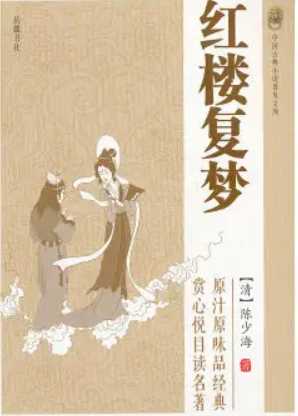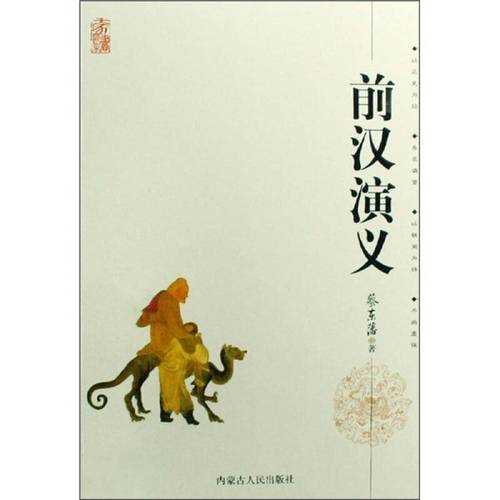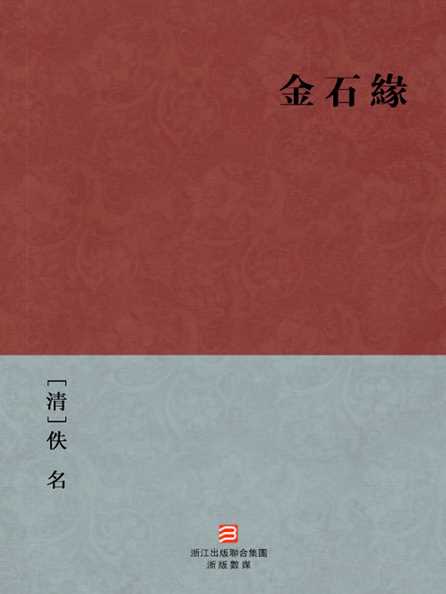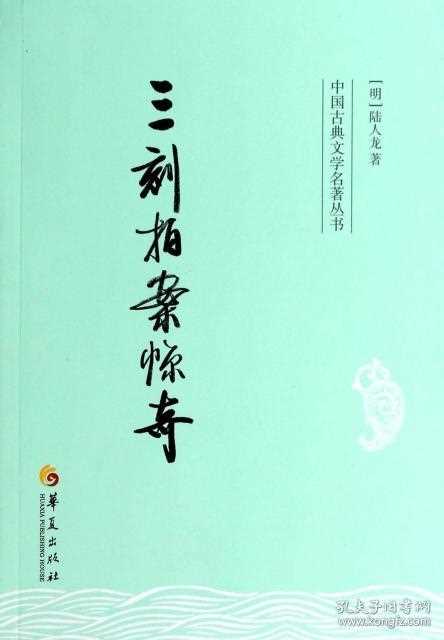话说宝玉因自己已是半老佳人,纵使丰韵犹存,恐不足动走马王孙之目,故尔改扮男装,借掩老态,究不能鸡皮三少,如古时的夏姬,不得不别出新裁,以冀取悦于人。昔太史公有云:“女为悦己者容。”可知妇人所重者,全在乎色,到了色衰之时,有谁怜惜?即千方百计想出种种的修饰,也不过遮一时耳目,安能恃此而不败?况来这句话还是指半老者而言,若真真头童齿豁,只怕愈修饰愈难看了。宝玉久历风尘,未尝不鉴及于此,眼前虽加意修饰,勉强与后辈争衡,然知非长久的计较,恐再阅数年,势必桃源洞口,无复有问津者矣。所以前岁由京返沪,怨白眼之相加,感青春之不再,便想退为房老,购求美貌的讨人,预备后日菟裘之计。只缘自己尚可勉持数载,以致延缓至今,倘一再蹉跎,非但财政困难,抑且惹人厌弃,岂不把昔日鼎鼎盛名尽行埋灭?倒不如急流勇退,使闻之者犹存思慕之心,方为上策。况我广蓄娇娃,独辟门户,与闭关自守不同,而我在从中主持调度,仍可与众客周旋晋接,不绝外交之路,外隐其名,内收其实,既不问谁毁谁誉,又可以自尊自大。待当财货充盈,我始风尘厌倦,择人而事,人必贪我而娶我,我尽可享老年之福。一举而三善俱备,我亦何乐而不为?且现有姨甥女月仙在此,色艺尚佳,再隔数载,实可与秀林伯仲,他年利市三倍,不难操券而得。
宝玉定了这个宗旨,使与阿金、阿珠细述一遍。阿金、阿珠均以为然,都说道:“大先生要做格件事体,只消倪到外势去放一个风,包格套小娘鱼,好格歹格,一个一个领得来拨看呀。”宝玉道:“奴算托仔唔笃格哉唔,笃一径放勒心浪仔介!”阿金道:“晓得。不过故歇大先生格牌子,阿要拿下来呢?”宝玉道:“眼下且得慢点看,管生意好勿好!等弄着仔讨人勒再说。”阿金道:“勿差勿差,作兴弄着两个讨人,面孔倒呒啥,弹唱一点勿会,如果学起来,笨格至少一年半年,聪明点格末,也要三个月工夫笃。”阿珠接嘴道:“我看上去,格件事体,总要开年春浪开办格哉,虽则还有七八个月,样样随要一浪弄起,哪哼来得及嗄?”宝玉道:“慢就慢点,只要事体弄得好,开年也勿要紧。”三人商酌方定,来了几位客人叙雀,遂把此事剪断。但非书中正文,毋须烦琐。
单说过了几天,阿金、阿珠分头出外,就将宝玉要讨人一事,或托亲戚,或托姊妹,一时传扬开去。自有那班做水贩的人,领着十几岁的小女儿,送至三马路来,请宝玉细细拣选。无如佳者十不得一,一连数天,看得宝玉厌烦起来,吩咐那班送来的人道:“唔笃要拣好格末送得来,奴价钱倒勿算格,大点也呒啥,格套邱货,哪哼会看得中呢?倒勿如免仔点罢。”那班人听了这几句话,果然数日不来,都向各处去搜求了。
忽一日,阿金有个亲戚,叫做周家姆,也是开过堂子的,现在虽已歇业,却有三四个讨人,只剩一个没有租出,年纪最小,正当学习弹唱之时,只因自己年老多病,所以闻得宝玉购买,肯出善价,特托阿金介绍,自愿割爱,将这小女儿带到宝玉那里。宝玉见了,甚为合意,因他品格清秀,态度轻盈,与月仙不相上下,问他多少岁数?弹唱可曾学过?他不待周家姆代言,自己便回答道:“奴今年十四岁哉,曲子学过仔两个月,会仔七八只,故歇倪先生还勒浪教奴勒呀。”宝玉听他口舌灵便,言语清澈,依稀小鸟依人,着实令人可喜,便回头问周家姆道:“格格小娘鱼倒还呒啥,阿是勒苏州买得来格介?”周家姆道:“俚轧实是荡口人,旧年冬里,俚格舅母(读姆)带上来卖拨我格,故歇因为我年纪老哉,管顾勿到,格落我想转卖脱俚呀。大先生如果看得中,真真俚格福气哉。”宝玉又问道:“周家姆,要几化身价,老老实实说末哉,不过十二分大,奴也出勿起格。”周家姆道:“大先生亦要客气哉,俚格身价,我旧年买下来格辰光,勿到三百块洋钿,后来为仔俚身浪,请先生教曲子,加二俚生仔一场病,倒甩脱仔几化洋钿笃,故歇大先生看得中末,身价随便末哉,我决勿争论格。”宝玉听他口气,大约至少要五六百元,但未讨定实价,怎好还他数目?
正要启口复问,见阿金走至房门跟首,向周家姆招了一招手,周家姆即便起身跟了出来。阿金低声说道:“倪大先生欢喜直爽格,问要几化身价,勿论大罢小罢,尽管老实说,勿要紧格。再勿然末,对我说仔轧实价钱,让我传言拨倪大先生,省得吞吞吐吐哉,想阿好?”周家姆道:“勿是啥我吞吞吐吐,我皆为自家本钱大仔点落,勿好意思讨实足价钱,照我格心里末,勿瞒金姐说,加点虚头要讨一千,起码盘子,至少七百块洋钿,再少要蚀本格哉。也晓得我格,我勿为自家年纪老仔点,我落里舍(读晒)得卖脱俚嗄?”阿金点点头,说道:“请外头坐歇,让我进去搭大先生说仔,回覆哇。”说着,便至里边与宝玉一说,宝玉早已定见,即吩咐如此如此。阿金方出外,回覆周家姆道:“倪大先生说格,讨格价钱忒大,顶多出足五百块洋钿,是格末是,周家姆,且得自家想想看末哉。”周家姆听了,心中虽然肯卖,却未便骤然答应,故意硬托阿金传言,再要略为加些。阿金因他是亲,只得走了一埭,添了几句好话,始说不要他一钱浮费,净到手五百大洋,周家姆也就应允,立即央人来写了一张卖身绝契,画了花押,宝玉当场兑出五百元交割,周家姆欣然领洋而去,不提。仍说宝玉又另出五十元谢了阿金中人,方与这个小女儿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胡玉莲。本来学过京调小曲,此刻仍叫他从师习练,更比月仙容易,虽喉音不及月仙,而妩媚之态,将来实可步宝玉后尘,因此宝玉十分爱惜,从未以老鸨手段施之于玉莲。
话休烦琐。次日,阿珠的结拜姊妹同着一个老妪、一个女儿,来托阿珠引见。宝玉看这女儿,年纪与玉莲仿佛,面容丰满,体态端凝,心中已甚爱悦,便问他要多少身价?这女儿是老妪甚人?那老妪答道:“这是我的孙女,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单单生下这一个。实因苦度不过,所以弄他出来的。若说身价,并不计较,最好以后与他往来,未知大先生可肯应允吗?”宝玉听他口音,不是苏州,又怜他年纪已老,无靠无依,因说道:“既然实梗,就登勒俚仔,做做粗事体也呒啥,奴照例出还工钱,不过要一个保人,只算格孙囡鱼押拨奴格,奴拨一百五十块洋钿,愿勒勿愿,随便末哉。”那老妪听说有了钱,又有饭吃,那有不愿之理?当场就唯唯答应。即托阿珠的结拜姊妹,做了保头,写了押契,兑了银钱,保头与中人都有好处到手。恕不一一细叙,以免烦杂。是时保头已去。宝玉因这女儿是押下来的,不改他的姓,只替他取个名字,叫做左芸台,与胡玉莲珠联璧合,燕瘦环肥,并皆佳妙。宝玉自得了这几株摇钱树,异常快活,专等他们技艺成就,工夫纯熟,便可大开曲院,以遂奢愿。但现仍挂着自己牌子,唤他们在房学习应酬,间或代出堂差,使知侑酒规模。从此宝玉优游自适,除训女外一无所事。
阅过了春花秋月,又届隆冬。因明春准备开办,不得不未雨绸缪,将应用东西逐渐购置。好在此间房屋也是六楼六底、走马洋台,与间壁原住处相同,足够敷用,不须另行搬场,省却许多跋涉。瞬息间残腊催归,新春报到,桃符换旧,梅蕊生香。宝玉早将商标摘下,所以交了新年,别无应酬繁文,十分清静,惟与阿金等计划开张一事,又添买了各房摆设器具,此外均已齐备,不必细述。是时宝玉隐姓埋名,韬光匿迹,虽际此良辰美景,并不驾车出游,招摇于十里洋场,以致一班旧好新知,只道他又往别处去了,怎知他暗地经营,为特别改良之计。
不说众客猜疑。单讲宝玉那天,阿金问起玉莲等商标用何花样?宝玉道:“只要拣时式点就是哉,奴想在外再做一块堂名牌子,以为阿好格?”阿金道:“蛮好,取啥格堂名佬?想定当仔,写俚出来,好马上拿得去一淘做。”旁边阿珠插嘴道:“大先生要取堂名,我倒瞎想着几个勒里,勿知阿好用格?”宝玉道:“且说拨奴听听看。”阿珠道:“故歇倪三个小先生挂牌,蛮好叫三仙堂、三雅堂、三庆堂哉。”宝玉摇头道:“切是切格,倒是脱熟落勿好。唔笃才响,让奴一干子想想看。”说着,皱了一皱眉头,忽然自笑道:“奴哪哼一径勒心浪格,故歇就会忘记?真真有点专哉,上海格大富翁,让还胡雪岩第一,俚格堂名叫‘庆余堂’,奴搭俚五百年前共一家,也好叫‘庆余堂’格。奴能够将来搭俚实梗有铜钿,开堂子当中,亦推尊奴独步,难末大杀胜会得来。”阿金赞道:“出色出色,只有大先生想得出,下埭能够搭俚一样,连倪才要发财哉。横势现在俚倒仔帐,已经死格哉,倪用‘庆余堂’三个字,别人决勿批评格,我想就拿去做哉。”
这几句话,阿金说得高兴,其实狠不吉利,宝玉并没有听出来,连连点首。阿珠却默然不语,辨出言中滋味,甚不佳妙,恐宝玉将来也是这个样儿,没有好好的收成结果。可见万事前定,预露先机,虽由宝玉自取,而一败涂地,总是一般。阿珠未便说出,致扫宝玉之兴,故尔缄口不言,独自出房去了。宝玉只道不用他所取堂名,因此心中不快,其实何尝为是,未免意会错了,口中却并不说他,单取历本过来一看,拣定念四吉日开张。少停告诉了阿金、阿珠,屈指相离尚有十天,交代预先几日,仍须照着旧规,到各处邀请客人。但这都是一班旧识,究属不多,不足以夸耀于春申江上,因唤近来新用的几个大姐、娘姨,系伏侍玉莲等三位小先生的,也嘱他们四面张罗,以期多多益善。
众人领命,逐日分头请客,足足忙到念一,方才停止。所请各客,虽闻宝玉退老林泉,别开蹊径,然在他面上,不得不前来报效。此外,一众新相识听得宝玉兴此盛举,莫不欲一扩眼界,遍赏群花,故应允当日摆酒的,或单台,或双台,计有十余台之多,预先定下。宝玉无限喜悦,到了念四那天,一早起身,因自己既做房老,并不十分打扮,单看玉莲、芸台、月仙等梳妆。一个个粉妆玉琢,等候接待众客。其时三人的商标与那“庆余堂”的金字牌子均已挂在门前,牌上都披着红绸,插着金花,甚是灿烂夺目。楼下天井里面摆着全新的灯担堂名,堂中一样挂灯结彩,仿佛人家有喜庆等事,陈设得金碧辉煌。所有前楼后楼各房间,除前楼上做了胡玉莲、左芸台的房,后楼上宝玉仍在左边一间,右首一间让月仙做了房,每间均隔为二,这是堂子中千篇一例的,毋容细表。
楼下各房,皆系待客的所在,凡遇生意茂盛,各人房中僭满,则后来之客,只好有屈在此摆酒的了。按此段“大开庆余堂”,是胡宝玉的一生大关目,故在下不能不描写一番,阅者幸勿以繁碎目之。午餐以后,诸客陆续驾临,大半是近时熟客,若一一志出姓名,非惟令人讨厌,抑且画蛇添足了。因最以前集中所载各客,早已风流云散,即内中尚有几人,而于事无关,亦何必屈指细数呢?况迎来送往,俗妓之常情;弃旧怜新,淫娼之故态,倒不如直截痛快,混称之曰众客,剪去许多葛藤枝节的好。
在下数言表过,仍说正文。下午众客渐集,仍是宝玉领头,带着玉莲等出来招接。客人各随所好,或在玉莲处碰和,或在芸台处叙雀,或在月仙那边就坐,惟几个至熟的,依旧在宝玉房中聚谈。迨至上灯过后,楼上前后大小各房皆满,即下面也有客人坐了。宝玉同玉莲等三人上下周旋,十分忙碌。少顷各房摆席,纷召群芳,但听猜拳行令之声,与弹丝弄竹之音相和,喧阗达于户外,洵足极一时之盛。怎见得?有一篇短赞为证:
楼开卖笑,洞辟迷香。
翠翠红红作伴,莺莺燕燕成俦。
一个如玉树临风歌白雪,莲花出水映丹霞;
一个如芸兰雅得诗书味,台榭新翻歌舞名;
一个如月姊多情离桂阙,仙人何处认桃源。
这边厢飞花行令,那边厢侑酒当歌。
侍者装烟,笑声吃吃;
先生把盏,情致绵绵。
上下楼管弦杂奏,依稀乐献东山;
前后房水陆纷陈,仿佛樽开北海。
今夕庆余堂上,极尽繁华;
他年黄歇滩头,空留韵事。
正是:
许多风月平章客,齐入烟花寨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