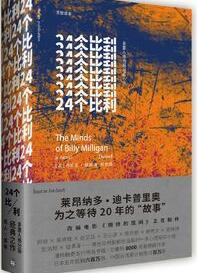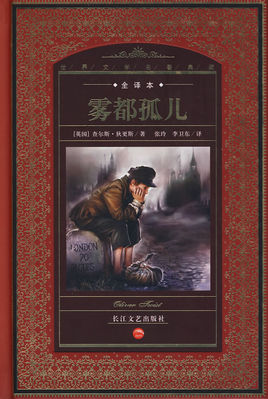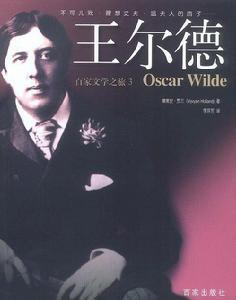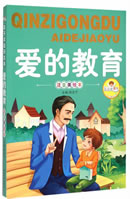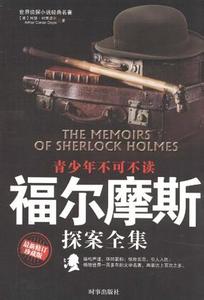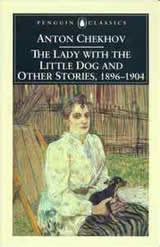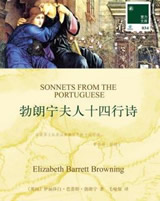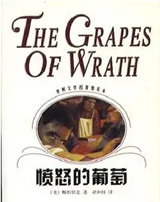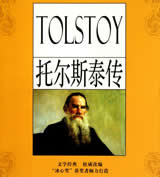第七章 向西部前进
第二天一大早,全家人又坐上了篷车。因为篷车的东西全都没搬下来,所以他们说走就走。
整个营区里,只剩下杜西亚姑姑的小屋孤零零地矗一立在那儿。草地上光秃秃的,测量人员站在已被拆除的棚屋的旧址上,忙着测量和打桩,准备在这儿建一个新城镇。
“等海依那边的工程安排妥当了,我们马上过去。”杜西亚姑姑说。
“我们在银湖见!”琳娜大声对劳拉说。爸冲着马吆喝了一声,篷车开始摇晃起来。
明媚的一陽一光照在没有拉上篷顶的篷车上,凉 风阵阵,沁人心脾。里随处可见人们在忙着干活儿,时不时有一两辆篷车从身边经过。
不久,道路向一块起伏的坡地斜伸下去。爸说:“前面就是大苏河。”
劳拉开始给玛丽栩栩如生讲述她看到的情景:“顺着这条路往下走,就是低矮的河岸,不过,河岸上一棵树也没有。只有广阔的天空,辽阔的草地,狭窄的浅浅的溪流。它本来是一条大河,不过,现在河水干了,变得就和梅溪差不多大小了。涓一涓细流穿过一个又一个水塘,流过干涸的布满沙砾的地面,经过龟裂的泥土地。现在,马要停下来喝水啦。”
“使劲儿喝吧,想喝多少就喝多少。”爸对一妈一说,“前面五十公里都喝不上水啦!”
在这条浅浅的小河的另一边,草地变得越发低矮了,像一道弧线弯了下来,一道弧线接着一道弧线,一道比一道更低,看起来就像一个短短的钩子。
“这条路一直向着草地延伸,在前方突然就不见啦,大概这就是路的尽头。”劳拉说。
“不会啊,”玛丽反对说,“这条路应该一直通往银湖才对。”
“我知道。”劳拉回答说。
“好啦,我觉得你不该那样讲,”玛丽一温一和地说,“我们在遣词造句上应该尽量做到准确,力争做到把表达的内容讲清楚。”
“我说的就是我想要表达的啊!”劳拉挺不服气地说。观察事物有多种方法,同样,描述事物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啊。
过了大苏河,再也看不见田野,看不见房屋,也看不见人烟。道路中断了,铁路的路基也不见了,一辆辆篷车经过时压出来的车辙隐约可见。劳拉看见无数个小木桩淹没在草丛中。爸说那是测量人员打下的木桩,专用来标记还 没有开工修建的铁路路基。
劳拉告诉玛丽:“这片草原就像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牧场,它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一直延伸到天边。”
天空万里无云,草一浪一翻滚,碧波荡漾,这种景象让劳拉觉得有些奇怪。不过,究竟是一种什么感受,她也说不清楚。这里的一切,包括坐在篷车上的她们、篷车、马匹、甚至连爸,看上去都是那么渺小。
整个上午,爸一直驾着篷车沿着模糊不清的车辙行进,沿途的景色单调乏味。他们越往西部挺一进,似乎就变得越渺小,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尽头。风呼一呼地吹着,掀起无边无际的草一浪一。马蹄和车轮发出一成不变的咯吱声,篷车坐板一直不停地颠来颠去,颠得人心慌意乱。劳拉心想:他们也许会沿着这个永远一成不变的地方一直走下去,而这个地方,压根儿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光临。
只有太一陽一在移动。它静悄悄地缓缓爬上天空。当太一陽一升上头顶,他们停了下来,给马喂食,在干净的草地上吃着野餐。
连续坐了一上午的车,现在坐下来歇一歇实在是太舒服啦。劳拉回想起他们过去从威斯 康星到印第安保留区,又往回走到明尼苏达的旅途中,不知有多少次露天就餐的情景。现在他们是在达科他州,要向更西边的地方前进。不过这次的旅程和以前不一样。区别不仅仅在于这次的篷车没装上车篷,车上没有一床一铺,还 有其他的原因。至于是什么原因嘛,劳拉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来,不过,她始终觉得这片草原就是非同一般。
“爸,”她问,“你以后找着一块放领地,它会和我们在印第安保留区的一模一样吗?”
爸想了想回答说:“不,这个地方可不一样。我也说不清它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草原的确就有所不同。总之,这地方就是不一样!”
“这有可能啊。”一妈一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现在在明尼苏达的西边,印第安保留区的北边,花花草草这些当然有所不同。”
不过,劳拉和爸并不是这个意思。花花草草实际上并没多大区别,这儿真的具有一种独特之处。那是一种巨大的宁静,能让你整个人沉静下来。你越是心平气和、气定神闲,越能感到这漫无边际的宁静包裹一着你,让你无处可逃。
风轻轻地吹动青草的声音,马的嘶鸣声,以及它们在篷车背后的饲料槽吃东西发出的刷刷声,还 有劳拉他们吃午餐发出的声音,甚至他们的高谈阔论都无法打破这无边无际的宁静。
爸谈到了他的新工作。他将成为公司的一名店员,同时还 是银湖营区的管理员。他要负责照看店铺,登记工人们究竟干了多少活儿,还 要清楚每个工人在扣除住宿餐饮费和在店里购物所欠下的债外,可以拿到多少工资。等每个月出纳员把钱送来,爸就会把工资发到每位工人手中。这就是他即将从事的工作,爸为此每个月可以挣五十元。
“最令人高兴的是,卡洛琳,我们是最先到这儿来的一批人!”爸说,“我们可以选择一块放领地。天哪,我们终于时来运转啦!在新的土地上,我们拥有优先选择权,而且在整个里,每个月还 可以赚上五十元!”
“这听起来的确很棒,查尔斯 。”一妈一说。
然而,对于寂静的草原来说,他们的谈话一点儿也没意义。
整个下午,他们马不停蹄地走啊,走啊,走了一公里又一公里,一路上荒无人烟,唯有天空和野草。他们走的那条小路,也不得不靠被篷车碾过的草丛来辨认。
劳拉看见昔日印第安人和野牛走出来的小路,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地面,现在已是杂草丛生。她看见奇形怪状的大洼地,四周笔直,底部也很平坦,那曾经是野牛打滚的泥塘,现在也长满了杂草。劳拉从来没见过野牛,爸说她以后很难看见野牛了。就在不久前,这儿还 有上千头野牛,它们属于印第安人所有,现在却被白人斩尽杀绝了。
无边无际的草原一直延伸到了遥远澄静的天边。风呼一呼地吹着,一刻也不停歇,被太一陽一晒成黄褐色的茂密野草随风摇摆。这天下午,爸驾着篷车一直往前行进,他快乐地吹着口哨,唱起了歌谣。他常常唱起的歌谣是:
噢,快来这个地方,
别害怕也别紧张,
山姆大叔富甲一方,
可以给每人一座农庄!
就连小宝宝格丽丝也跟着咿咿呀呀唱起来,尽管她吐词并不清楚。
噢,来哟,快来哟,
快快来到这个地方,
噢,来哟,快来哟,
别再犹豫也别彷徨,
噢,来哟,快来哟,
不要担心有什么损伤,
山姆大叔富甲一方,
可以给每人一座农庄!
太一陽一渐渐西沉。这时候,草原上,有一个骑马的人出现在篷车后面。他跟在他们身后,不紧不慢地走着,跟了一里又一里,渐渐地靠近他们,一直到太一陽一沉落下去。
“离银湖还 有多远呢,查尔斯 ?”一妈一问道。
“大概还 有十五公里。”爸说。
“附近没有人家,是吗?”
“是的。”爸回答道。
她不再说话。大家都默不作声。他们忍不住不断地回过头去看看后面那个骑马的人,每当他们回头去看他的时候,就越发感觉他离他们近了一些。他一定是有意跟在他们后面,在太一陽一完全落下去之前,他并不想赶在他们前面去。夕一陽一西下,草原上浅浅的凹坑布满了一陰一影。
爸每次回过头看看那个人,便小心翼翼地抖了抖缰绳,让马儿跑快一点儿。可是马儿拖着载得满满当当的篷车,行走的速度怎能与一个人骑着一匹马相提并论呢。
那个人离他们已经非常近了,劳拉可以看见他腰侧的皮槍套里插着两支手槍。他的帽檐拉得低低的,遮住了双眼,脖子上松松地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巾。
爸来西部的时候带着槍,可现在槍却不在篷车上。劳拉不知道 槍 放在哪儿,又不好问爸。
她又回头看了看,突然看见另外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跟了上来。那个人穿着一件红衬衫,骑着白马远远地跟在后面,看上去十分小,不过他气势汹汹,飞一般的追上来。他赶上了前面那个人,两人一道追了上来。
一妈一压低声音说:“现在后面跟着两个人啊,查尔斯 。”
玛丽胆战心惊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劳拉,出什么事了?”
爸飞快地转过身看了看后面,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现在不用担心啦,”他说,“跟来的是杰瑞老大。”
“杰瑞老大是谁啊?”
“他是一个混血儿,有一半法国人的血统,还 有一半印第安人的血统。”爸若无其事地解释说,“他是一个赌徒,还 有人说他是个盗马贼,但他是一个好人。杰瑞老大绝不会让任何人来抢劫我们的。”
一妈一吃惊地看了看爸,张开嘴巴想说点什么,可紧接着又闭上了嘴。
那两个骑马的人跑到篷车旁。爸招了招手说:“嗨,杰瑞老大!”
“嗨,英格斯 !”杰瑞老大向爸招呼道。他身旁的那个人凶巴巴地扫视了他们一眼,然后便策马往前奔去。杰瑞老大则骑着马跟着篷车一块儿向前走。
他看起来真像一个印第安人。个子高大,身材魁梧,但一点儿也不显胖,棕色的脸庞瘦瘦的。身上穿着的红衬衫红得像一一团一火。他没戴帽子,直直的黑发在扁平的、颧骨高高突起的脸上不停地晃动。他那匹雪白的马既没有马鞍也没有马勒。那匹马儿是那么的逍遥自在,它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可是它却心甘情愿陪伴着杰瑞老大,杰瑞老大去哪儿它就跟到哪儿。他与马儿配合得是那么天衣无缝,就如他俩是多年朝夕相处的好友。
他们跟在篷车旁边走了一会儿,接着马儿扬起蹄子,迈着流畅优美的步伐飞驰而去。他们一口气跑下一个小小的低洼地,然后又跑了上来,直直地朝着西边天际那轮火红的落日跑去。那如烈火般鲜艳的红衬衫和雪白的马儿渐渐消失在万丈光芒中。
劳拉终于长长吐了一口气。“噢,玛丽!那匹马是那么雪白,那个棕色皮肤的男子的个子是那么高大,头发是那么油一黑,红衬衫是那么引人注目!黄褐色的草原环绕着他们,他们直直地飞奔到了落日中!他们会冲出落日,跑遍全世界!”
玛丽想了想说:“劳拉,你知道他是不可能跑进太一陽一里去的,他和所有的人一样,骑着马在地上跑。”
但是劳拉觉得她并没说错,她说的是千真万确。那匹美丽的自一由的马儿和那个奔放的男人冲进太一陽一里的那一刻,已经永远烙印在劳拉的脑海中了。
一妈一还 是有些担心那个人会埋伏一在某个地方抢劫他们,但是爸安慰一妈一说:“不用担心,杰瑞老大已跑到前面去找他了,杰瑞老大会跟他待在一起,直到我们走进营区。杰瑞老大不会让人来一騷一扰我们的。”
一妈一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们的女儿是否安然无恙,然后紧紧搂一抱着格丽丝。她不再说话,因为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但是劳拉知道,一妈一其实一点儿也不愿离开梅溪,一点儿也不喜欢现在这个地方。她不喜欢在暮色苍茫中在荒郊野岭匆匆赶路,而且更要命的是,还 有可能遭遇骑马人的抢劫。
天色越来越暗,鸟儿发出孤独的鸣叫一声。灰蓝的天空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黑色条纹。直线条是野鸭群,V字形线条是雁群。领头的鸟儿一声紧似一声地呼唤着它的同伴,其他的鸟儿也跟着回应。整个天空都回荡着尖锐的声音:“吭!吭!吭!呱!呱!呱!”
“它们飞得特别低,”爸说,“准备在湖上过夜呢。”
前面就是一个湖泊。天边出现了一道细细的银线,那就是银湖。位于银湖南面的是波光闪烁的亨利湖和汤普森湖。双子湖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黑点,那是“孤树”。爸说那是一棵大白杨树,是大苏河和杰姆河中间唯一能看见的树。它长在只有路面那么宽的高地上,根系深深地扎在双子湖中间,可以充分地吸收水分,所以才会长得这么枝繁叶茂。
“我们以后从这棵树上采些种子,种在我们的土地上。”爸说,“你们在这儿看不见灵湖,它在银湖西北方,离这儿大约有十五公里呢。卡洛琳,你看,这儿是多么好的一个狩猎场啊。真是地肥水美,到处都是飞禽啊。”
“是啊,查尔斯 ,这一切我全看在眼里呢。”一妈一说。
太一陽一沉下去了。它像一一团一流光溢彩的液体,渐渐沉到深红色和银色一交一相辉映的云雾中。清冷的紫色影子从东方升起,缓缓地掠过草原,然后慢慢爬上高空,天色越来越暗淡。低低地悬挂在漆黑的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风猛烈地刮了一整天,夜色笼罩着大地,风儿也变得一温一柔起来,在草丛中呢喃低语。在夏夜的天空中,整个大地都渐渐平静下来。
爸在低垂的星空中马不停蹄地赶着车前进。马儿踏在草地上踩出轻轻的踢踏声。在遥远的地方,几盏灯光透过漆黑的夜晚发出微弱的光,那就是银湖营地的灯光。
“接下来这十二公里我们就不用再看路了,”爸对一妈一说,“我们只需沿着这些灯光走下去就行了。我们和营区之间除了这片平坦的草原和空气,再也没什么啦。”
劳拉感到又冷又累。那些灯光看上去若隐若现,虚无缥缈,也许是星星在一眨一眨的呢。整个夜空星光闪烁,在黑夜中变幻着各种图案。车轮飞转,草丛沙沙作响,这种声音一直萦绕在劳拉耳际。
突然间,劳拉的眼前一亮。一道门出现在她眼前,灯光从屋里射一出来。亨利叔叔穿过明亮的灯光乐呵呵地走过来。劳拉心想,难道这是亨利叔叔在大森林中居住的那幢屋子,劳拉很小的时候就去他家玩过呢。要说不是,怎么亨利叔叔就在眼前呢?
“亨利!”一妈一大声喊道。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卡洛琳!”爸大声说,“所以就没事先告诉你亨利在这儿。”
“天啊,我真是感到太意外了,惊讶得差一点儿停止呼吸!”
一个高个儿男子冲着他们微笑,原来他就是查利堂哥,那个当年在燕麦田顽皮捣蛋不断给亨利叔叔添麻烦,被几千只黄蜂蜇伤的大男孩。“嗨,小家伙!嗨,玛丽!还 有小宝宝卡琳。你们都长成大姑一娘一啦,不再是小丫头了,是吧?”查利堂哥扶着她们从篷车上走下来,亨利叔叔从一妈一妈一手中接过格丽丝,爸扶着一妈一从车上跳下来。堂姐露意莎走过来,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嘴里嚷嚷着,把他们推进小屋。
堂姐露意莎和堂哥查利现在都长大了。他们住在这间工棚里,替那些修铁路的工人做饭。那些工人已经吃过晚饭,现在都去工棚里睡觉了。露意莎一边说着这些事情,一边把在炉灶上热着的晚餐盛好让大家吃。
吃过晚餐,亨利叔叔点上一盏灯,领着大家去工人们替爸盖好的一间小屋。
“全是用新木材盖的,卡洛琳,屋子里干干净净,实在是太棒啦!”亨利叔叔举着灯让他们看看新的木板墙和靠墙的一床一铺。小屋的一端摆着一张一床一,那是爸和一妈一的,另一端摆着一张上下一床一,劳拉、玛丽、卡琳和格丽丝在这张一床一上睡。堂姐露意莎已经早早把一床一铺好了。
不一会儿,劳拉和玛丽就躺了下来,一床一上铺着厚厚一层新鲜干草,沙沙作响,她们迅速地把被子拉到鼻子底下,紧接着爸就吹熄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