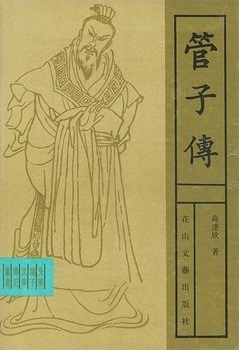有一天,我接到了总部的一个命令,要我去调查一个社团的情形。这个社团,显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几天之人,他们将要用“德国工人党”的名义来举行会议;而且费德还将前去演说。
我必须去赴会,察看众情而做一个报告。
现在。军队对于政党发生的好奇心,已经充分地明白了。
自从***之后,军人已经获得了政治上活动的权利,就是毫无经验的军人,也充分地来利用这种权利了。
但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发觉了军人对于***党的同情,已在慢慢丧失而倾向于民族复兴运动,因而十分后悔,才知道应该撤回军队中的选举权,并且还应该禁止其参加政治。
衰弱了的资产阶级,以为军队必须回复过去的情形,而为德国国防的一部分,但是中央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意凶,那差不多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颗毒齿,必须把他来拔除的。
但是,没有民族主义,那么,军队仅仅成为一种永久的维持治安的警察而巳,不再是抵抗敌人的一种力量了。
以后和年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所以,我对于上述的工党,虽然是毫无所知,然而也决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旨德的演讲完毕了我很高兴,我以看已足,准备出场时候,忽来宣布说珊在人人都可发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
但是,起初所见闻的,一些也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后来,忽然有一位“教授”
站立起来说话了,他对于费德的议论发生了疑问,待到费德对他了满意的答复之后,他又突然把“事实的根据”作为要素,毅然地建议着,说这个新兴的青年党最是适于能使巴维利亚,脱离普鲁士的压迫而奋斗的。
这位先生真是厚脸,他还说这事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日耳曼奥地利必定会立即和巴维利亚联合德国的和平也就有了希望,以及其他类比的无意义妄盲。
在这时候,我乃不得不请求主席,准许发言,我也来发表一些意见。
我因此把这位“学者”的狂言痛加驳斥,我的言论,也就获得了很的胜利。
我的话还未说完,他已经像丧家之犬一般的狼狈逃出去了。
在那时,我会把这件事反复的加以思索,并且预备置之勿论了。
可是,这真是使我一生惊奇的,就是不到一星期,忽然戮接过了一张邮片,说是已经准许我做德国工人党的党中:并且请我去参加下星期三的该党的委员会。
他们这种做求会员的方法,真使惊诧得不知所以,叫人恨既不对,爱也不是。
我想自己来树立一个党,我绝无参加现成党派的心意。
真的,我实在不会有过参加他党的梦想。
我真拟动手写信去答复该党的时候,忽然我生出了一种好奇心,决意要那天我自己到会,趁此机会要亲自解释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忽然,有人来告诉我,说是全国工党的首领将来亲自出席。
这一个消息,使这听到很有一些惊奇。
我的理由,也只好慢慢来声明了。
恃然,他真的准时出场了。他就是费德讲演时的重要的发言人哪。
这件事更使我诧异了,我决计静待着,看他有些什么事件发生。
无论怎样他们的大名,我是已经知道了。
该党全国的首领,是叫赫勒先生(Herr Harrer)慕尼黑的主席便是安顿。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
开会了首先是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记录,并且再对演说的人表示谢意,接着便是***员的选举----就是通过我入党的问题。
我就开始向他们发问。
我方才知道了该党除少数重要的原则外,毫无所有,其他是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党纲,没有小册子,没有印刷品,甚至一个区区的橡皮图章都也没有置备:然而,他们却有着极大的信仰的良好意志。
我不愿对他们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们所研究的是些什么事了,仓促产实渴望着一种新运动,这种运动,实在是比了一般称做党的范围还要大。
于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来最困难的问题了。我对于这个党究竟是加入呢还是不加入呢?
命运似乎在向我示意,我绝不应该加入当时的热呢现成的大政党,我将更详细和来说明我的理由。
据我看来,这可笑而人数很少的团体,尚未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并且还能存个人活动的余地,这在我实在是--件很有利的事。
该党尚有待整顿,这个运动的范围愈小,那么,这个运动适当的表现也愈快。
该党的性质、目的和方法,还可以决定,这在现存的各大党之中是绝不可能的。
我对于这件事愈是反复的思索,我就愈是坚信这种小规模的运动,可以作为复兴民族的先声,这是在现在的议会中的各政党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政党,仅仅知道牢记着陈腐的观念。或是因为有利可图的缘故而来拥护一种新制度。
现在,这里所提倡的,乃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并不是--种新的选举的口号。
我经过丁两天的苦思闷想,最后。我才决心进行着我听取决的步骤。
因为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关键,这时候,这后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的。
这就是我实行德国工人党的经过,他们还给了我--个第七号的临时党证。
更新于: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