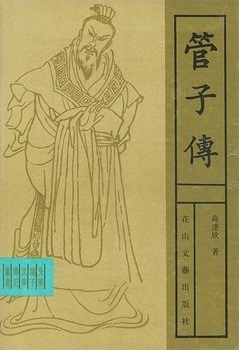我现在来叙述我党发展的初期,并且再来简略的叙述一下和它相关的事件,我决计不想来涉及本党的理想目的。
因为,如果把本党的目的来一一说明,那就得要占去了一册的篇幅了。
因此我想在下编中来详细的谈论一下本党的党纲,决定党纲的原则,并且再就我们的见解去说明“国家”这个名词的意义。
我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几十万的群众而盲,他们的希望,大都是相同,不过他们苦于不能说出他们的意思而已。
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个人勇往直前的来作战士,而在后面附从的人那就有了不知亿万,这确是一件大注意的事。
这种改革的目的。潜伏在数十万人的心坎中,经过了几百年,方才有人崛起而宣布这一致的要求,自己来担任领袖,促其实现。
现在,群众们的愤懑,就足可以证明了他们的心目中都具有的彻底改革现状的势望;有许多人厌恶着选举,还有极端的疯狂般的左倾的人,也可以作为佐证;他们就是新运动所第一应该顾到的。
我们要恢复我民族的政治力势力,第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应该先恢复我民族自卫的欲望。
经验告诉我们,对外政策的建立,以及国家强弱的判别,根据于现有的军备者少,而根据于民族的显著或是潜蓄的抵抗力者多。
因为同盟条约,是人所缔结的。
因此像世人都认为英国人的指挥和精神,很是果敢坚毅,那么我们仍钭把英国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同盟者了。
因为他们一经奋斗。
就立刻决定殚精竭力,不惜时间和牺牲,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最后的胜利。
从这地方,就可以见到一国的军备,不必随时和他国成了任何样的比例。
要把德国的目的自治国家的新运动再建立起来,必须要集中力量。博取群众的拥护。
我们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丝毫没有希望,而且很缺乏爱护民族的热忱。
凡是对内对外的强有力的民族政策,无疑的,必定要受到他们所对。
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很是愚昧无知,在自由解放之前,曾用消极抵抗的态度去反对毕士麦;因为他们素以怯懦著名,所有我们也不用去怕他们有了那样的积极的反对。
但是,就国内一般具有国际同情的群众而论,那情形又不同了。
不但是他们的本性倾向于暴横的观念,就是做他们领袖的犹太人,也是愈来愈残暴了。
除此以外,凡是一种运动,出于自卫机的,必定要被些背叛民族的党魁所反对仇视。
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复过去的地位,必要首先来制裁这辈祸国的罪魁,在钭来的法庭之中对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事件,将不再作为通常的国事犯来审判,而作为背判民族的罪来审判。
因此,不论是那样的恢复德国的独立的思想,必定和恢复我民族的坚强的意志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
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新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唤醒群众的民族观念。
从策略上说,有下面的许多要求,由此发生。
(一)要使民族运动能够吸引群众,就应当不惜任何重大的社会牺牲。
但是,运动的目的,既在为德国民族而唤醒德国的工人,那么当民族生活的维持和独立还不曾受到威协的时候,经济牺牲性,自然还不曾到了必要的时候。
(二)要使群众民族化,那决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观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唯有毅然决然地把全力集中在这种目际上。
大多数的民众他们并不是大学教授或是外交家。
一个凡是要想得到民从的拥护必须知道用那一种的秘锁,才可以去启发民从的心灵。
此种秘锁,并不是一客观的力量,而是一种决心和毅力。
(三)如果我们为了的目的,积极的指挥着政治斗争同时再努力于消灭敌人,则我们必定能够获得群众,这是毫无疑义的。
群众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去和那目的显然相反的人握手言欢,这决不是群众所能懂得的。
他们只知道强胜弱败而已。
(四)如果要把某一阶级列入于民族的全体,或是纳进国家,这方法并不在贬抑上等阶级,而他在提高下等阶级。
但是担负这种责任的,那决不是上等阶级,而是正在争取平等权的那个阶级。
现在的中等阶级,他们能得参与国事,这并不是赁藉了贵族的帮助,是靠着他们自身的实力,以及他们领袖的领导。
要使现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义的国民团体,其中最大的障碍,并不是阶级的利益,而是国际领袖的态度,因为这辈的国际领袖,他们是仇视着民族和祖国的。
那些工会对于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狂热的民族观念的话。那么工人会可以使无效的工人一变而为民族中的最优良的分子,并且和各处纯粹的经济斗争,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倘使一种运动,要使德国的工人倾向于自己的民族,并且对疯狂的国际主义,加以鄙弃,那么,必须切实反对那些大雇主所取的态度,因为雇主把民族的意义,认为就是雇工在经济方面应该屈伏于雇主之下的。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维持民族的经济,只知靠着他自己的强力,横肆要挟,那么他对于民族所犯的罪,实不下于雇主以残栈的剥削手段,去蹂躏民族的劳动力,从他们的汗血中去榨取厚利。
因此这个新兴运动的同志的来源,第一便是工人团体这种运动的任务,是在使工人们脱离遇妄的国际主义,从贫困的社会之中使他们解放出来,从不他们低落的文化这中把他们知识增高起来,且能在团结完善、和充满丁族感情及热望的社会中去成为一种主要的分子。
实在,我们的目的,并不愿意在民族的壁累之中欣起了变动,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员改变了他们的态度,我来信奉我们的主张。
整个运动的方针,对于这原则是极关重要的。
这种一贯而明显的态度,必须要表现于史党的宣传之中(这态度是宣传者必须具有的;宣传的内容与方式,必定要能够感动群众,并且再观察其实际的成绩是怎样,那才可以测验这种宣传的是否正确。
在群众的大会之中,效力比较最大的是演说,这演说并不在能感动知识分子,而是在能投合群众的意思。
要使政治达到改革运动的目的,我们决不能单由苦心劝导。或是感化当局的方法便并能到目的的。
唯一的方法,便在夺取政权。
然而,仅仅把政局,变动了一下,因而便取得了行政权,这是仍能认这种“苦跌打”(Coupdetat)为成功的。
必定要***根本目的和意志完全已经实现;而且为民族所造的福利较旧时代使大家所享受的为多。
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像盗匪行为的德国的***暴动,根本不足以语比。
但是假如夺取政权,是实现改革的前提,那么把改革作为目的的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便当为民众运动,而非文人的茶话会和游艺会。
这个新兴的运动,在本质和组织上虽对义会加以反对,但是,在原则以及和党的组织上,便否认取决于多数的任何的原理,这个原理的含义,谓领袖如果是仅仅维持秩序和执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见,那是对于他的身价有损的。
依照了新运动的主张,不论事件的大小,领袖是具有绝对的威权,并且还负有完全的责任的。
把这种原则去贯彻于全党,并全再推行于一国,那就是新运动主要任务的一种。
最后这种运动,它认为它的任务并不在恢复那--种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对其他的政府,它是在创立民主政权和君主政体所依着维持的基本原则。
它的使命,并不在建立一个君主政体,或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在创立一个日耳曼的国家。
这种运动的内部组织,并不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便利的问题。
最优良的组织,必须使领袖和党员间的隔阂尽量的减少,因为组织的使命,是要把一个确定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常在一般人的脑中造的----输入民众的脑海中而促其实现,在党员增加的时候。必须要成立支部;这支部便是将来政治团体中各地的细胞组织。
这各运动的内部组织,应当依照下列的纲领;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于慕尼黑一地。
训练忠实党员,并建立一学校,以便为这种理想作将来的宣传。
把现在在这里所得的显著成功,作为将来取得必要威权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领袖的权威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公认之后,于是再来成立地方的支部。
做领袖所需要的资望,不但是意志,并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较之由纯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为重大才能意志和坚忍三件事完全集于一个人身上,这人便是最良好的领袖。
一种运动的将来,是有赖于从事运动者的狂热(甚至是偏激)。他们把这运动当作唯一的正当的运动,极端反对那性质相似的其他的组织。“
如果说,一种运动和他种运动联合起来,便可以增加力量,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这种运动的目的也许是相似。)我向来承认运动数量的增加,便是范围的扩大,但是,那些浅见的入,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以为就是势力的增强;其实,徒使这运动的本身。孕育着衰弱的种子。
凡是一种理想所寄托的无论什么组织,它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的宗教狂热和那能容忍的固执的精神,他们攻击其他的组织,坚信着人家都是不对的只有我是的。
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并且以这种武器,那众。这理想,奋斗于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无敌的。凡把压迫加之于这种组织。那是恰好使其内部的实力增加。
基督教的伟大,并不在于委曲求全而使教义和古代类似的哲学思想相调和,是在于他们对于本身的教义,努力于坚决和狂热的宣传到及辩护本党的同志加于民族敌人的一切仇视以及这种仇视的表现用不到惊奇看作这是平常而当然的事。
因为谎言和诽滂根本和这种仇视的表现是不能分离的。
不论是那一个,凡是不受犹太报纸的攻击、诽谤和污陷的,那么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欲判断他的意见的价值,信念的确否,以及意志的强弱,完全可以用我们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更新于: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