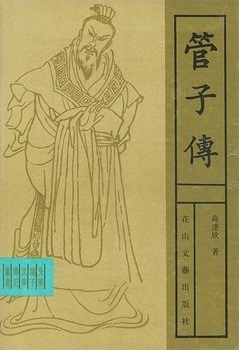宣传必须在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须广征人材,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
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组织,因为他们所得的结果,大都是黯然没有生气的。
为了这缘故,我们如果采取宣传方法从一个中心点去广播某一种的观念,然后再就所得的人材当中,就审慎的去选择领袖人物那是最要紧的。
常有一种人,初看像是毫无显著的才能,岂知后来竟是卓越的领袖人物。
大家都以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特质和能力,就是理论上有丰富的知识,那是大误而特误的:因为在事实上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大理论家就是大领袖的才具----自然,这种才具,自然不是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问题的入所乐闻的。
煽动家虽然不过是一个黠的政客:可是他既是某种观念传播给民众,可见他必定是一们心理学家。
如果叫他来做领袖,那必定较不通人情的理论家为优。
所以讲到领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够鼓动群众的才能而言。
理想爱和领导群众的能力是截然的两件事。
假使一个人一身能够具备理论家、组织家和领袖的本领,这真是了不得的伟大人物了;然而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
前面我已经说过当我党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对于宣传这一点我们就加以十分的注意的。宣传的使命,就是在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俾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
在这过程中,宣传的目的,实在比组织的目的更重要。
宣传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的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组织的目的,就是使信徒之中最优秀的分子成忠实为党员。
至于信徒们办事的效能怎样,才干怎样,智力怎样,人格又是怎样,这都不是宣传的本身所应该去顾虑的;因为宣传的目的,就是在招致信徒,至于在众人中去慎选干员,俾能推进运动,而使主义能够到达成功之路那实在是组织方面的工作。
宣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替未来的组织设法罗致人才;而组织的第二个任务,那就是争取权力,俾希望达到新主义的最后胜利。
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在注意党员不因内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运动的工作,因而陷于衷弱地步,还须注意于奋斗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够再接再厉臻强固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所以要注意着不应该去滥招党员。
因为人类中只在少数的有具有毅力和胆量;所以如果一种运动的党员,要是漫限制的招收。
那么这个运动终有衰败的一目的。
如果单单是为自卫计,那么,一种运动而要想维持着它的胜利,就得要限制党员的人数;就是以后想扩大组织,也要单详加考察,审慎出之。
惟其是如此,那才能使这运动的干部时时更新,时时健全。
干部必须要握着指挥运动的全权----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宣传的内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赞同,总揽一切的权力,进得着一切的工作,以谋理想的能够达于实现。
我主持党中的宣传事务,那时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将来的伟大运动留下发展的馀地,还宣传着最激烈的原则,去吸引那些最优良的分子来加入我党。
我的宣传越是激烈惊人,那么,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坚的人越是生着畏避的心而不敢来侵入我们组织的干部,这些都是有益于我党的。
当时我采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用作我党的宣传,使我党的运动日趋于激进;从此以后,凡是加入我党的人,便多是激进的人。
这种宣传不久就有了成效,有几十万的人数,不但深信我们是对的,而且极希望我常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是怯懦而不敢牺牲的。
直到一九二一年,这种吸收同志的工作还是不错,而且对于我党的运动虽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不过这一年的夏天,由某种事件显示了我党的组织不及我党的宣传,于是是宣传的成效,也就日见显著了。
从一九一九年到--九二○年,党员大会选出一个委员来指导我党的运动。
根滑稽,这一个委员会竟采取我党所极端反对议会制度。
我不愿附和这样笨的办法。
不久,我不再去出席于委员会了。
我只有为我自己作宣传,不问其他的一切。
我不听任何无知者的劝诱而改变方针,同时不去干涉他人的分内事务。
等到新章程一经采用,我就被任选为党中的总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权及附带的权利,这种愚笨的办法也就立即废止。
用实行专责的原理,去代替委员的合议制。
总理是负责指挥这个运动的全责的。
日子长久了,大家就公认这种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党的统治上该是这样。
委员会只有空谈而毫无一些成绩,所以如果把它来解散最好使他们去从事实际工作。
眼看着他们一声不响的离职,以后不知到那里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来。
因了这事使我想念到同样的大制度,那是国会(Reichstag)。
如果叫那些坐谈的议员去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要他们各人对于工作须负责任的时候,他们必定会迅速的鸟兽散了。
一九二○年十二月,民族观察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由我们来接办了。
这个报纸,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对于人民的意见是多所爱护的,现在变为民族的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机关报了最每星期刊行两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为日报,又到了是年的八月底,于是便扩展而成为所共和的大张的形式。
民族观察报是一种“民族”的机关报,它有着长处,自然也有它的谬误和弱点。
它的内容虽然不错,然而它不能作为商业经营。
原想此报由众人来定阅,以报费来维持生命的,可是它不知道和他报去竞争,以谋自己的生存,徒然用爱国的人们的一些报费去弥补营业不良的损失,而且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不当。
我看到这种危机,于是颇费苦心去极谋救济。
在一九一四年大战的时候,我曾认识了马克思。阿曼(Max Amann),他现在在本党中提任着事务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偶然到了这位军队中的老友,我便请他担任党中的事务主作任,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优缺,所以迟疑了好久,才开始答允。
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愿意被庸碌的委员会所牵制,而愿意对唯一的领袖负责。
结果他挑选了几个人去任报馆的编辑。
这几个人以前曾隶属天马维利亚人民党的;但是,依他们的工作成绩而论,那是极能胜任的。
这种试验,成效卓著这就是因为本党以忠诚坦白的态度去赏识人才;所以能够使职员心悦诚服,比较往日所收的效能尤为迅速而稳固。
以后他们便成为良好的民族社会党员了。
非特他们的言谕是这样,而且还能见之于实行。
他们在吾党新运动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实坚定,而出于至诚的。
在两年当中,我的见解慢慢他获得了实现,至小就最高的领导机关而言,我的见解,在现在党中已经成为极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证明这种制度已经获得了成效,当吾在四年前加入这运动时候,那时党中还没有一颗橡皮图章。
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吾党遭到解散,财产都被没收,一切贵重的物品,以及报纸所值总数已超出十七万金马克了。
更新于: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