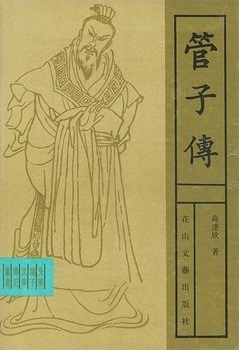列车终于是沿着京奉线前进了,我们一起八个女官,合着张德,和他手下的那班太监,齐象庙里所塑的木偶一样的侍立在太后的左右。大家各怀着一颗很兴奋的心,准备欣赏这一次长途旅行中的种种奇趣;但谁也不敢在脸上露出一丝兴奋的情态来,连眼睛也不敢往车外看,只当没有这回事一样。我们的车子是在午后四点钟左右出发的,而第一个站乃是丰台,丰台离北京不过十一公里,等于是北京站的旗站一样。我们的火车,便在这一段短短的距离内,踱着牛步一样的大步,蠕蠕地往前滚去;凭是开得这样的慢,我们还不敢相信太后必能满意,只要车子滚得稍不自然一些的话,伊就要感觉到不快了。
照我们预定的行程,太后将在车抵丰台之后,进伊第一次的车上的晚餐。晚餐过后,略事休息,便直驶天津,希望在太后准备安寝之前,能够到达天津。因为依内务大臣庆善的主意,象太后这样尊贵的人,殊不宜寄宿于任何一处村镇中,虽然在事实上,太后本不下车,车子不论是停靠在村镇里,或大都市中,原没有什么分别,但庆善总以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我们的列车任是开得怎样的慢,丰台终于是到了!而我们的晚膳,也在同时端整下了。平常的时候,火车从北京到丰台,至多也不过三四十分钟,我们却足足行了两个钟点以上,真可说是打破了全世界的火车的最低速率。但是对于太后,凭它走两个钟点也罢,走两天工夫也罢,反正有的是时间,今天过了,还有明天,明天过了,还有后天,大后天…………,伊简直从不曾想过时间有多少价值;而且伊自己到了车上,整个的政府,便等于带来了,一切军国大计,同样可以裁决施行,因此,伊就越发的不注意时间了!
因为伊不知道宝贵伊自己所有的时间,于是伊对于别人和时间的关系,也是十分的漠视。单说我们这一次上奉天去,火车行驶的迟速,似乎单是影响了太后自己或我们,其实却影响了无数的人。譬如你这个时候凑巧要从天津到北平,或从天津到锦州,在寻常的时候,是只要有钱买票,你就不难顷刻即达;但在这时候,适逢皇太后的御用列车正在铁轨上大踱其方步的当儿,你就倒霉了,无论你有多少钱,或有怎样重大紧急的事故,都不用想搭什么火车!好在你有的是时间,尽等着吧!一天,两天,三天,…………这样老等下去,总有一天会放你过去的。也许你这个人的忍耐工夫太浅,等不到太后的专车到奉天,你已经生生的急死了,那还不是自寻烦恼吗?我敢说太后是永远不会想到伊这个“断绝交通”的禁令将与他人以何种的影响的;即使想到,伊也必认为这是理所当有的事情,决不因此发生什么怜念或不安的感觉。
火车到丰台站便停下了,我从车窗里面望出去,却不见有一个闲人。据我所知道。这地方原是很热闹的,但现在竟变得象荒漠一样的静寂了,连一些声音都听不见,我不由得佩服这些地方官的才干和魄力,他们为迎合太后起见,无论怎样严酷的手段,都会施展出来的。可是那一班被严禁着不许走近车站,甚至不许随便向我们这列御用火车看一眼的民众,对于太后这一次在这里经过的事实,将作什么感想呢?怕是谁也不会注意的。依我猜测起来,他们必然是怀着一腔特殊的紧张的情绪,在悬想真以为是呵护他们的天老爷,在这里经过了。本来,皇帝原有“天子”之称,那末,皇太后和天老爷当然也有相当的关系;就算伊是代表天老爷的,亦无不可,反正伊的权威也着实不输于天老爷!
因为这时候还在春季中的缘故,白河的名产----鲫鱼,恰好成为一种最合时令的礼品0所以当我们的车子从北京开出的当儿,这里附近一带的官员,都正在不惜重金的搜购才出水的鲫鱼,以供太后佐膳。及至车到丰台,好几尾才出水的大鲫鱼,便用很精致的东西盛着,经过了一番极腐化的礼节,郑重其事的献上来了。可是这些官员虽已如此的小心侍奉,而太后却象没有知道的一样。理由是丰台附近一带的官员,都是些微末前程,名姓不见经传的脚色,根本还赶不上和太后见面咧!①
然而太后虽不接见他们,或者他们自己也知道太后决不能让他们进见,但他们无论怎样胆大,也不敢偷这一次懒;每个人都在火车未到以前,赶上车站来了。他们的唯一的目标,只愿太后对于站上的布置,表示满意,四周也不见有半人闲人,这样他们便可以安心了。不过他们还是很胆小,尽在距离列车较远的所在,忙着乱着,谁也不敢擅自走近过来。我打车窗边远远地望过去,但见许多穿着五颜六色的公服的人列成了约莫半公里长的一行,蠕蠕地挤动;大家都透着一种诚惶诚恐的神气。拼命在张罗。可是凭事实来说,他们所忙乱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跟太后或这列车,永远不会有什么益处,真所谓“无一足取”,只有这尾鲫鱼,总算差强人意。
说到鲫鱼,大概谁也免不掉要食指大动吧?鲫鱼原是一种滋味很美的鱼类,尤其当它才出水的时候煮起来,那味儿便格外的鲜美。寻常富贵人家的筵席上,我们往往可以见到这一味佳肴。有些欢喜讲究吃的人,为着要夸耀他自己的富有,和对于吃的讲究起见,每喜在高朋满座的时候,临时教当差们用挺大的木盆子,盛着几尾生趣盎然的鲫鱼捧到客人的面前来,请他们随意挑出一尾,立刻拿进去洗剥烹煮;有些人竟会教他家里的厨夫当着客人的面前,把他们所挑中的一尾鲫鱼,立即洗剥起来,以表示绝对不再掉换。
太后在丰台站上所收受的那几尾鲫鱼,也曾经我逐一验看过,因为太后自己不愿意和那些官员见面,所以就派我去充代表,我验看的结果是很满意,没一尾鱼不是活泼泼地在游泳。但我们并不曾教我们的厨夫当场把它杀死。大概太后的个性虽然是特别的坚毅果断,然也不忍眼睁睁地瞧着一尾鱼在伊自己面前毕命。
可是这几尾鲫鱼却并不能因此而就得苟延残喘,因为太后赞成不赞成把这几尾鲫鱼在伊面前洗剥,乃是一个问题,至于伊爱吃不爱吃,则又为另一问题。何况才打附近河里捉起来的鲜鲫鱼,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很难得的美味,太后岂肯错过?所以那几尾鲫鱼一送入“御膳房”之后,不消多大工夫,便煮成熟菜,端端正正地捧上来给太后尝新了。太后举起筷来,只夹了一片肉吃,已不迭声的赞好了。接着,伊又命令那些太监把这一碗鲫鱼依旧送回御膳房去,这意思并不是说不要吃,乃是要他们重新换一个方法煮过。这个方法就由伊自己所指定的:第一步先把所有的鱼骨全部剔出来,只留鱼肉,连皮也不要;第二步再把分量和鱼肉配得相称的嫩豆腐,加上了糖,酱油,盐等等的调味品,和它混在一起煮;这样便成为一盅极鲜美的鱼羹了。
从前人对于鲫鱼,还会利用它来作一种卜自己休咎的东西。那是鱼鳃下的一根短骨,一尾鱼共有两根,恰好生在头部的两边。它们的形状和一柄扇子略有几分相似之处,但较鱼身上其他各部分的骨头略软一些,而且它的某一边很平整,所以尽有直立的可能。当它直立时,看去真象是一条小小的帆船。它有一个别名,唤做小仙人,这当然是因为可以用它来卜咎的缘故。那末究竟如何卜法呢?说来是很滑稽的,手续更是非常的简单:只须你用筷子夹住了这一根鱼骨,在离开台面约莫半尺的高度上掷下去,连掷三次,如其三次之中,能有一次把这根鱼骨掷得直立起来,那就算是一个十分吉利的朕兆了。而这个掷的人,便将无疑的得到一种可喜的幸福。我知道在外国也有这样相类的迷信的举动,所差的只是我们用鲫鱼的鳃骨,他们用鸡或鸽子的胸骨而已。
皇太后的思想原是很旧的,而且特别的迷信神佛,伊见了这一根号称“小仙人”的鱼骨,当然也得试上一试!不料连掷两下,这根鱼骨都不曾立直,这样可就危险了。伊的脸上已很显著地透出了一种懊恼的神气,虽然伊还不致于十二分的深信一根小小的鱼骨,真会影响到人的命运;但伊总觉得如果三掷而鱼骨仍不立直,毕竟是一件很扫兴的事情。幸而事情并不象伊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坏,第三次掷下去,这根鱼骨竟就偏不倚的站直了。伊当然也是高兴极了,不过我想要如这第三掷依旧失败的话,伊决不肯就此罢休,必将四次,五次,六次,…………以致于无数次的掷下去;反正伊是一个贵不可言的皇太后,谁还能限制伊只许掷三次呢?这样不停的掷下去,那根鱼骨少不得总有一次要站直的;而伊也必总有一次会满意了!我日常留意太后和行事,不但对于这种小的事情如此,便是对于一切军国大计,伊也往往很能忍耐,决不因稍受一些挫折,或阻碍,而即变更伊自己的策略,这种精神,当然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
当那剔尽了骨头和鳞甲的鲫鱼肉,和着嫩豆腐一起煮好之后,便又第二度的捧到太后面前来;伊就用一柄银匙,接连的喝了几匙,同时还啧啧有声地称赞着,使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的人,也看得垂涎欲滴了。后来,伊忽然把吃剩的一半,指明要赏给我吃。这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了!因为太后如果把吃剩的东西,或喝剩的茶水,指明赏赐某人吃,这个的人身价,顿时便增加了许多;不但旁人都在艳羡他,就是他自己也必认为是一桩极荣誉的事情。所以太后此刻把这一味新鲜的鱼羹,留一半赏给我吃,实在是很可喜的;何况用嫩豆腐和在一起煮的鱼羹的滋味,的确是很不错的呢!
太后的食量虽然并不象一般老年人那样的减退,但因为御膳房供呈上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无论一碗菜,或一盏汤,总使伊不能吃喝得罄净;于是便养成了伊爱把余剩的东西,赏给服侍伊的人去吃喝的习惯了。可是我对于伊这种恩典,总是非常的小心应付:如其伊并不曾吩咐我把余下的东西吃掉或喝掉,我无论心里是怎样的爱吃爱喝,也必竭力忍耐,立刻把那原碗或原盅递给小太监们去收拾;如其伊已经吩咐明白,要教我把余下的东西吃掉或喝掉,那时我就不能再客气,必先恭恭敬敬的向伊磕上一个头,表示我对于伊的赏赐,已是十二分的满意,感激,接着便把碗中或盅中所剩的东西,毫不迟疑的吃喝下去,无论我腹中是怎样的饱满,也得欣然服从,否则便是故违圣旨,罪不赦了。
记得有一次,另外有一个女官,正和我一起服侍太后,太后恰好已喝过了几口茶,想把那茶本放下来,这位女官便走过去替伊接了;其时那杯中还有半杯茶留着,伊也许是因为口渴太甚的缘故,竟不曾注意太后并没有说明,要教伊代喝,便不假思索地向太后磕了一个头,把那半杯茶喝完了。我隔着伊的肩膀,偷眼去瞧太后,只见太后,正在看着伊微笑,我不由掌不住也笑了。在太后意思是因为这一个过失,毕竟太小,犯不着怎样严厉的责备伊,所以爽快就不说了,只把笑来惊觉伊。后来,这个女官当然便醒悟过来了,伊当然是万分的感激太后,可是对于我,伊反而不肯轻易放过了。伊认为我的窃笑是一种有意的挑拔,因此大有怒不可遏之势,当场虽不曾发作,过了一天,伊终于利用某一个机会,直截了当的数落了我一场。伊说:
“你真是太聪明了!谁也够不上你。可惜你太把别人看得不值一文了!你往往欢喜玩弄人家,使人家受窘,作为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人家究竟受得住受不住,你却绝对不问了。可是你要明白:轮资格,人家都比你先进宫好几年咧!”
我对于伊所给我的这一场数落,并不曾提出什么反抗,也没有把伊对于我的误会,作什么解说,只是付诸一笑,马上便丢开了。
我们在丰台站上所吃的一顿晚餐,也是很富有严重性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一餐乃是上车后的开首第一餐,而且晚餐照便又是每日两次“大餐”中的一次;于是那一百碗的正菜,便象宫中一般的送上来了。这些菜都是装在一种木制的大匣子里的,如果在寻常的火车上,那些车门必然是太小了,必不能容许这些硕大无朋的食匣子通过;幸而我们这一列御用火车上的门户,都已重新改造过,差不多已大过了寻常的一倍。于是每当进餐的时候,好几十名太监,便在外面的月台上,排成了很长的一行,打那代表御膳房的那辆车上起,一直排到太后这一辆车上;所有那些满装著名色山珍海味的食匣子,便象小学生所做的授木棍的游戏一样的从第一个太监,依次传授过来,约莫要隔上四五分钟,才授到站得和太后的餐桌最近的那个太监,----这人十九是张德----就由他把匣子里的菜捧出来,安在桌子上。这些匣子的外面,都用金子一般鲜明的黄色油漆漆着,再加上匣子里所装的碗盏,又都是很好看的磁器;同时那些传递食匣的太监,也各穿着五颜六色的公服;因此,单这上菜的一幕,已是很美丽动人的了!可惜除掉那些愚蠢得可厌的官吏之外,旁的人便不用想见到这样的好戏。
待到我们的第一次晚餐完毕以后,太监便教人传令出去,吩咐开车;于是我们便继续给这列黄色火车装载着,慢慢进望天津行去。不料庆善的主张虽想使太后到了天津再安歇,可是太后竟不能领受他的厚意,车子行到中途上,伊就声明要安歇了。其时,庆善当然不敢再进什么忠谏,列车便马上停下来了。这里,不但不是庆善所理想的大都市,且也不在什么小村镇上,简直是在一片辽阔无人的荒野里;但太后是绝对不曾注意及此,只催促好坏些太监和宫女,忙着把伊的衾枕放妥贴,便悄悄地睡去了。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