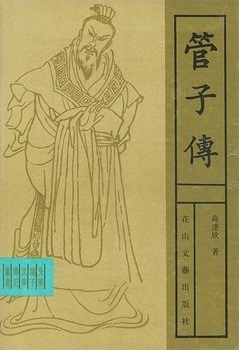照宫中的习惯,虽然不是明定的法制,逢到每月的朔望两日,照例是要唱一次戏的。这些戏的脚本有许多就是太后自己所编的;原来太后对于中国的古剧认识得也很深切,再加伊的文学本来也有相当的根底,所以要写些剧本,实在不是一件难事!宫中唱戏原也算是家庭娱乐的一种,故除元旦,元宵,和万寿节等大日子,难得召班外面的伶人进宫演唱之外,平常日子都是由一班太监担任的,他们也都曾下过一番苦功,能戏极多有几个杰出人才的技艺,反比外面的伶人更好,这是太后久已引为快事的。
侥幸得很!太后为着追念同治而伤感,以致于合整个的古宫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下的第二天,恰巧是月半,正该轮到唱戏的日子。以前每当朔望的前一日,太后多半是预先会把明天要唱的戏点定了,吩咐下去的,而且伊所点的戏,往往老是那么几出,这几出当然就是伊老人家所最爱听的,伊虽连续的一次,五次,十次的听下去,也不会觉得厌烦的;这中间,自然又要算伊本人新编的戏占多数。因此,外面的的人----包括一切王公大臣----虽从没有机会听到太后所编的戏,而我们这几个,却无不听得十分烂熟,连字句也背得出来,甚至已听厌了,巴不得太后不要再点出来;因为我们所最爱听的戏,终究还是那些原有的老戏。这些老戏不但是历史悠久,而且无论那一处的戏班子,都有相类的脚本,只是演员所用的方言不同而已;它们的所以能流传得既久且广,当然自有一种引人入胜之处!
我上面不是已经说过,每当太后有什么不快的感觉时,合宫的人便都连带的会发愁起来了;所以我们总是要尽力的设法使伊快活,尤其是在这些气象阴森的盛京古宫中,我们倘若再不在精神上找些适当的调剂,真要变为生趣索然了!因此,当我想到今天是月半,照例应该唱戏的时候,我心上真觉得高兴极了。
“老佛爷!”这一天的早上,我虽然瞧伊的脸色尚不十分温和,但为着要揭去这一重浓厚的愁雾起见,我竟极大胆地向伊说道:“今天又是月半了!我们不是应该唱一次戏吗?依奴才的意思,如其让这里的老祖宗们也见见我们那些热闹的玩意儿,使他们知道如今的天下,还是跟先前一般的升平安乐,可不是一种很好的孝敬吗?再者,我们在这里既不再有什么好去处可以出去玩,那末光是枯坐着,也太气闷啦!唱戏倒是最好不过的消遣。”
太后听了我的话,居然露出了一丝笑意,并把头微微点了一点。
“不错!你这个主意确是好的!就依你吧!”伊便绝不迟疑的核准了我的建议0①
“那末,请老佛爷吩咐,今天该唱那几出戏呢?”我的冒险的尝试既已成功,胆子便格外大了,爽快催伊点起戏来。
“我没有什么成见,就把你所爱听的戏点一两出来吧!”伊的笑意渐渐地透露了。
这真是一个特殊的恩典啊,原来每次唱戏,所有的节目十九都是太后自己指定的,不但我们这些女官从不曾享过这种特权,便是光绪,隆裕,以及一般公主,福晋之类,也是很难得轮到有奉太后懿旨点戏的机会;因为这也是表示宠眷的意思,决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盼望得到的!如其有人轮到了点戏那真和脸上装了金一样,这个差使荣耀固然很荣耀,而肩膀上的责任却也不轻呢!第一是你所点的戏必须没有什么犯讳,或于当时的情形不尽适宜的地方,第二便是必须博得太后的爱听。第一点比较还容易,只须稍微想得周到一些,便不致有什么问题啦!第二点可就大大的不容易了!然而万一你所点的戏竟不能引起伊的兴趣,这事情便糟了,你所受的羞辱和窘迫,将十倍于你所受的虚荣。想来真是很可虑的!尤其是这几日,太后的性气很不好,已使合宫的人都觉得难以度日,假使再触恼了伊,大家还好说什么话呢?况且我们不久就要回京去了,谁都希望在离开奉天之前,不要再留下一些不良的印象;于是我就格外的感到困难了。
此刻我虽然要想辞谢这个点戏的差使,也已不行了;因为方提议唱戏的人便是我不点还教谁点?这真可说是作法自毙了!但我明知懊悔已经不及,只得尽量利用我的脑筋,左思右想的考虑了约莫有七八分种模样,幸而太后也体凉我,知道我是在挨命的搜索枯肠,也就不忍催促;后来,我居然想起了一出情节极热闹的“四郎探母”。
戏码既定,自然就有人下去准备了。
关于唱戏的一切设备,宫里头是购置得非常周全的,并且都有人很小心地管理着的,要用时不难一索即得。所有的布景,戏装等等,更是无一不精美,再加逢到春天,就有适用于春天的行头,到夏天,秋天,冬天,亦复各各不同。读者听了这些话,也许不能深信无疑,以为这是事实上很不可能的事;然而却是真的!在北京宫中,就有十二个高手的缝工供养着,什么事情都不做,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老是在裁制戏装,或是打好了图样发往苏州或广东那些地方去定制,总是一些不惜工本的。这一次,他们虽然都不曾随驾东来,但我们早已把唱戏时应用的各种东西一件也不遗漏的从车上载来了。光是照料这一项娱乐品,也有一个老太监负责专司其事,他手下还有一二十个小太监充助手咧。所以我们不论唱什么戏,只要点下去便都可以排得出来的,一小半的原因,固然是行头的齐备,而最大的原因,却是那些唱戏的太监,不论生旦净丑,个个多会唱许多的戏,随时可以凑得起来,不至缺角。
唱戏就不能少戏台,幸而盛京这些宫院的建筑虽然已很破旧,但在某一座大殿前面的空地上,却也有一座戏台建着。当然,它的年龄也是很老的了!格式和我们寻常在神庙中所见的戏台相同,只有一层楼那样的高,不过地位比较阔大些。论到戏台,北京宫中的那一座也还平常,最特别的要算是颐和园里的那一座了!它一共有三层,据说当初建的时候,那些楼板全是活络的,可以上下移动,做得差不多和现在的升降机一般的灵巧。当最上的一层上在演戏的时候,下面两层为看戏的人所瞧不见的台上,已暗暗在准备着了;待到上层的戏演完,便立即把它吊上高头去隐过了,第二层便在同时吊上来,所有的布置已早就摆下,连最先出场的戏子也已在台上站着了。这样把舞台吊上吊下的结果,就省却一番检场的工夫,前后两出戏尽可很紧接的演出了。在那时候,如此巧妙的构造,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新鲜把戏,着实惊动了不少的人,而主持这件工程的设计人员中,第一个便是太后自己。可惜来为因为不很安全的缘故,就停止使用了;但规模的宽畅,构造的精美,还是非常的出色,远非别处的戏台可。
如今来到奉天,一切都很陈旧,再要有这样精美的戏台自然是不可能的了;但为不使太后感觉到过分的难看起见,临时的张罗修饰,是不可省的,好在我们有的是太监,他们人数既多,办事又能干,这些零星夹杂的事情交托他们去办,真是无有办不了的。果然隔不了多少时候,就有人来报道:“一切全齐备了,戏也扮好了,只等太后的懿旨一下,马上就好开锣。”这时候我就得把我所点的戏告诉太后了。----方才我只是差人去知照了那些唱戏的太监,并不曾先奏明太后。----造化得很;伊听了居然立即表示赞成,使我心上顿时安定不少,而且伊还在一路走往那唱戏的所在去的时候,很有兴地把这四郎探母一出戏的情节,原原本本的说给我听;其实我既然知道点这一出戏,怎会不知道其中的情节?不过太后是绝对不管的,伊总欢喜倚老卖老的,很郑重地把无论什么事情,当做一件新知识,新发明一般的告诉人家;而听的人又因摄于伊的积威之下,虽然心上实在不愿意听,但也不能不装着很有兴,很重视的样子,默默地倾听着。如其不这样的话,或竟忍不住而失笑起来,那就算大大的越礼了!所以我们都已习惯于这一种强迫的听讲,再也不会触恼伊的。
可是平心论来,伊对于讲故事的兴趣虽象是太浓厚了,往往是硬捉人家来听讲;但伊的口才,却委实不错,一桩很平凡的故事,经伊一讲,便比原来的要动听了许多。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以致于第五,第六次的重复的讲述,也总不至丝毫精彩都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确也听得很高兴。
不一会,已到得那戏台前面,太后就在正中安着的御座坐下,我们这一起的人,便照例分着两边,在伊后面侍立着,我抬头把这戏台一看,不由就暗暗地佩服那些太监的能耐。他们竟在极短的时间里,把这一座陈旧不堪的戏台,收拾得很象样了;而且竭力的模仿颐和园里那一座的格式,差不多已模仿到三四分模样了。又喜当我们未来之前,先来收拾的人也注意到这一座戏台,所以台上的几根柱子,早就重样漆过,那些雕在柱上的飞龙,也一律加敷了一重金颜色,黄澄澄地耀得好生夺目;此刻再挂上几幅绣花的锦幔,顿觉面目一新,好比一个乡下老头儿换上了一套时新的袍褂,他原有的一股寒酸愚蠢的土相儿虽不能完全掩过,但至少是不会再如何触目的了!太后也点头微笑,表示这座戏台尚可用得,那末我们的戏不就可开锣吗?却还不能咧!要开锣是必须由太后自己吩咐下去的,谁也不敢擅动;而此刻的太后,还正在很有兴地给我们讲着杨四郎怎样失落在番邦,怎样和铁镜公主成婚,后来怎样思亲,公主又怎样给他盗令,他怎样进关…………等一切详细的节目,伊决不肯让我们听了一半便停止,于是戏就搁下来了。一直待伊讲到杨四郎怎样回去太迟,以致给萧太后知道,险些要把他斩首,幸得公主力救才免,这一段故事方始完毕。
待伊的话匣子一停,大家都知道戏是快要开演了;伊也不用说什么话,只把手一摆,旁边的太监就飞一般的奔近戏台边去,高声叫道:“老佛爷有旨,吩咐开锣!”台上便霎时间金鼓大作,一幕一幕地演出来了。在演戏的时候,太后还不肯安静;尽是絮絮不休的把戏剧上的各种习惯和轶事说给我们听。其实伊也是因为看戏看得太多的缘故,再也无心安坐静观了。不过伊所给我们说的,却是大半是前此伊早就告诉我们的老话,而我们是不得不假装着闻所未闻的神气来听伊说的。
“唱戏的人可说个个都是非常信奉神佛的!”今天,伊居然说出了一段比较新颖的事迹来。“尤其对于那人称伏魔大帝的关公,格外的恭敬虔诚,无论一个怎样欢喜说笑话的人,只要是轮到他今天拜关公。他就立即会端庄起来。而且还得先去买一尊关公的佛像来,弄好了高供在桌上,点起香烛,诚诚恳恳的磕了头,然后再取出来,依旧供在桌子上,再磕过头,最后,还得把它搁在纸锭上焚化。经过了这样的一番做作,他们方始能安心,否则必将惴惴然以为大祸将临。”
“唱戏的人又是最爱守旧的!”太后继续的把伶人生活形容给我们听。“无论一举一动,以及戏文中的唱词,念白,行头上的花纹,插戴,都视同金科玉律一般的谨守着,永远不肯改变;不但他们自己一生一世是这样,就是传到他们的子孙或徒弟,也仍然如此!”
这两段话可说是极中肯的,我后来又听别人也是这样说起过。
我以为中国旧剧的文场,还不失为一种很优美的歌剧;至于武场就不免太热闹了!每逢演到两军交战的时候,大锣大鼓,敲得人的耳朵也几乎震聋;再有那种拚性舍命的蛮打,也失之太野,我是最不爱瞧的。
这天的四郎探母演完之后,太后告诉我说,那个演佘太君的身材的很小的太监,成绩最好,该赏他一赏;我却根本没有研究,只得随便含糊的应了一个是:后来这个太监究竟有没有得到伊特赏,也就不得而知了。
更新于: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