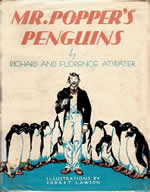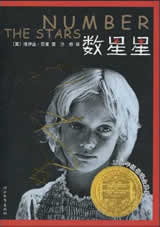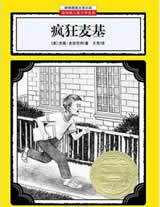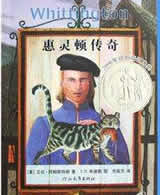第十章 舞会见了,海蒂
1918年4月2日
蒙大拿州维达镇西北方三里处
亲爱的查理:
我希望很快就可以寄个包裹给你――放心,这次不是袜子!很高兴知道我上次寄给你的袜子让你和同伴们足足大笑了一场。我不擅长织东西,但是挺会缝拼布被的。派瑞丽对我的进步感到满意。老实说,我也很满意。我猜,你已经猜到我在帮你缝拼布被了。我把它叫作“查理的螺旋桨”。是我自己设计的旋转图案,庆祝你升为技师。被子虽不防水,却足以保暖。
我下国际象棋的技术大有长进。吉姆上星期来下棋,虽然还 是他赢,但是我的表现也不赖。他从路易斯 敦的那边听到一些坏消息:一群暴徒跑进当地的高中,烧光所有的德文课本。那所居然没被烧掉,还 真是奇迹。有位气愤得辞职了。
我试着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垦荒。卡尔教我怎么辨别土壤播种的时机。公鸡吉姆是用尝的,卡尔的方法显然比较好――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捏一捏。我的土还 是一块一块的,种子会烂掉。巴布・奈夫吉说不用担心,等到下个月中旬再播种也不迟。我希望不需要等那么久。
读了我的农事报告,你会笑我吗?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整天担心土壤啊、气候啊,似乎很可笑。我的担心不全是为了自己。现在当农夫是很爱国的事呢。政府鼓励我们种得越多越好。想想看,我种的麦子可能是某些士兵的粮食呢!
但是希望不是你的粮食。希望等到八月谷物成熟时,你早就安全返家了。
你的
海蒂・伊尼斯 ・布鲁克斯
我仔细看看自己的钱包,任何蛀虫待在里头都会饿死。我不禁想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穿过沙漠,上帝为了喂饱他们,从天上落下食物。我抬头研究一望无垠的蒙大拿天空,显然这阵子不会有食物或任何东西掉下来。我很担心,每天祈祷时总要向上帝请愿:“主啊,我需要一些收入,让我撑到收割季节。”我试着解释,“我不挑剔,可是我需要您的帮忙。”再一次的,我期待上帝神秘显能。
毫无头绪的――也盼不到从天而降的讯息――我做完了谷仓里的活儿。确实渐渐赶走了。草原上缀满紫色的番红花、黄色的风铃草和毛茸茸的猫尾草,我经过时总忍不住摸摸它们。真想摘些花送给派瑞丽。想是这么想,但还 有一堆篱笆等着我呢。我收拾好工具,继续出门干活儿去。
一匹马载着一位骑士,朝我这儿来了,看起来相当眼熟。绥夫特・马丁自愿从维达的巴布・奈夫吉那里帮我顺路带信过来。这样一来,我就不用亲自跑到城里,但我宁可他不要这么做。
“进展很快嘛。”他滑下麻烦的背,轻轻落地,脚上的那双靴子磨损得相当厉害。
“恐怕钉不完吧?”我又钉了一个钉子。
绥夫特脱下帽子,把它挂在马鞍上。他后脑勺上一束不听话的头发翘了起来,像个问号。我可以闻到发胶的淡香。“需要我帮你敲一会儿吗?”
我的手臂哀求我说“好”,可是我顽固的心却回答:“不,不,多谢了。”
“我把你的信带来了。”绥夫特拍拍大衣的口袋,“还 有一些报纸。我知道你喜欢读报纸。”
“谢谢你。”我脱掉手套。
他迟疑了一下,似乎想说些什么。“又有一封从法国来的信。”他说。
“是我的查理。”我听出他声音里的疑惑,立刻这么回答,并把信塞进我的午餐篮子里。
“好朋友吗?”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话让我的胃一紧。
“我们认识很久了。那只猫就是他送的。”
绥夫特快速点点头,好像要把这项讯息塞进脑子的资料库里。
“我最好开始干活儿了。”我说。
他朝他的马走去。“午安,海蒂。”
“午安。”他还 没踩上马镫,我已经开始钉钉子了。
“噢,还 有一件事。”他停了下来,“舞会,在维达活动中心举行。你会去吗?”
“我不跳舞。”我可以想象艾薇阿姨会坚决反对地说:“接下来就要喝酒胡闹啦!”
“如果我说那是你的爱国责任呢?”他问,“这场舞会是为了募集自由债券的钱。”
一听到“爱国”两个字,我立刻全身僵硬,我还 没忘记厨房桌上的讯息。“就像参加忠诚部队吗?”
他吓了一跳。“什么?”
我告诉他桌上纸条的事。“我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他玩弄着麻烦的缰绳,似乎有话想告诉我,我等着。“你有没有……”
他抚着马的脖子。“你说了什么关于战争的话?让别人觉得你可能反战吗?”
“我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战事。”我说――除了公鸡吉姆――不过没必要让绥夫特知道。
“那,或许……”他又顿住了,“你知道的,海蒂,这阵子大家都严密地注意别人。”
我挥舞着手中的榔头。“如果有人注意我,他们只会看到一些跟爱国无关的捡石头啦,筑篱笆的。”我逼自己露出笑容。
“别拿这些事情开玩笑。”他的口气冷却得比灭火还 快。
“你倒是说说看,我做过什么可以让人指责我不爱国的事?”对话的气氛改变了。我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卷进漩涡里。不管绥夫特有多迷人,他仍是防卫委员会的头子,也是他的儿子。
“我知道你不喜欢听,但我还 是要说,大家都在谈论卡尔・慕勒。”
“什么?”我几乎失手让榔头掉在地上,“谈论什么?”
“你听说了郎多普那边的维恩・汉弥顿被控告的案子吗?他说他不要去打仗,如果被征召了,他们必须把他抓走。”
我点头。我曾在报纸上读过。
“有一天在巴布的店里,卡尔说那个人有权利说这些话,说是言论自由什么的。”
“难道不是吗?”
“这是战时,海蒂。”他看着我的眼睛,“而且卡尔是外国敌人。”
“他才不是敌人。”我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绥夫特对我微笑,是那种艾薇阿姨式的微笑,是她跟我说打我是为我好时的那种微笑。“我不想让你不开心。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他耸耸肩,“也许只是一些孩子的恶作剧,我是指那张通知。”
如果他想转变话题,这招并不管用。“绥夫特,他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他说,“他很幸运。”
他把帽子从马鞍上拿下来戴好。“关于舞会――我不是要骗你,确实是为了募款。如果你来的话,请为我留一支舞。”他抛给我一个温暖真诚的微笑,让我忍不住责怪自己或许多心了。
我也对他微笑。“你的脚趾会后悔的。我不太会跳舞。”
“我是个好老师。”他说。
“我最好回去干活儿了。”我转身看着篱笆,试图掩饰脸上的红晕。
“舞会见了,海蒂。”他一个箭步跃上麻烦的背,马上转身骑走。
我的心跟着麻烦的马蹄声狂跳。我摸摸身后,找到了一块大石头,立刻跌坐下来。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就像走钢丝似的。我深呼吸了几次,让心跳放缓。宣传单的事情当然就像他说的那样,绝对是场恶作剧。而且,他跟我讲卡尔的事,是在帮我忙。我可以告诉卡尔,要他在镇上说话小心一点。或许,绥夫特和我其实很相像。他坚持某些自己在意的事情,譬如:他的牧场和国家。我也很顽固;不管艾薇阿姨怎么打我,坚持要我改过,我还 是那么顽固。
我想象自己在舞会上努力不要踩到绥夫特的脚。我敢打赌,只要跳一支舞,他就会去找别人了。若是蜜尔・包威看到我跟这么迷人的男人跳舞,大概会气死吧?我想起八年级的那场舞会。“噢,海蒂。”她对我说,“穿得这么朴素来参加舞会,真是聪明啊。”她的朋友都笑了。我当时就想离开,可是好心的查理却过来邀我跳华尔兹。我确定他的脚一定被我折腾得要命,可是查理完全不抱怨我笨手笨脚。“你穿蓝色很好看。”他说。
想起他的善良,我忍不住叹气。望着一排等着钉铁丝网的柱子,我又叹了口气。
我举起榔头继续工作,一直钉到再也举不起榔头为止。然后我吃带来的午餐,从玻璃罐里喝清凉 的井水。只要运用一点儿想象力,我可以假装自己喝的是阿灵顿那家药房卖的草莓汽水,或是郝特叔叔店里卖的果汁;并假装这些冷掉的饼、不够脆的苹果和水果干是一顿丰盛的宴会。把手拍干净后,我开始读信;那些报纸则等到今天工作结束了,吃完晚饭之后,再来当“甜点”享用。
查理的信相当简短,他终于收到我的信了。查理目前在机场值勤,必须二十四小时轮班。他在信末写着:
很多人都倒下了,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各种疾病。我到目前为止逃过一劫,但是这边的流行性感冒很严重,那些病毒简直跟德国佬一样可恶。昨天我们看到一排被毒气弄瞎的士兵――他们像一排大象一样,每个人的手都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
下一段被检查信件的人剪掉了。我继续往下读:
我遇到三个来自蒙大拿大瀑布区的士兵。他们好想办一场棒球赛。我可能会参加,让他们瞧瞧爱荷华的厉害!
你的(寂寞的)朋友
查理
我颤抖着把信收好。春天的太阳似乎又冷了几摄氏度。查理从军的时候多兴奋啊,他要去拯救世界!我接到查斯 特舅舅的信,离开艾薇阿姨的时候,也很兴奋。我猜,查理的情况和我相似。我们都以为自己即将展开的新生活既英勇又风光,多少是有点英勇和风光。可是你必须忍受挖掘、刮除、扒开泥土、痛苦与折磨,才找得到英勇和风光的那一面,如果真的找得到的话。
我摇摇头,甩掉这个想法,接着拿起郝特叔叔的信。这封信很厚,完全不像他的作风。或许郝特叔叔也寄了杂志剪报,他以前寄过一次。
我撕开信封,一张纸掉了出来,落在地上。“付给海蒂・伊尼斯 ・布鲁克斯 :美金十五元。”是支票吗?我再仔细看,是《阿灵顿新闻》付给我的。我赶紧展开郝特叔叔的信,寻找答案。
亲爱的海蒂:
我非常喜欢读你的来信,于是就拿给《阿灵顿新闻》的编辑乔治・弥顿伯格先生瞧瞧。他觉得你对垦荒生活的描述如此生动,一般读者也会有兴趣阅读。你可以看看他的信(随信附上),他希望刊载更多你写的故事。但愿你会答应他。
爱你的郝特叔叔
我拿起弥顿伯格先生的信。他希望我“每月写一篇”,每篇的稿费是十五元,一直写到我真正拥有自己的农场,不再是个垦荒者为止。
“哈利路亚,塞子!”我大喊一声,把老马塞子吓坏了。蒙大拿的天空确实降下了食物――至少,描写蒙大拿的天空可以带来食物。“实实在在的钱!”我用手指头算算月份,“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塞子,总共有八个月呢!八乘以十五是……”我迅速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块钱!”我把手臂伸向广阔的蓝天,“谢谢你,主啊,谢谢您神秘的安排。”
我小心地把信和支票塞回午餐篮子里。接下来的一整个下午,我都在钉钉子,并想着要写给弥顿伯格先生的下一篇文章。每个月十五块!一直到我真正拥有这块地为止!我会先预留最后一笔手续费:37.75元。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支出,可是我的存款就足以支付了。也许我可以买一双像样的、合脚的靴子,不用再穿郝特叔叔那双旧靴子;我也可以帮自己订一份《狼点新闻》。报纸和靴子只要七块钱就可以搞定。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了。“塞子,我们一定做得到。”筑篱笆的时候,我手中的榔头就像羽毛一样轻盈。
钉好最后一根钉子,收拾好工具之后,我简直是飘着穿过了整片繁花盛开的草原。“塞子,你认为其他的百万富翁今天都在做些什么呢?”我问,脑子里还 闪过一幅画面――派瑞丽指着《猴林目录》里三块钱一把的橡木摇椅,说:“坐在这上头摇宝宝该有多好。”他们正打算存钱买新的牵引机,她绝对不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那晚帮紫罗兰挤奶的时候,这头牛的脾气比平常更坏:它似乎知道,正在帮它挤奶的是一双自私的手。
“好吧。”说着,我拍拍它的肚子。可恶的牛,我觉得它在帮上天传达讯息,“我就继续穿这双旧靴子吧,这样就可以帮派瑞丽买那把摇椅了。”
紫罗兰用它的大眼睛看着我……一脚踩在我的右脚上。什么嘛,刚刚才说它是上帝的使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