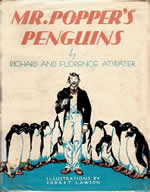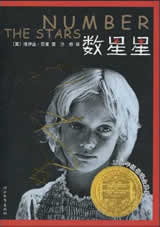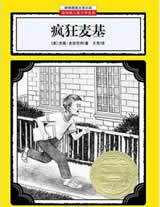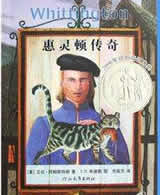第十八章 原谅敌人,也原谅我们自己
1918年7月
阿灵顿新闻
垦荒家庭――独立纪念日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豪华的乐队舞台或城市公园,就无法像大城市里的人那般热闹地庆祝独立纪念日。大家都会来到狼溪岸边野餐、打棒球、谈论旱季。虽然气氛轻松,但我们会在中午时分一起向前线的士兵们致敬。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笔者――都祈祷联军在肯地尼战役的胜利代表这场战争即将结束。
“到时会有香草冰淇淋。”一提到国庆日野餐,却斯 足足说了五分钟之久,“还 有棒球赛!”
“听起来真棒。”我又从井里打了一桶水,并把这桶水拖到奄奄一息的里。感谢上帝,幸好查斯 特舅舅挖的井够深。今天早上,我打了无数桶水去浇长豆,手臂累得仿佛随时都会从肩膀上脱落。
却斯 灌满一小盆水,细心地给我的向日葵浇水。“去年就是这样。”他说,“她在咖啡罐里种花。她说今年种的是小宝宝。”我们两个都笑了。
为洋葱、地瓜、甜瓜和胡萝卜浇水时,我想到这辈子所浪费的水。在这里可不行!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即使是星期六的洗澡水也得好好儿利用才行,先用来洗澡,再擦地,然后清洗前廊小花园的灰尘。
我站起身来伸展伸展,试着驱走背部的酸痛。“哎哟。”
“卡尔说,已经三十二天没了。奈夫吉先生说是三十一天。”却斯 把手伸进盆里,用手指蘸些水在脸上洒了几滴,“我认为卡尔说得对。”
“我也赌卡尔是对的。”我揉揉却斯 的头发,“如果要我打赌的话。”
有却斯 帮忙,我的活儿很快就做完了。我要他赶快回家去。“我们明天来接你,一大早哟!”他转头喊着。我进屋继续忙个不停,很快的,四个野樱桃派被摆在厨房的桌上放凉 ――如果在这么可恶的热天里还 有可能凉 下来的话。
从上个星期开始,我就把床垫搬到屋子外头睡觉。晚上,屋内连一丝微风也没有,即使开着门也一样。
睡在屋外的第一个晚上,简直无法入睡。只要躺在草原上,就会听到一大堆声音。一旦鸡群安静下来,夜里的鸟立刻开始聒噪。一整夜,草喀喀嚓嚓地响个不停。但愿是因为风的关系,可是空气却凝重得犹如糖浆。不,这些草叶摩擦声属于草原之卒:老鼠、野狗,还 有天晓得是什么。派瑞丽不久前才看到一只臭鼹。唯一不会让我担心的,就是咬伤紫罗兰的那只狼。过后,它就失去了踪影。觊觎狩猎奖金的猎人一定已经抓到了它,这一带的狼几乎都被他们捕光了。
把床垫拖到户外的第二个晚上,我终于被失眠、热浪和整日拔草的辛劳打败,一下子就入睡了,速度好似抓田鼠那般迅速。床垫下的草地凹凸不平,睡起来不怎么舒服,但总比跟烤箱一样的屋里强多了。
独立纪念日的早上,胡须先生用砂纸般的舌头把我舔醒。我拍拍它,伸了个懒腰。
“哎哟。”睡在户外的转天早晨,我总会发现脖子或背部又扭伤了。我僵硬地弯腰,将床垫搬回屋里,打理好自己,准备前往狼溪。除了水果派、毯子、国家战争储蓄日的扇子之外,我还 带了一样东西,大家看了肯定会吓一跳。
准备好后,我继续写信给查理:
一开始,莉菲和我很担心萝缇,她是那么的小,现在.那个孩子却犹如一桶猪油般的强壮。不知道其他孩子是否会吃新宝宝的醋,可是他们都很喜欢她。麦蒂几乎把她宠坏了!她想为萝缇缝一床被子――姐妹被――我正在帮她。针脚不太平整,但是充满了爱。
一听到马匹的铃铛声,我立刻停笔,抓起帽子,环顾四周。如果我忘了什么,也没办法喽。我提起装满东西的篮子,出门跟慕勒一家打招呼。
“你简直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派瑞丽说。我露出微笑,欣喜地发现她双颊泛着樱桃似的红晕。生下萝缇后,她的身体恢复得很慢。
“你是说我看起来像画里的烤鹅吗?”我爬上马车,坐在她身边,开始扇风,“是不是再也没风可以吹了?”
“溪边会比较凉 。”她说,“既舒服又凉 快。”我们安静地坐在马车上。天气热得让人连聊天都提不起劲。
“哈罗!”到了野餐地点,吉姆帮孩子们下马车。麦蒂直接跑到莉菲身边,要她看看慕丽的新帽子。却斯 帮卡尔拴好马,就跟小艾尔莫和路德教会的一些孩子跑到溪边抓蟋蟀。
“已经在荫凉 里帮你们留好位置了。”莉菲招手要我们过去。我们铺好毯子,把苹果箱当成萝缇的小床。
我倒冰红茶给大家喝,并且跟一些教会的女教友聊天。“所有的人都来了吗?”我问。
“奈夫吉家的人要等中午打烊才来。”莉菲用冰凉 的杯子碰碰额头,“他们从来不会错过任何棒球赛,即使巴布也一样。”
我对着冰红茶微笑。等一下要让他们瞧瞧爱荷华阿灵顿的厉害!
“葛莉丝和维恩也快来了。”她继续说,用手指数着我们的邻居,“马丁一家倒是很少来。”
正合我意。
果然就像莉菲说的,奈夫吉一家下午来了。
“要打球了吗?”巴布一边驾着马车,一边高声喊着。
虽然有些人抱怨天气太热,但球场很快就整理好了,球员们也分好了队伍。我已经很久没有打棒球了。我的邻居都不知道我会打棒球。感谢查理之前的耐心指导,我打得很好。
我把手伸进篮子里,准备让大家惊喜。
“谁都可以玩吗?”说着,我的左手戴上了棒球手套。
“这是怎么回事?”葛斯 特・崔夏特朝着我的方向吐了一口口水。他刚刚还 在抱怨路德教会的德国人也想打棒球。维恩指出“崔夏特”听起来就像是德国姓氏,葛斯 特却摇摇头。“是瑞士姓氏。”他说,“瑞士。”我猜,我上场打球一定让他恼怒不已,甚至比看到德国人打球更生气。
“我想加入。”我对他说。
葛斯 特吹着口哨。“那么,你最好参加……”他指着保罗・齐林杰,“另一边。”
我点点头,加入保罗那一队。我们先打击。打击不是我的强项,但是保罗打出一垒安打后,我也跟着打出一支一垒安打。紧接着,亨利・汉萧击出一个强力二垒安打,把保罗送回本垒。现在轮到却斯 打击。
“短打!”我喊着。即使天气这么热,如果来个短打,我还 是可以跑回本垒。
然而,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已经有两人出局了,却斯 还 是见球就打,被三振出局。
“出局!”特迪牧师大喊。
却斯 丧气地丢下球棒。“我差点儿就击中了。”他说。
特迪牧师拍拍他的肩膀。“下次运气会好些。”他说,“现在轮到你跟队友上场守卫。”
却斯 守左外野。我们一律把年轻人摆在外野,他们才有力气跑来跑去接外野球。保罗拿了球,走向投手丘。第一个打击者是维恩・罗宾。
“看你能不能打到这球!”保罗吹嘘着。
维恩的眼力很好。他打击出去,球飞了起来。接下来的五个打击者也打击成功。
“没人出局。”特迪牧师喊着,又有一个打击者跑回本垒,“五比一。”
“嘿,保罗。”我站在三垒叫他,“过来一下。”
保罗一脸疑惑,但还 是走了过来。我建议跟他交换位置时,真希望我手边刚好有部照相机,可以趁机拍下他的表情。
“我一直都是投手啊。”他说。
我指指目前满垒的情况。“像现在这样吗?”
他摇摇头,终于把球交给我。我赶紧站上投手丘。
“等一下。”葛斯 特大喊。
“海蒂,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瞧瞧。”莉菲扯着喉咙大叫。
特迪牧师擦擦脸上的汗。“投球!”
我一连三振了两个打击者,查理看了一定很高兴。只投了六球。
维恩再度站上打击位置。“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他喊道。
“我的球会快得让你看不见。”吹牛实在不是淑女该有的行为,不过棒球就是这么回事。
“那是指对女孩子而言吧。”他故意激我。
我用力一投,球朝着本垒板飞去。维恩猛地挥棒,球飞过我的头顶,飞得远远的。所有的跑者都奔回本垒,球赛结束,我们惨败。
“真抱歉,保罗。”我把球交还 给队长。
“只是玩玩嘛。”他说,并对我眨眨眼,“下次你一定会把他三振出局。”我们握手,一言为定。
“下次。”我说。
“来吃冰淇淋吧。”齐林杰老爸宣布。我敢说,那些冰淇淋放在我的水果派上正好。
我们聊天、吃东西。派瑞丽和我走到溪边,脱掉鞋子和袜子,让脚丫子凉 爽一下。我们把从溪边摘来的野李子装进午餐篮里,等装满了,又回去跟其他人谈天说地。齐林杰老爸率先动手收拾。“还 有黄昏的活儿要做呢。”他说。
“我们也该走了。”派瑞丽说。我帮她把疲倦、肮脏的孩子们和所有东西都搬到马车上。
派瑞丽准备把麦蒂放到马车后头时,麦蒂尖声嚷着:“我要坐在海蒂旁边!”
“好的,宝贝。”我把她从派瑞丽手中抱了过来,一起坐着。才几分钟,麦蒂就睡着了。她趴在我的膝上,身子像热水袋般热得发烫。我胸前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
快到我家时,我轻轻地把麦蒂抱到派瑞丽怀里。“在这里放我下来吧。”我告诉卡尔,“走一走会比较凉 快。”我亲亲麦蒂的额头,拿起放在车后的篮子,沿着小径走回家。看到屋子时,我身上的衣服也几乎干了。我坐在前廊阶梯上,闻着膝头上篮子里的野李子香气,先是回想这美好的一天,接着思考该怎么写这个月的《垦荒家庭》。
一阵马蹄声让我顿时回过神来。牛仔常常骑马经过我的农场,追着一两只尖角牧场走失的牛。今天这三位骑士似乎正朝东前往马丁家。其中一位离开另外两位,让马转了个身:一匹相当高大的骏马――往我这边骑来。
“晚安,海蒂。”我从站着的地方就可以闻到酒味,“野餐好玩吗?”
“是的,马丁先生。”我站起身,转身进屋,今天晚上别想在外面睡了。
“好热,对不对?”他挥舞缰绳打蚊子,“比去年还 糟糕。”
“没错,是很热。”他显然不是骑过来讨论天气的。
“去年夏天还 有蝗虫呢。”绥夫特在马鞍上挪挪身子,“上一分钟,天空还 像狼溪一样清澈。”他抬头看天,研究着黄昏的景色,“下一分钟,立刻暗得像黑夜,全是蝗虫。”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才几分钟,葛利家的麦子就被吃光了。”绥夫特摇着头,夸张地表示同情,“罗宾家也是。接着是亚麻。他们的收成还 不够付种子的钱呢。”他粗鲁地笑了一下,“当然,它们不只吃五谷而已。我的外套挂在篱笆上,居然也被那些蝗虫吃掉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马丁先生?”他当然有话要说。我的背脊发凉 ,不管他要说什么,准不是什么好事。
“只想引起你的注意。”他滑下马来,“只是这样。”
空气中传来草原上的细碎声音。我支起耳朵,仔细聆听是否有蝗虫的拍翅声。
“好啦,我注意到你了。”
他朝我走近几步。“这种生活很辛苦。”他的声音变得更温柔了。
我忍不住放声大笑。“别再宣传啦。”
“海蒂。”他停顿一下,说,“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彼此的相处出了问题。”
“问题?”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你放火烧了别人的谷仓,这叫作问题?带一群人欺负艾柏卡先生,这也叫作问题?”我生气地拍打裙子。
他往前迈了一大步,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臂猛烈摇晃,篮子里的李子都飞出来了。“我要你听好。让我把话说完,就这么一次。”
难道我已经习惯他的粗暴了吗?我的腿并未发软。我看了一眼他的手,他立刻放开。
“卡尔家的火不是我放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根本没办法阻止他们。别问我纵火的人是谁。”他投降似的高举双手,“不过,我还 来得及在火起之前,把你谷仓里那堆烧着了的稻草拉出来。”“什么?!”他试着拯救我的谷仓,而不是放火烧掉它?
“还 有艾柏卡那件事,我承认是失控了。”他摇头咒骂一声,“法律说我们必须支持国家和这场战争。如果大家都像艾柏卡这样逃避责任……”
“你真好意思。”我冲口而出,“逃避责任?那你的责任呢?你安安全全地站在这里,可是别人呢?例如,艾尔莫和……和……”我不愿意跟这人提起查理的名字,“无以计数的其他人,都上战场去了。”
绥夫特的反应仿佛是我拿鞭子抽了他。“你说得对,大家都这么想。大家都认为我是在逃避责任。”他揉揉额头,“我不想等征召令,我已经登记入伍了。”
“那你为什么还 在这里?”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绥夫特捡起一颗被他摇落的李子,“后来我发现,妈妈求州长让我领导防卫委员会。征兵处说那可以当作我的服役。”他转着手里的李子,接着弯起手臂,把李子丢进夜色里。
绥夫特脸上的那种表情,我太熟悉了。跟艾薇阿姨住在一起时,我的脸上就曾经无数次地出现过那样的表情。我此刻的感觉犹如即将为拼布被缝上最后一片花样。这是一个愤怒的人。他气自己的,无疑的,他更气自己,怪自己为什么要听别人的话。我忽然想到――也足以理解――绥夫特和我在这件事情上十分相似:来这里之前,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
我无法克制自己,那一刻,我原谅了绥夫特由于人生苦涩所干的坏事。“对不起。”我说,“原来你有这么多困扰。”《圣经》上说:要善待彼此。我几乎可以看到我的天使冠冕上又多了一颗星。
他转身面对我。“所以,我才需要你的地。”
“什么?”我的冠冕滑了下来,“不,我的意思是说,没想到你有这么多困扰,但这并不表示……”
“都是因为那个一直和你通信的家伙吗?”绥夫特的眼睛盯着我,“你在帮他垦荒吗?”
“查理?”这段对话千回百转,简直就像麦蒂裙子上的花样,“绥夫特,谢谢你救了我的谷仓,也谢谢你试着拯救卡尔的谷仓。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你不卖?”天太暗了,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但他的声音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愤怒。
很奇怪的,艾薇阿姨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她曾经告诉我:一位真正的淑女至少得拒绝两次求婚,才能接受。当然,她指的是婚姻,可是我决定还 是听她的话。“不。”我再次拒绝他买地的要求,“晚安,绥夫特。”并尽量保持尊严地迈上阶梯。我打开门,转过身,他已经骑上麻烦,让大马转了个身,蹄声有如般地离开了我的院子。
那晚,我听到的不只是蹄声,还 有真正的闪电。天空降下了雨水――美丽的雨――浇灌着饥渴的草原。
听着屋顶上的雨声,我坐下来写7月份《垦荒家庭》的结尾:
我叔叔心目中的英雄是亚伯拉罕・林肯,独立的象征。关于林肯的故事,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选上总统之后,让几个政敌担任官员。看来,不论是当时或是现在,最大的自由来自原谅。让我们拥抱这样的自由,原谅敌人,也原谅我们自己。
1918年6月15日
法国某处
亲爱的海蒂:
最近我常常想到你。你以前怎么惹我笑,怎么像风车一样转动手臂投球,怎么吹额头上掉落的头发。我需要想这些愉快的事情。
我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打赢战争回家。此时此刻,我却觉得自己似乎永远也无法离开这些泥巴、寒冷和痛苦了。
我知道你期待我这个老充满幽默,可是我最要好的今天早上死了。我离他不到二十码。在所有的训练里,他们并未告诉我们死亡是什么模样。
我头一次对自己是否能活着回家失去信心。我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了。我以前总是吹嘘说我杀过德国佬。杀人没什么好吹嘘的,没什么值得吹嘘的……
你的查理